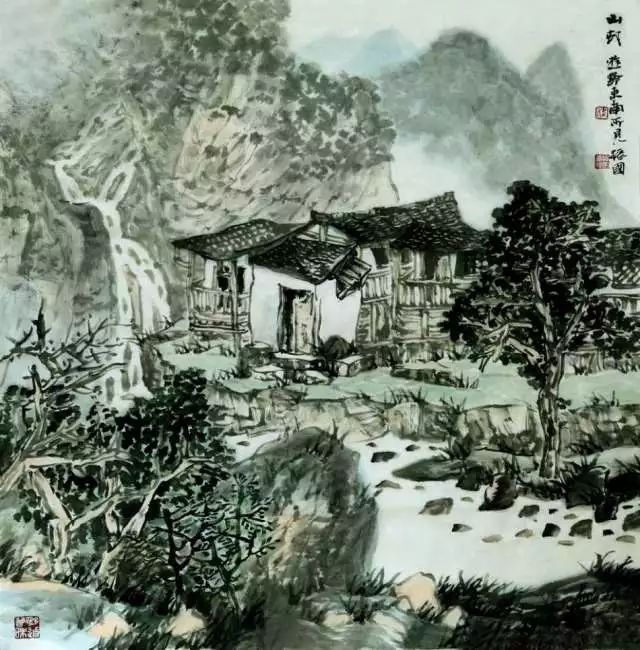访谈丨董天策:以问题为中心:传播学与符号学之互补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传播符号学理论与应用 › 访谈丨董天策:以问题为中心:传播学与符号学之互补 |
访谈丨董天策:以问题为中心:传播学与符号学之互补
|
要说学古代文学对研究新闻传播的影响,我觉得在于文化底蕴和人格精神方面。譬如读屈原、读杜甫、读陆游、读辛弃疾,自然也就忧国忧民,关心时事,以报效国家作为精神追求。这种入世精神与新闻传播的责任担当与历史使命是完全相通的。当然,古代文学也有另外一个传统,像陶渊明、苏东坡,或归隐自然,或放达人生,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决不同流合污。去掉其中的遗世成分,这个传统的独立精神也是新闻传播工作者很需要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新闻业是随着民主政治而发展起来的,就中国而言,新闻业的产生也恰恰是在开启民智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闻传播是对社会的及时介入,积极介入,采编技巧只是入门路径,一个记者编辑要真正成功,靠的是家国情怀和道义担当,这些东西和文学是一脉相通的。
何一杰:您和国内外很多在传播学领域内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学者一样,都有文学或者其他学科的背景,现在的新闻传播教育却分得越来越精细。对此您怎么看? 董天策:从文学或其他学科转行到新闻传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历史的机缘。当时,新闻教育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教师,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引入,又激发了很多人的兴趣。于是,转行也就很自然了。在我自觉不自觉地转入新闻传播之后,慢慢感觉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很可能活跃而疏浅,所以我一直跟新闻院系的学生讲,要加强文史哲、政经法的功底,光凭新闻传播学的那点东西,肯定是不够的。原来说记者是“杂家”,要见多识广,但真正达到“家”的程度,就决不是什么都知道一点,一定是很专业了。 现在,很多综合性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都有主辅修制,学生呢,都忙忙碌碌,似乎修了很多课,还辅修了其他专业,结果是拿了学分,拿了毕业证书,至于究竟具备了什么真才实学,难免茫茫然。其实,我觉得倒不一定要去辅修什么专业,关键是要钻进去,尤其要在养成人文底蕴上下功夫。我们的专业越分越细,似乎是为了保障人才培养越来越专业化,但学生的视野和格局却越来越小,缺乏创造性。美国的专业并没有我们分得那么细,尤其是常春藤高校,一二年级基本上都不分专业的,修些通识课,注重博雅教育。这些东西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柢,你读读柏拉图,读读莎士比亚,对人类的文明文化,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空间就有了解。 现在世界变化太快,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变化巨大,让人两只眼睛总是要盯住眼前,总是着眼未来。未来媒体格局怎样,谁也说不清楚。处在大变革大变动时代,我们其实应该静下心来,在关注现实变化的同时,还要往回看,回到历史的现场,回到历史的纵深,去领悟一些东西。所以,不仅要广泛涉猎,而且要深刻思考。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人文精神,要有社会责任,要有历史使命。比如要有家国情怀,对社会政治的积极关心,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精神营养除了来自新闻本身的传统,还来自更广泛的人文传统。人文传统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底色与人格底蕴,最终决定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何一杰:您这次来参加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我们都非常期待您的发言。符号与传播关系甚为密切,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传播学和符号学无需区分关系。更常见的是传播学家和符号学家讨论的相互归属的问题。您如何看待传播学与符号学的联系? 董天策:符号学跟传播学的关系,不能说谁属于谁,它们的研究路径不相同。符号学传统更多跟哲学、解释学相近,它要解释意义如何产生,意义怎么发挥作用。既要深入符号与符号的关系中,又在文化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传播学,特别是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更多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范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学界有一场关于新闻与传播的论争,讨论两者要不要分家。凯瑞认为新闻与人文学科关系更紧密,跟传播的实证研究不是一家人,新闻终归还是要去建构人们的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国没有分得那么细,实证研究的路子虽已起步多年,但由于不少人的学术训练不到家,未免步履蹒跚,批判研究的路子更是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短时间内恐怕也难以发展起来。要推进传播学的发展,从符号学的视野出发,运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中各种符号学问题,倒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术路径。 何一杰:的确如您所说,符号学在微观的结构意义和宏观的文化意义上都有深入,但我觉得从微观到宏观的连接上符号学的研究还有些缺乏,而传播学对过程的重视恰好弥补了这一点。这个意义上,二者的研究可能同属于一个更大的范式。您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中国符号学应当寻找怎样的突破口? 董天策:对我来说,这是两个高难度的问题。虽然涉猎过符号学,却没有专门研究,不敢对当代中国符号学的发展乱做评价,只能说说对符号学发展的感知。大体上,20世纪80年代,语言学界率先介绍和研究西方的符号学理论,特别是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理论;进入90年代,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三分法符号学研究方法、卡西尔(Ernst Cassirer.)从符号学出发的人类文化哲学、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Бахтинг)的对话思想等等,得到广泛的介绍和研究,这就突破了语言学的传统,进入到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2000年以来,中国符号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更加多元,注重把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方法同具体的研究领域结合起来,符号学分支领域百花齐放,枝繁叶茂,譬如传播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影视符号学等等。当然,符号学理论研究也有纵深开掘。譬如赵毅衡先生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以中国文化为基础,以批判、发展的眼光阐述符号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符号学本土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图片来源于网络) 至于中国符号学应当寻找怎样的突破口?实在无力从理论上回答。不过,我注意到,四川大学以赵毅衡先生为领军人物的符号学团队,最近这些年来十分活跃,出版了专门的学术刊物,推出了一大批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召开了有影响的学术会议,正在形成中国符号学的西部学派。关于符号学西部学派,赵毅衡先生有专文阐述,我不敢妄加评论。无论如何,像四川大学这样围绕符号学领军人物组建一个充满学术活力的学术团队来开展符号学研究,应当是中国符号学突破的一种重要学术方式。 何一杰:在您看来,就目前的学科状况而言,符号学与传播学如何互相有所补益呢? 董天策: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符号学与传播学是可以互补的。解决问题需要调动多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资源。比如说研究舆情,肯定要去统计分析,掌握动态,跟社会科学有高度关联。但是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现在投入了那么人力物力财力来监管舆情,可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却往往不按人希望的路子走,甚至问题还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我们单从技术上努力是没法解决问题的,这时就该冷静地分析问题的根本。网上风平浪静,不意味着社会稳定。社会本身就处于一种运动变化之中,利益是多元化的。引导不同的利益集团理性表达,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价值研判了。从价值研判角度,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话语,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话语,探讨这样的问题,符号学尤其是话语理论、修辞理论,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对问题而言,其实不是哪个学科能够彻底解决的,需要多学科的视野,多学科的理论,多学科的方法。探讨中国转型社会的传播问题,不仅需要实证研究,也需要批判研究,还需要进行符号学的审视。当然,还有很多的学科都会发挥协同作战的作用。 何一杰:您一直对新媒体问题非常关注。网络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工具、方式、观念不断更迭变换,您觉得传播学应如何面对新媒体时代这种快速更迭的挑战? 董天策:现在的传媒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变革、转型过程中。新媒体是对信息集权的颠覆,网络是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以往能够控制的内容,现在控制不住了,我觉得这是和民主的历史洪流合拍的。很多人觉得,这样不就天下大乱了吗,所以总是思考怎么去管,怎么去占领阵地。但是我就要问,怎么管得住呢?难道我们要回到清王朝,要闭关锁国吗?不可能嘛。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固然要注重技术方面,但根本问题还是要更新我们的观念。一些根本的观念弄不清楚,很多东西我们肯定是做无用功。我们应当引导新媒体进行更理性、更健康的表达,但决不能不允许人们说话。新媒体并非洪水猛兽,我们把它想象得很可怕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敌我思维在作怪。在我看来,新媒体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觉得不要天天跟学生讲什么新媒体的冲击啊、危机啊。危机固然包含了危险、风险,但也同时包含了机遇、机缘。当前这一波新媒体浪潮之后一定会诞生新的媒体形态,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再怎么变,人类社会始终都需要新闻,而且越是高速发展,对新闻越是充满渴求。现在做调查性、分析性、解读性报道的记者都从传统媒体走得差不多了。但社会需要事实,需要真相,如果说传统媒体不作调查报道了,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别的媒体去干这个事。对我们而言,新媒体现在是“破”,但“破”过之后“立”起来的一定是新的东西,一定与我们原来的东西不一样。原来的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应该真正地改革,哪些应当坚守,哪些应当扬弃,这才是我们要研究的大问题。 何一杰:您曾说,您的教学与研究始终处于“漫游”状态:不仅在新闻与传播之间漫游,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漫游。您认为在这个传媒大变革的时代,理论与实践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董天策:教学与研究在新闻与传播之间漫游,一半是无奈,一半是自觉。说无奈,是因为工作的需要让我漫游在新闻与传播之间;说自觉,是因为我觉得拓宽学科视野对于研究很有好处。譬如我对“新闻策划”的研究,由于之前有传播学、公共关系方面的积累,就能够从公关与新闻的互动来加以审视,从而澄清似是而非的认识,得出比较符合实际而又比较科学的结论。当然,学术漫游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学术研究不够专精,缺乏深度,所以我早就想收缩战线,在某些领域深深扎根,弄点有深度的东西。然而,由于这些年在当院长——学术的生产队长,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着眼整个学院的学科布局,不得不在若干领域去鼓捣,去动员,去热热场子,这也是一种无奈。 至于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漫游,基本上是我一以贯之的取向。在我看来,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种实践性、应用性学科,一定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传媒大变革的时代,实践探索往往走在理论的前面,理论思考似乎总是在追赶实践。但我想,如果总是这样,理论就太灰色了。传媒大变革需要大理论,但大理论的提出不仅需要敏锐的眼光,创新的勇气,而且需要深厚的学养,需要高瞻远瞩。我们做研究的,一定要比业界的人站得高看得远,别总跟着他们跑。现在很多人做研究,往往停留在对现象经验的描述上。早些年讲三网融合,现在又叫媒体融合,老师一天到晚讲这些,最后学生没学到什么,媒体融合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面对急剧的变化,一个真正的学者既要观察最新的变化,也要跟它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进行独立的审视,进行理论的分析判断。另一方面,很多学术的理论脉络我们还没理清楚。不少研究者匆忙上阵,似懂非懂,似是而非,教出来的学生更是似是而非,这样的学生太多了。理论脉络太空疏,我们就没有根基。同时又很着急,很浮躁,总想拿两个新名词新概念去贴狗皮膏药。贴上去,不管用,越不管用心越慌,这就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理论要关照现实,但关照现实不等于我们完全认同现实,要有所分析,有所批判,这样才能有所建构。要做好这个工作,需要真正在学术史、思想史、理论脉络和研究传统上下些功夫,然后聚焦现实问题,开展独立而深入的研究,才能有真知灼见。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何一杰:听您一席话实在受益匪浅,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相信在您的严谨治学与严肃育人之下,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必将纷呈精彩!
延伸阅读
董天策:《传播学导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董天策:《新闻传播学论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董天策:《中国报业的产业化运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董天策:《网络新闻传播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董天策:《消费时代与中国传媒文化的嬗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董天策:《问题与学理:新闻传播论稿》,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 董天策:《新闻·公关·广告之互动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董天策:《公关理论导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 董天策:《仁智的乐趣:山水泉石》,北京:文津出版社,2013年。 本文刊载自《传播符号学访谈录——新媒体语境下的对话》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 (本期编辑:要鑫)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