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汉学家:传统中国,在军事艺术方面几乎没有可供胜利者学习的地方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记载查士丁尼事迹的史书有哪些 › 西方汉学家:传统中国,在军事艺术方面几乎没有可供胜利者学习的地方 |
西方汉学家:传统中国,在军事艺术方面几乎没有可供胜利者学习的地方
|
过去的中国军事史研究,多专注于军事制度史和探讨考证一场战役的起因、过程和影响。事实上,军队能够运用武力手段改变政治、社会现状;社会变迁与政治决定也会改变军事制度。国家、社会与军事制度三者是贯通的、相互发生作用的。 《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300—900》作者大卫·格拉夫是知名的中国军事史研究专家。在本书中,他把战争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下,将军事制度、战争形态与当时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情况联系起来,既纵观各时代的演变,亦横向地观察当时各范畴的相互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多面向的视野,展现的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互动的军事战争史,由此更深刻地揭示了引发统一与分裂的内在动因。 本文选摘自《中古时期的战争:300—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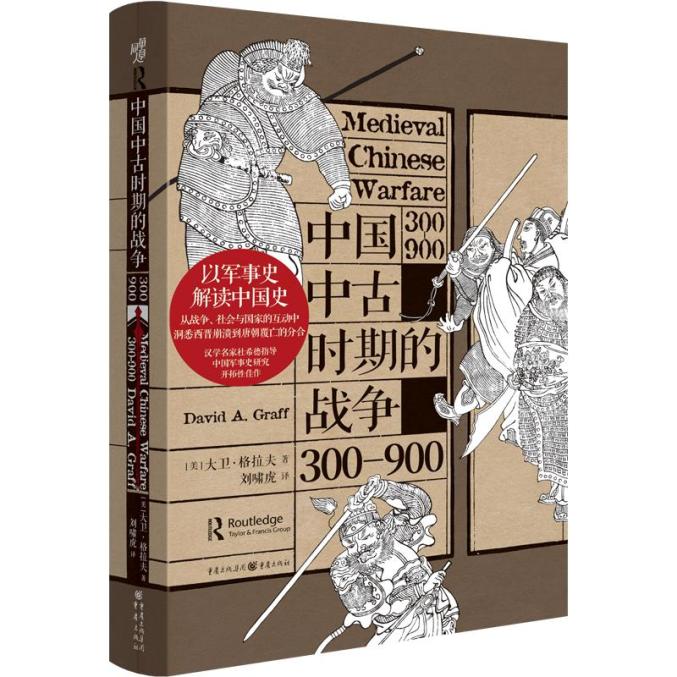 作者: [美]大卫·格拉夫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 华章同人 书系:华章大历史 译者: 刘啸虎 出版年: 2023-11 用西方语言撰写的中国军事史著作并不多。很少有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对军事兴趣浓厚,而军事历史学家又极少关注中国。军事史的总体研究大多遵循半个世纪前富勒(J.F.C.Fuller)写的《西方世界军事史》(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的思路,这些研究明确局限于“西方世界”(通常定义为欧洲、近东和欧洲殖民地)。即使是那些试图撰写一部更具全球性的军事史的学者,如《战争史》(History of Warfare,1993年)的作者约翰·基根(John Keegan),也往往对古代中国不屑一顾,反正长期以来他们对亚洲的战争方式抱有成见。 公允而言,学者从事概括性的总体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缺乏大量英文和其他西方语言专业文献的限制。这种忽视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从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西方汉学就习惯于审视一个军事力量弱小、军事技术落后的传统中国,这个中国是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幸受害者。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在西方汉学家看来(当然是偏见),传统中国似乎是一个长期的失败者,在军事艺术方面几乎没有可供胜利者学习的地方。 西方学者对中国军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其一是当代军事分析和对近期冲突的研究。其二是研究战国时期(公元前453—公元前221年)的军事经典,尤其是《孙子兵法》。自1772年钱德明神父(Père Amiot)翻译的第一个法文译本出版以来,《孙子兵法》十三篇已被翻译成多种西方语言。20世纪初,卡尔斯罗普上尉(Captain Calthrop)和翟林奈(Lionel Giles)开始致力于《孙子兵法》英文版本的翻译。目前至少有六个竞争版本出版。市场对此似乎永不满足。这种流行,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文本本身的深刻性,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孙子的军事思想在其他时代、地点和活动领域的适应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东方智慧书”的广泛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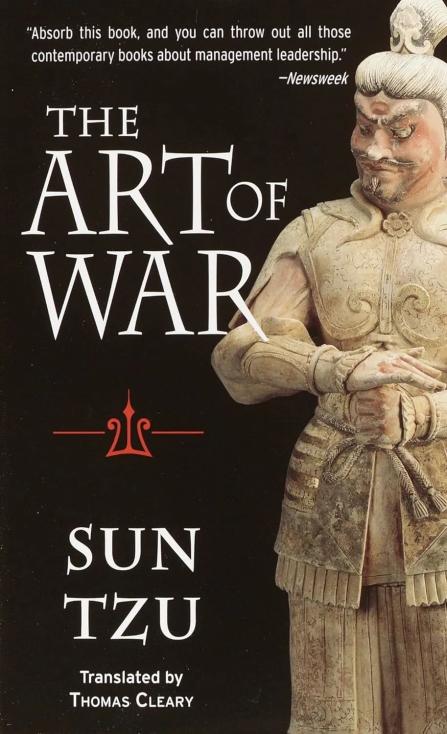 《孙子兵法》英译版 由Harper Press出版 然而,重视早期经典和近期冲突的研究,使得中国军事史的大部分仍有待探索。在近一代人的时间里,由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和小弗兰克·A.基尔曼(Frank A. Kierman,Jr.)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古代中国的战争之道》(Chinese Ways in Warfare)仍然是关于“帝制中国”(即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用兵作战和军事实践最重要的英文著作。那些希望对中国军事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只得去查找晦涩难懂的专著、未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零散的文章、非军事史书籍中的单独章节以及各种外文著作。在帝制中国的广义时间框架内,有关从220年汉朝灭亡到960年宋朝建立这一时期的军事史著作尤其少。也许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华世界充满动荡和分裂,与那些国力强盛、开疆拓土的朝代相比,很难引起军事历史学家的关注。 现代的中文二手文献当然要广泛得多,但质量参差不齐。学术成果最多的领域当数军事制度研究。军事制度研究是范围更广的中国制度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中期由学者官员杜佑编纂的《通典》——的一个子领域。关于中国历史上特定时期的军事编制、军人征募流程和服役期限,已经有大量详细的研究。依据现存的档案文书、史书记载和文学文本而进行的细致研究,所形成的著述可能会让非专业人士望而生畏。 与军事制度史相比,战争史相对较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诚然,关于前现代时期的军事史,我们有大量多卷本的史书,比如由中国台湾“三军联合参谋大学”主编、1967年于台北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历代战争史》,以及1998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于北京出版的二十卷本《中国军事通史》。不过,这些著作和其他类似的著作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些著作一般由编委会而非个人撰写,通常只是对传统的断代史叙述进行转述,很少进行考据校勘、严格论证和打破窠臼的质疑。像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约翰·基根等富有创新精神的西方实践者那样,为历时两千余年的帝制中国撰写军事史,几乎没有人用任何一种语言尝试过。 本书的目标远没有那么宏大。它并非意在彻底改变中国军事史的书写,而是试着弥合中西语言文献在描述从西晋崩毁到唐朝灭亡的六个世纪里战争、国家和社会相互关系方面的巨大鸿沟。这项研究以对军政大事相当直接的叙述为基础,按照年代顺序编排章节。在这一基本框架内,笔者会在适当的地方穿插介绍军事制度、社会和政治结构以及战争手段的发展变化。本书的目的即在于阐明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军事制度和社会变革之间的某些最重要的联系。 将“中古”(medieval)一词用于中国历史时,我们需要做一些解释。有中国历史学者广泛使用(但远非普遍使用)在前,笔者选择4世纪初和西晋灭亡作为中国中古时期的开端。彼时,秦始皇在五个多世纪前建立的大一统帝国最终崩溃,并迅速陷入动荡和分裂,而这一状态持续了近两百年。显而易见,当时中国与大致同时期的欧洲和地中海世界平行发展。笔者将在下一章中就这一点进行更详细的探讨。中国中古时期的终结则不甚明显。为进行这一特定的研究——并将本书控制在合理的篇幅之内——笔者选择沿用日本汉学先驱内藤湖南的观点,将中古时期的结束时间定在唐朝(618—907年)末期。读者应该意识到,其他学者〔如傅海波(Herbert Franke)〕有时也会将“中古”的称谓加诸宋朝(960—1279年)和元朝(1206—1368年)。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本书所论及的“中国”并非一个单一的帝制国家,而是东亚一片广阔的次大陆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极具多样性。其内部区域——“汉地中原”——人口规模最大且最为密集。该区域包括华北平原、渭水流域、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以南的各江河流域。这里的人口大多是定居的农民,从语言、文化传统和自我认同上来说,他们皆为汉人。但是,许多山区居住着不同的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习俗和族群认同。还有一些民族居住在外围边疆,包括蒙古地区和准噶尔地区的干旱草原、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东北地区的森林和青藏高原的高山沙漠。这些民族大多并不从事农耕,而是从事渔猎和畜牧,有些(尤其是草原居民)完全是游牧民族。外围区域一般不适合汉人农民定居和开发,与之相反的方向却出现了大规模的迁徙,尤其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的前半段。来自外围区域的“胡人”大量定居中国北方。直到581年,北方各政权的所有统治者基本皆为胡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族与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通婚,采用汉人的服饰和习俗,从而渐渐失去了他们独立的民族和语言特征。但是,这一过程绝不是单向的。也有汉人军户迁往北方边塞,接受“胡人”同袍的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例子。中古时期中国民族认同的可塑性,将是本书反复谈及的一个主题。 本书所呈现的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图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可用史料性质的影响。有关这一课题,真正的“原始史料”极少,而“原始史料”包括中国干旱的西北地区敦煌和吐鲁番出土的抄本中少量的一手官府文书(如差科簿)、专述典章制度的政书、几部重要的唐代兵书以及收入类书和文集(大多为宋朝编纂)的一些诏敕和奏疏。但在通常情况下,本书必须主要依赖于涵盖300—900年的“正统”断代史,包括《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尽管依据前朝的档案文献,但这些史书大多修撰于唐朝初年。《旧唐书》直到10世纪中叶才编修完成,《新唐书》更是到11世纪下半叶才编成。与这一时期相关的另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即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成书于11世纪晚期。《资治通鉴》本是私修,后来得到朝廷支持。除《资治通鉴》之外,上述所有史书都是在国家主持下,由士大夫修撰而成的。出仕而以此为职志者,供职于史馆或其他几个曾负责编纂官方正史的机构之一。所有这些史书都经历了漫长的编修删改,没有一部史书可以真正被称为原始史料。 鉴于我们对中国中古时期战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史官,因此有必要弄清楚史官的史料来源于何处,史官如何处理史料,以及史官可能在叙述中加入了哪些偏见、歪曲了哪些史实。唐代的史官在描述用兵作战时,理论上应该能够利用非常广泛的原始材料,这些原始材料不仅包括一手的文书档案,如檄文布告、信札尺牍、奏疏表章、各种军情记录和往来通信,以及授官、封赏和大赦的诏敕,还包括在一些旧战场立碑记功的碑刻文字、见证者和参与者的直接证词、纪念开国皇帝赫赫武功的宫廷乐舞,甚至还有名将统兵布阵的战阵图。史官使用了这些史料中的一部分,尤其看重史料的纪实性。大量的诏敕、奏疏、檄文和信札都以节略形式被收入史书。涉及特定战事的细节时,最重要的史料或为前方将领向朝廷发出的“露布”,或为“行状”,即已故高官(包括将领)的亲属和门生故吏上呈朝廷的逝者传记。 “露布”通常会记录交战的时间、日期和地点,以及估计的敌军规模、敌军将帅的姓名(至少是部分官军将领的姓名)、作为总体作战计划的一部分而由众将各自领受的任务,有时还会列出众将麾下的兵力。这些文书基本不记载交战的细节,但详细记录了斩获敌军的人数。从存世的少数样本来看,“露布”是一种相当片面的文书。它虽然将敌人的损失记录得非常详细,但基本不提己方官军的伤亡,除非伤亡奇迹般极少。肯定也有向朝廷告败的制度,但此类文书似乎没有存世。这显示奏报制度存在根本的偏见。告捷的将领有望厚加封赏,告败的将领则将面临严厉责罚,如此一来将领自然会强烈倾向于上报积极的一面。有的将领,如隋朝的杨素和8世纪中叶的高仙芝,要求自己的幕僚在奏报时必须对事实巧言粉饰。有的将领则习惯于冒功报捷,将小胜谎报为大胜,败仗谎报为胜仗——即使谎报者一经发现即遭惩处。此等行径在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期尤为盛行,因为唐玄宗尤喜边功。  《中国中古时期的战争》目录 将领的“行状”也可以为其贴金。因为行状通常是由逝者的亲属或门生故吏撰写,而非吏部考功司的官员撰写。且行状往往与慎终追远的随葬墓志非常相似。两者都会以最有利的方式呈现主题,突出逝者的功绩,隐去逝者的败绩。有时两者会未经核实或审校,被不堪修史重负的史官直接采用为列传之底本。 将领及其亲友把大量纯属杜撰、真伪参半以及歪曲失实之事掺入史料,使之长存。除此之外,史官还将自己特有的成见和偏见带入对战争的描述中。撰写过中国军事史的西方汉学家抱怨,传统的中国战史记载很少提供有关战事情况或细节的信息。例如傅海波指出,即使是征战大事,史官也往往用最简洁的措辞来描述:“‘X军败于Y’,‘Z城克(或不克)’——这是通常的记载。”在中古时期的中国,统兵作战者、司职撰文奏报者与编修战史者基本上是脱节的。虽然未必不通文墨,但中国中古时期统兵作战者的文学才能和兴趣有限。官修史书的编写固然为“文官系统中的士人精英”所独占,但这些人在朝廷史官和谏官之间来回迁转,很少到藩镇任要职,遑论统兵作战了。 由于对战争的具体细节知之甚少或不感兴趣,加之史料来源中细节极少,这些士人出身的史官可能更乐意借用前代史书的模式套路来描述当时的出兵作战。他们反复使用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和与战斗有关的典故来描述作战,而非试图对事件进行精准的再现。在提供细节时,他们通常更关注奇谋妙计或战役中独特而鲜明的特征。 史官出身的士人精英不仅对军事的具体细节不熟悉,而且往往对战争和军事充满敌意。士人重文轻武,认为动武是“一种不可取的选择,基本是承认失败”。他们极力限制和削弱武官在朝廷中的权力与影响力,有时还反对大举出兵征伐域外。文化上的重文轻武,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早期。还有一种悠久的文学传统在很早之前便已形成,王靖献(杨牧)教授称之为“对战争的省略”。在中国诗歌中,“战斗,真正的兵戈相向,从来不被提及……这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而使有关英雄事迹的诗歌无法发展成为对战斗的详细叙述”。由此看来,这一传统同样适用于军情奏报和史官编写的战史。“露布”重点突出谋划部署和战果斩获,而非战事本身。正史中的战史记载一般也侧重于战前的运筹帷幄和战后的复盘详解。 文人偏见左右正史,不仅仅是删改史实的问题,而且可能严重歪曲中古时期中国战争的史料来源。史书中常有将领引用《孙子兵法》和其他古代兵书来证明和解释自己的决策。但这样的史料是否确凿可信?与武人相比,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可能更熟悉这种书本知识。在士大夫起草的奏疏和其他文书中,撰写者经常会引用兵书。他们已经习惯于引用儒家经典来支持自己的政策立场并攻击对手。史官选择运用想象力把军事决策的图景描述得更为详细,而不是用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严格论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史官有意刻画一种基于文本权威的论证模式。也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熟读兵书是克敌制胜之关键,非常适合制衡武人。这意味着没有武艺、毫无军旅经验的士人可以成功执掌天下兵权。 中国传统史家对待军事史的另一个方面,即对数字的处理,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质疑。熟悉中世纪欧洲和拜占庭军事史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中给出的许多军队规模都令人难以置信。现代历史学者一直认为中世纪编年史的作者所描述的军队兵力存在水分。为证明这一点,他们有时是通过挖掘更可靠的文献史料,有时则是通过指出不能忽视的时间和空间限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即使在6世纪上半叶查士丁尼王朝的扩张时期,拜占庭的野战军也不过两万五千人,且实际规模通常要小得多。 中国现代历史学者也对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军队规模(以及大多数其他数字)提出了类似的质疑。杨联陞在《中国经济史上的数词与量词》一文中指出,“军官们多报兵员的数目,并且夸张他们的军功,都是公开的秘密”。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则发现了文本证据:三国时期(220—280年)的将领报捷时,把敌人的伤亡人数乘以十报上去是惯常做法。现代中国史学者李则芬(李曾是一名军官)断言,古代史家撰写史书时持纯粹的文学态度,缺乏常识,根本不曾试着记录准确的数字。 这种批评并非完全公允。诚然,中国断代史的编修者及其所依据的原始史料的编纂者很少有实际的军旅经验,但这些人也是正常运转的官僚体制中的成员。这个官僚体制保存了大量的记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即使甚少收到全功),以编制和维持人口、税收、国家支出、官粮供给、兵员以及皇家牧场中的马匹等领域(在此仅列举数个令人关注的领域)的准确数字。中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史家司马光对数字从不轻信。遇到史料中有关军队规模的记载自相矛盾时,司马光几乎总是选择较小的数字。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将中国古代史书中给出的所有数字统统视为虚妄。夸大官军的规模,与夸大杀伤敌军的数字,动机恐怕并不相同。考虑到中国人口和行政资源众多,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其他传统史书中记载的绝大多数中国军队规模似乎并非不可信。史书记载的军队规模大多不到五万人。极为庞大和模糊的数字(如“数万”“百万”)一般与叛军或异族(通常是游牧民族)有关。中国史家没有可靠的文献来源可供使用,因此让想象力信马由缰。 中国中古时期的军队规模到底有多大?从我们所掌握的非常有限的史料来看,最佳答案是:通常比传统史家记载的数字要小,但一般不会小太多。如史载官军的野战军团兵力不足五万,这样的记载完全可以采信。这样的军队规模在那一时期是最为常见的。唐初将领李靖在其兵法论著中以两万人的兵力作为行军的典型范例,这或许并非偶然。出于各种原因,一些更大的数字固然可疑,但鉴于中国极为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行政资源,十万人或更多人的军队也并非绝不可能(据史书记载,西汉末年,帝国人口超过五千七百万;隋朝为四千六百万;742年唐朝鼎盛时期,帝国人口略低于四千九百万)。然而,我们应该知道,这种规模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此庞大的军队,转移、补给和指挥时会显得极其笨拙,除非兵分数路,但分兵之后又难以由一个单独的指挥中心进行有效的协调。只有作战部队的兵力数字大到不合情理,后世史家才应断然不予采信。如果史载这样的兵力基本准确无误,那么这个数字肯定不是指在同一个战场上一道行军、扎营和作战的某支军队的兵力,而是在广阔区域内作战的数路独立军队的总和。 原标题:《西方汉学家:传统中国,在军事艺术方面几乎没有可供胜利者学习的地方》 阅读原文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