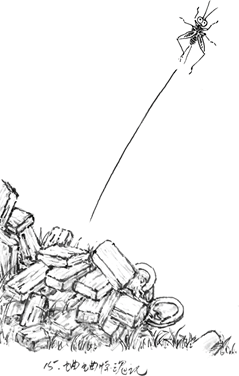那些虫子们争先恐后的,像精灵老师丨春分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萤火草在哪里找 › 那些虫子们争先恐后的,像精灵老师丨春分 |
那些虫子们争先恐后的,像精灵老师丨春分
|
是的,后来,我爱上了读书,在读书中知道,地球上的虫子太多了,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的是两亿只! 为了写出这两亿只小虫子,我又爱上了写作。 但我一直没有写出我的小虫子。 我需要继续阅读,阅读更多的书,比如《昆虫记》,我需要一把钥匙把我的生命打开。 果真,到了2022年,我写出了这一批小虫子。就是这些白纸黑字的“小虫子”。等待好久了。从童年到中年。但好饭不怕晚啊,我很担心我的文字比不上那些既老实又狡黠的小虫子们。 如果要说《小虫子》的写作收获,我想了想,应该有三点: 第一,生活奖赏的是有心人,你要学会挖掘与你生命有关的素材。 第二,每个人都不是天才的写作者,要学会挖掘,就得学会反复的自我训练。 第三,写出好作品,需要大量的阅读,比如我读了好多年的《昆虫记》,我就写出了属于我自己的,一个苦孩子的《昆虫记》。 所以,一起加油吧,这个世上爱虫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昆虫记》呢!
《小虫子》插图,邵展图 绘 蚕宝宝批斗会 蚕宝宝是母亲的叫法。 蚕宝宝也是虫子。长得和袋蛾差不多,也和袋蛾一样会吐丝结茧的虫子。 母亲从来不允许他叫它们是虫子,而应该叫它们“蚕宝宝”。母亲说,如果叫它们虫子的话,它们会不高兴的。不高兴的后果,就赌气不肯吐丝了呢。 他很熟悉母亲说这种话的口气。 这就是用“甜话”哄小孩呢。 他也不叫它们是虫子,也不跟着母亲叫它们是“蚕宝宝”。 他心里早就有属于他的叫法:宝宝。 “宝宝”这个词,只属于他呢。 “脸皮真厚呢,宝宝长,宝宝短,好像你真有宝宝了。” 无论母亲怎么嘲笑他,他也没改口,依旧是“宝宝”“宝宝”地叫。 他不是说“甜话”呢。 “宝宝”就的确是他的“宝宝”。它们怎能不是他的“宝宝”呢?根本就不用怀疑,他就是这些“宝宝”们的母亲,他就是这些“宝宝”们的父亲。 刚刚来到他家的宝宝们不像是宝宝,而像一群小小的“芝麻点”,密密麻麻地粘在半张蚕纸上。 “芝麻点”们一动不动。 母亲给他做了个示范。含一口水,等会,让水有温度了,再均匀喷在有“芝麻点”的身上,把睡觉的小宝宝们“唤”醒。 他太紧张了,还没来得及喷到“芝麻点”的身上,竟把含在嘴巴里的水咽下去了。 第二口水喷到了“芝麻点”的身上了。 母亲看了看,喷得还算均匀,可以了。 他看了又看,母亲说蚕宝宝不会这么快醒过来,要放在有太阳的地方晒三天呢。 他很担心因为自己粗手粗脚,“唤”得不均匀,有些“宝宝”被大水淹死了。 这可是他在这个春天的“责任田”呢。 为了防止他呆看,母亲逼着他去把两张竹筛拿到河边刷干净,说这可是蚕宝宝们要睡的床呢。 旧竹筛被他刷得像新竹筛一样。 想不到母亲又指着墙角一张大圆柳匾,让他顶着去河边刷干净。 比桌子还大的圆柳匾可比竹筛难刷多了。他不觉得难刷。 实在太神奇了,那么小小的蚕纸,上面的“宝宝”能睡这么大的床?两张竹筛和一张圆柳匾加起来,比他睡的床还大呢! 洗竹筛和圆柳匾让他洗得全身湿透,母亲担心他受寒,命令他又在太阳下晒晒。 清明节前的春风是暖和和的,阳光也是暖和和的。 和未醒过来的“宝宝”们一起在阳光下晒,他也想打瞌睡了,但又不敢睡过去。 万一在他打瞌睡的时候,那些宝宝醒过来了呢。 母亲说没有这么快。 万一呢。 在半睡半醒之间,他梦见了白花花的“宝宝”们爬满了院子里的竹筛和圆柳匾。 蚕纸是在第三天早上有变化的。 有一小部分,隐隐的黑芝麻样的东西出现在蚕纸上:蚕纸上有“霉”斑了! 他惊叫起来,把正准备喂猪的母亲吓了一跳。 哪里是长“霉”斑了,这是蚕宝宝“醒”了。 无论怎么看,也不像是蚕宝宝啊。 它们太像黑丝线头了。不仅像黑丝线头,还像蠕动的小蚂蚁。一点也不是想象中的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你生下来,比它们还丑呢。” 无论多么丑,也还是他的“宝宝”呢。 “醒”过来的宝宝似乎也认定了他,一律朝着他这个方向蠕动,像是都要挤到他的目光里争宠呢。 “蚕宝宝饿了!” 母亲的话他既惊恐又惊喜。惊恐的是,这么小的“宝宝”,它们的嘴巴在哪里呢?惊喜的是,这么小的“宝宝”竟然懂得要吃了。 他赶紧找到一棵桑树,连摘了几个桑叶枝头的细叶芯。再跑到“宝宝”们面前,一点一点撕碎。 母亲说这是蚕宝宝们的口粮。 嫩桑叶口粮被他撕得很细,他生怕把这些刚出世的“宝宝”们噎着了。 “蚕宝宝和你当初一个样呢。” 母亲似乎很感慨,说了他刚刚生下来的许多说不上嘴的丑事。 他一点也不想听,也听不进去。 “这样的吃法要把我们家吃穷了呢。” 这句话他听进去了。 他拍着胸脯让母亲放心:放心,有他这个爬树高手呢。 他说前半句话时很响亮,后半句是压低了嗓门说的。 他生怕把那些正在吃桑叶的“宝宝”们吓着了。 “宝宝”们吃得并不快,“宝宝”们的牙齿可能还没长全呢。真的吃不穷的。 “宝宝”的胃口实在是好,吃,吃,吃…… 都吃了一天了,他站在竹筛边也看了一天。 到了晚上,“宝宝”们还没有睡觉的意思。 天啦,难道“宝宝”们想不到睡觉吗? 母亲说蚕宝宝会睡觉的,只不过还没到吃饱的时候。 第二天,“黑丝线”们变粗了些,有点像小黑蚂蚁了,只是缺少了小黑蚂蚁的黑亮。 第四天早上出来的,那些“小黑蚂蚁”们一动不动了。 他的魂都吓掉了:肯定是采摘到了打了农药的桑叶! 把他的“宝宝”们全毒死了! 还是母亲有经验,说这叫“打眠”:蚕宝宝吃饱了,要睡觉了,睡完觉就会蜕皮换衣服了! 他吓掉的魂又慢慢回到了他的身上。 后来每次采摘桑叶的时候,他怕桑叶被人家打了农药,他都要先嚼下去一片叶子的。 桑叶的味道有一点点清香,也有一点点苦涩。 他和他的“宝宝”们吃的都是一样呢。 “宝宝”们再次蠕动起来,不再是“黑丝线”了,蜕去了黑色的皮,变白了,变胖了,有些像胖娃娃的样子了。 胖娃娃的胃口又大了起来。 “宝宝”们大了,就得分家。 是母亲和他一起分家的。 母亲和他一起把“宝宝们”分放到早准备好的竹筛中,口粮当然也是分放的。 “宝宝”们以更好的胃口表达了它们对新家的喜爱。 又鲜又嫩的口粮消失得很快。 母亲喜欢看蚕宝宝吃桑叶口粮的样子。 “活像老害吃饭的样子,都是狼吞虎咽的,都生怕别人抢去呢。” 他的胃口也跟着“宝宝”们一起大了起来。 每次吃完第一碗之后,他都有想去锅里盛第二碗的冲动。 但他没去盛饭,母亲吃得比他还要少呢。 放下饭碗的他得赶紧继续去找桑树。 村里不止一个人家在养蚕,每只蚕宝宝都要吃桑叶,但他采摘的桑叶无疑是最多的。他知道整个庄前庄后的每棵桑树分布地图,当然也知道哪棵桑葚最甜,哪棵树上的桑叶好吃。 “宝宝”们也喜欢他采摘的桑叶,吃,吃,吃…… 沙沙沙的声音,像在下小雨,又不像在下小雨。 他喜欢这沙沙沙的声音。 后来,他实在太困了,拣了一张最大的桑叶盖在那些“宝宝”们的身上。 到了早上,“宝宝”们把桑叶被子给吃掉了。 他去采桑叶的积极性更高了,每天都旋风般拎着蛇皮口袋出门,然后再旋风般回来。回来的时候,蛇皮口袋里全是“宝宝”们的桑叶口粮,还有他特地去更高的地方采摘的最大两枚桑叶。这是“宝宝”们每天的桑叶被子。 每天早上,毫无例外,桑叶被子都被“宝宝”们吃掉了。 “宝宝”们每天一个样,添加桑叶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必须每天出去采摘两次桑叶。 每天负责给“宝宝们”清理蚕砂的母亲说,蚕宝宝的头又昂起来了,一旦它们的头昂起来,就是要“打眠”换衣服了。 蚕宝宝每“打眠”一次,就代表长了一岁。 四五天就一岁。 又四五天一岁…… 他掰起指头算了算,按照这个速度,到了过年,“宝宝”们就不再是他的“宝宝”了,会比他大许多岁,比父亲和母亲的岁数还要大呢。 第三次“打眠”之后,“宝宝”们的口粮慢慢紧张起来。 “宝宝”们长大了,两张竹筛早已睡不下了,它们早被分家到了那张圆柳匾上了。嘴巴变多了,变大了。 原来是“一间房子一间灶”,现在是“三间房子三间灶”。 桑树长叶子的速度跟不上“宝宝”们的嘴巴了。 沙沙沙,沙沙沙,“宝宝”们在吃食,过去像下小雨像刮微风,现在像下暴雨像刮狂风。他的“宝宝”们要吃,其他人家的“宝宝”们也要吃。大家都在比赛爬桑树。 本村的桑树都快被他和那些小伙伴们撸成了光头。 他越走越远。 他现在会趁着有月亮的晚上出去弄。 有次回来,他的脸上多了几道新鲜的伤疤,母亲问怎么回事,他说是桑树的枝头回弹过来弄出来的伤疤。 很多时候,采摘回来,只是在水缸里舀上一葫芦水,咕噜咕噜喝下去,就迫不及待地把桑叶扔给“宝宝”们了。 他根本管不得自己肚子饿了。 他说看“宝宝”们吃桑叶口粮,看着看着就看饱了。 “宝宝”们的胃口实在太好了,桑叶丢下去,不管这是桑叶口粮还是桑叶被子。它们吃得理直气壮,吃得心安理得,一会儿,桑叶就被啃出了大缺口,再过一会儿,一片桑叶就剩下了空叶脉了。 桑叶的营养都到了“宝宝”们的肚子里了。 “宝宝”们在一伸一缩“打眠”蜕皮的时候,他特别担心“宝宝”们的力气。 对于有力气不大“蜕”不了的“宝宝”们,他会心疼半天。 “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才知报母恩。” 他有了做母亲做父亲的那种感觉。 “宝宝”们有了两寸多长的时候,父亲准备给“宝宝”们的“蚕山”了:草蜈蚣。 父亲向六指爷家借来了铡刀,从草垛上抽出去年秋天的糯米稻草。 这批糯米稻草是特地“藏”在草垛中间的,去年下了几场雪,糯米稻草还像去年那样新,那样有淡淡的糯米稻草的香味。 父亲是庄上堆草垛的高手,也是扎“草蜈蚣”的高手。 用铡刀把稻草们的头尾铡掉,留下中间一段,这将是“草蜈蚣”的爪子。 父亲大约估算了一下,编了两条长长的“草蜈蚣”。准备结茧的“宝宝”们将睡在“草蜈蚣”的很多草胳肢窝里结茧。 看着家里多出来的两条“草蜈蚣”,再看着依旧没心没肺在吃桑叶的“宝宝”们,他心中酸酸的。 母亲说,过不了多久,“宝宝”们就不再吃桑叶了。 那些秃了好多天的桑树们就可以好好长桑叶了。 “宝宝”们越来越胖了,一胖起来就懒,明明是那么鲜嫩的桑叶,它们尝了几口就不再吃了。 蚕宝宝真的快上“山”了! 他心里还是酸酸的。 准备上“山”的“宝宝”们是有信号的。 “马头”高高弓起,腹部颜色从白色变成黄色,然后慢慢透明起来。 母亲在两张筛子和圆柳匾里,找出头部弓起的“宝宝”们,小心地提起来,对着亮光照一下,如果腹部已完全透明了的,就把它捉到草蜈蚣的胳肢窝里。 这叫做“捉亮蚕”。 “宝宝”们几乎是同一批变“亮”的。 亮得他眼花缭乱,母亲和他手脚不停,花了两个晚上,才完成了“捉亮蚕”的工作。 他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宝宝”们都安睡在草蜈蚣的胳肢窝里了。 夜里,他睡不着。 眼泪流一脸。 抹了一脸,又一脸。 失去了“宝宝”吃桑叶的声音,家里静得很。 父亲和母亲在轻声说话,好像是在说某人的坏话呢。 …… “这个老三不愿意和别人说话。” “摆脸色。脾气变怪了,不喜欢叫人。” “采摘桑叶累了,喜欢甩脸色。” “没养蚕宝宝的时候,脾气还没有大起来。” “现在他的脾气大得很呢。” “也回嘴了,喉咙特别大。” “不能批评,会一蹦三尺高——地球背面的美国人都听到了。” “鞋子不提来走路,学做二流子,鞋子磨坏了,吃鞋子。” “裤子屁股后面老磨出洞,吃裤子。” “这个老三像癞蛤蟆,嘴大喉咙小。” “看看看,你们家老三把被子都哭潮了。被子哭湿了谁洗?还费肥皂呢。” “这么热的天裹被子,他难道也要上草蜈蚣吐丝吗?” “他从小就喜欢裹被子睡,还不让人碰他呢。” …… 他把自己裹得紧紧的,任凭父亲和母亲开他的批斗会,眼泪又咕噜咕噜流了出来。 后来他睡着了,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在这个长长的梦里,他不停地飞,从这棵桑树的枝头,飞跃到另一棵桑树的枝头上,一直飞跃到平原的最深处。
萤火虫,银簪子 很多虫子飞过去了,还会飞回来,就像他没捉得住的萤火虫。 那些没捉得住的萤火虫们虽然永远也不能将黑夜点亮,但它们还在坚持在黑夜里固执地闪烁。忽明忽暗,忽暗忽明,就像他的那些“鼻涕虎”“尿床宝”“大肉包子”这样的小名号。一个追赶另一个,有时候,前一盏灯熄灭了,后面的一个小名号又成为下一个萤火虫追逐的目标了。 后来,那些如萤火虫的小名号也消失在夏天里了。 逝去的人带走了他们的记忆,同样带走了他的那些小名号。 依旧活着的人已经衰老,他们也记不得他的小名号了。 他的大名覆盖了那些有特别痕迹的小名号。 但他对于他的那些好听的不好听的小名号,哪怕仅仅诞生过半天的小名号,都记得清清楚楚呢,还有母亲在夏夜里乘凉哼唱过的那个童谣。 那是他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母亲开口唱歌呢。 萤火虫, 夜夜红, 飞到西, 飞到东, 好像一盏小灯笼。 后来,他把有关写了这个童谣的文字给母亲看,母亲说她看不懂。然后他就回忆,说了很多话,还当着母亲的面把这首童谣唱完。 他没从回忆童年的温馨中走出来,母亲就噼里啪啦戗了他一顿,一口气列出了他两大罪状: 第一,胆大不孝顺,竟开她的玩笑。 第二,他读书读糊涂了,因为她从小到老,从来没有唱过歌,半句也没有。 母亲的怒戗,令他既羞愧又高兴。他长大之后,后来考上了大学,做了教书先生,母亲基本上就不戗他了。 但狠狠用话戗他的母亲才像是嫡亲的母亲啊。 童年时代的母亲,母亲的肚子里嘴巴里全是“火药库”,浓烈的“火药味”会让他迅速回到童年。 母亲给他唱童谣的那天,母亲已先后戗了他两次。 第一次是早饭后,他抱怨家里连一只鸭蛋都没有,母亲指着他的鼻子说: “我们家没有鸭蛋,你应该投胎到有鸭蛋的人家去。” 母亲以为他好吃,想吃咸鸭蛋,其实他根本不是想吃咸鸭蛋,他只是想一只完整的鸭蛋壳。 他没跟急脾气的母亲辩解,跟母亲辩解肯定会再被戗一次。 第二次被戗是在晚上,院子里特别冷清,他记不得家里人去哪里了,反正只剩下母亲和他两个人。外面也没有月亮,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正准备去点灯,母亲又开始戗他了。 “点灯干什么?吃饭又不会吃到鼻子里。” 对啊,吃饭当然不会吃掉鼻子里。 被戗了的他赶紧扒完了晚饭,迅速溜出去了。他有太重要的事要做,这几天,几乎全世界的萤火虫来他们村庄开大会了,到处都是亮闪闪的萤火虫。红背萤火虫。黄背萤火虫。还有很少见到的黑背萤火虫。 伙伴玩萤火虫的方法很多呢。可以把捉到的萤火虫屁股粘到眼边,两个眼睛就变得亮晶晶的。可以把萤火虫搓在两只手上,在黑暗中的两只手就是亮晶晶的。可以把萤火虫放在脚下一拖,这样在地上就出现了一条发光的线。谁画得长,谁就是冠军。 这几天最时髦的玩法是“鸭蛋灯笼”:萤火虫放到空鸭蛋壳里,然后把鸭蛋的空头反过来,屋子里就多了一盏“鸭蛋灯笼”。 偏偏他家里没有一只鸭蛋。 他还是找了一只半斤装的农药水瓶,把外面有骷髅头的标签洗掉了。 没有鸭蛋灯笼,做一只茶色的“玻璃灯笼”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等他抱着“玻璃灯笼”回到家,握着一把蒲扇的母亲还坐在黑暗中发呆。 母亲差点被他的“玻璃灯笼”闪晕了。 “你把它们放在农药瓶里?不会全毒死了吧?” 他说他洗了起码一百遍。 母亲笑了,“玻璃灯笼”照耀下的笑容特别好看。 “你不能把萤火虫放到帐子里啊,萤火虫会趁着你睡着了,钻到你的耳朵里吃脑子。你这人本来就笨,被萤火虫吃了脑子会更笨了。” 这个很迷信的说法,母亲说得特别认真。 她不太像那个总是戗人的母亲了。 过了一会,母亲可能还是很担心他把萤火虫放到蚊帐里,又说: “要不,你还是把它们全放掉了吧。” 母亲像是在求他。 他把“玻璃灯笼”的瓶盖拧开了。 没有一只萤火虫飞出来。 他凑近瓶子看了看,萤火虫们好像全昏过去了。 还是有农药味的。 他抱着“玻璃灯笼”摇了摇,还是没有一只萤火虫出来。 他使劲地摇瓶子,还是没有萤火虫出来。 母亲让他别摇了。 他一句话也没说,胳膊酸痛酸痛,心里更疼。他好像听到母亲心里在说:“看啦,小糊涂虫就是小糊涂虫!竟然用农药瓶装萤火虫!” 可能他本来就是犟脾气,他在继续摇晃。“玻璃灯笼”随着他的摇晃,原来有的荧光慢慢暗淡了下来。 他的心也在一点点暗下去。 突然,有只黄背萤火虫摇摇晃晃地飞在他们的眼前,他搞不清是他手中“玻璃灯笼”里出来的,还是刚刚从外面飞过来的。反正,这只黄背萤火虫实在太亮了,是他见过的最大最大的萤火虫,简直就像他们家里的一盏小月亮。 母亲也盯着这只萤火虫看。他不敢呼吸了。 萤火虫围着他转了一下,接着放过了他,飞向母亲那边…… 过了一会,萤火虫落到母亲的头上了! 天啦,实在太神奇了。 这只萤火虫像是母亲头上的“银簪子”! 母亲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头上有“光”闪烁。母亲没说话,他也没有说话,“银簪子”在闪烁。 他多想这只“银簪子”在母亲的头上多留一会儿,要不,就永远留在母亲的头上啊。 后来,这只美丽的“银簪子”还是飞走了。 萤火虫, 夜夜红, 飞到西, 飞到东, 好像一盏小灯笼。 很多虫子飞过去了,还会飞回来,就像他没有捉得住的萤火虫,就像母亲那天晚上说过的话唱过的童谣,至今还在他的记忆深处闪闪发亮。 现在他每年都会见到萤火虫的,每次见到萤火虫的时候,他就格外想念脾气暴躁说话很冲总是戗他的母亲。 “真像银簪子吗?你可不要哄我。” 过了会儿,母亲叹了口气,说:“你老子都没给我买过一个银簪子呢。” 摘自庞余亮《小虫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2月版 x 庞余亮 | 小虫子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点击跳转,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购买
稿件初审:孟小书 稿件复审:徐晨亮 稿件终审:李红强 点击上图查看新刊目录 《当代》微店 订阅《当代》: 1.《当代》邮发代号/2-161 2.《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邮发代号/80-194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