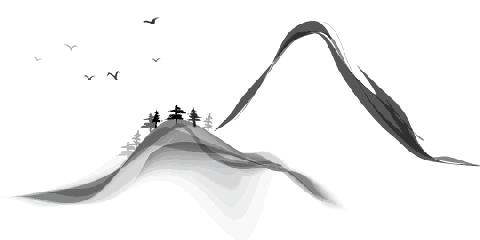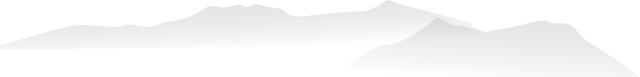梁涛丨中国哲学的新思考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荀子的著作主要有哪些 › 梁涛丨中国哲学的新思考 |
梁涛丨中国哲学的新思考
|
唐端正先生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为唐君毅先生的学生,《荀学探微》所收录的文章多发表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洗礼,这些成果不仅没有失去学术价值,反而益发显示出其重要性。由于唐先生的文章多发表于香港、台湾的杂志上,内地(大陆)读者检索不易,故我征得唐先生的同意后,将其有关荀学的论述整理成册,再次推荐、介绍给读者。我在梳理前人的荀学研究中,注意到港台地区的荀学研究似乎存在两条线索:一条以牟宗三先生的《荀学大略》为代表,认为荀子代表了儒家的客观精神,但存在“大本不正”“大源不足”的问题,其价值在于可以弥补孟子思想之不足。这一看法在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韦政通的《荀子与古代哲学》、蔡仁厚的《孔孟荀哲学》中得到进一步阐发,其最新论述可以台湾政治大学何淑静女士的《孟荀道德实践理论之研究》《荀子再探》为代表。作为牟先生的弟子,何教授在整体继承牟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深化。这条线索影响较大,代表了港台地区荀学研究的主流,故可称之为主线。另一条则以唐君毅先生为代表,不同于牟先生对荀子的贬斥,唐先生认为荀子言性恶,乃是针对道德文化理想而言,是用道德文化理想转化现实之人性,“荀子之所认识者,实较孟子为深切”。唐端正先生则注意到,《荀子·性恶篇》的主题,不只是性恶,还提到善伪。“我们与其说荀子是性恶论者,不如说他是善伪论者。”针对牟先生将荀子的心仅仅理解为认知心,唐端正先生则强调,荀子的心实际具有好善、知善、行善的功能,绝非能简单用认知心来概括。两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这条线索,影响虽然无法与前者相比,只能算是辅线,但在我看来,实际更值得关注。近些年我借助出土材料,提出荀子的人性主张实际是性恶心善说,即是对唐端正先生观点的进一步推进。我甚至认为,不断摆脱牟先生所代表的主线的影响,而对两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辅线做出继承和发展,可能是今后荀学研究的一个方向。这也是我向学界推荐、介绍唐端正先生旧作的原因和用心所在。
刘又铭教授是我研究荀子的同道,也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又铭兄在重孟轻荀的台湾学术界首次提出“新荀学”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极大反响。对于又铭兄的观点,我也有一个接受、认识的过程。又铭兄曾在《从“蕴谓”论荀子哲学潜在的性善观》一文中提出,“就深层义蕴而言,荀子的人性论其实仍可归为某一种(异于孟子)类型的性善观”。对此我曾不以为然,批评其没有摆脱传统认识的窠臼,仍是以性善为标准来评判荀子,为此不惜让荀子屈从于性善。现在看来,我之前的认识有误,又铭兄的努力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我近年提出荀子是性恶心善论者,虽不能说是受又铭兄的影响,但的确反映了自己思想认识上的转变。以往人们为性恶论辩护,主要是与西方基督教相类比,认为基督教可以讲性恶,荀子为何不可以讲性恶?荀子对儒学乃至中国文化的贡献恰恰在于其提出或揭示了性恶。但这种比附忽略了一点,即基督教是在有神论的背景下讲原罪、性恶的,人的罪(恶)正好衬托出神的善,故只有在神的恩典、救赎下,人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在基督教中,性恶与有神论是自洽的。但在中国文化中,由于理性早熟,人们逐渐放弃了对人格神的信仰,特别是到了荀子这里,天已经被自然化了,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讲性善,则肯定内在主体性;讲性恶,则突出外在权威、圣王。但在荀子那里,又不承认圣王与常人在人性上有什么差别,认为其同样是性恶的,这样,第一个圣人或圣王是如何出现的便成为无法解释的问题,其理论上是不自洽的。所以,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性恶论是“大本已坏”的判断并没有错,宋儒的错误在于忽略了荀子思想的复杂性,误以为荀子只讲性恶,不讲心善,忽略了荀子同样肯定人有内在道德主体性。为荀子辩护,不必非要肯定性恶的合理性,而应对荀子人性论的复杂性、全面性做出准确的梳理和解读。 又铭兄提倡“新荀学”,特别重视《荀子》这部经典,我则主张“统合孟荀”,提出“新四书”的构想,所以我们对荀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不同的,但这种分歧并不是截然对立、彼此排斥的。在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统合孟荀与道德重估”的会议上,曾有学者质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统合孟荀?难道不可以提倡孟学或荀学吗?我的回答是,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当然可以有新孟学、新荀学,但也可以有由统合孟荀而来的新儒学。在儒学的创新上,不妨百花齐放,各展所能,各施所长,至于结果,则留给历史去选择。 李存山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学者,曾长期负责《中国社会科学》的工作。十余年前,他辞去副总编辑的职务,回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哲研究室,专心从事学术研究。记得一次聊天时,李老师曾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出版专著了。我知道李老师在精心准备一部大作,而这部著作是关于范仲淹的。当时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出版不久,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李老师写出了《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指出余著忽略了范仲淹对宋初三先生的影响,同时提出,余英时先生把朱熹的时代称为“后王安石时代”并不恰当。与其称之为“后王安石时代”,毋宁称之为“后范仲淹时代”。当时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有一份内部刊物——《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由我具体负责,我将李老师的文章发表后,很快收到余英时先生的回信: 梁涛先生: 收到寄赠《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六辑,十分感谢。李存山先生大文兼评拙作,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很感谢他赐教的雅意,乞代为致意为幸。贵刊资讯丰富,对于同行的人是极有帮助的。特写此短札,以略表致谢之忱。 敬问 安好 余英时手上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九日 以往的宋明理学研究由于受哲学范式的影响,主要关注理气、心性等所谓道体的问题,余英时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理学家与以往的儒者一样,真正关心的仍是人间秩序的问题。他提出“内圣外王”连续体的概念,强调理学家不仅关注“内圣”,同时也关注“外王”,甚至认为“外王”的问题比“内圣”更重要。余先生主张对朱熹的研究要从“思想世界”回到“历史世界”,并视之为一场哥白尼式的倒转。但在我看来,似仍有一间之未达,主要是因为余先生采取了历史还原的方法,将“内圣”还原到“外王”,认为“内圣”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外王”的问题,但二者的关系如何,却往往语焉未详,未能说明理学家关于道体、形上学的讨论与现实政治之关系的问题。其实,宋明理学的主题应是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当时的学者一方面推阐天道性命以寻求礼乐刑政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锐意名教事业以作为天道性命之落实处,故理学家对道体或天道性命的讨论绝非空穴来风,做无谓的工作,而是从哲学、形上学的角度为现实政治寻找理论依据。对于理学家的思想恐怕要这样解读,今后的理学研究也需要在“思想世界”和“历史世界”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所以,在接到主编本套丛书的任务后,我立即与李存山老师联系,希望将他计划写作的《范仲淹与宋学精神》列入本套丛书。李老师谦称,只完成了几篇文章,编在一起只能算一本小书。但书的“大”“小”岂可用字数衡量?李存山老师强调范仲淹的重要性,认为其“明体达用之学”代表了宋学的精神和方向,相信李老师的这本书对今后的宋明理学研究会产生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杨泽波教授是著名的孟子研究专家,在孟子研究上用力颇深,他的《孟子性善论研究》是改革开放后孟子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完成孟子研究后,杨教授转而关注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哲学,积15年之力,出版了皇皇5大卷、240余万字的《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可谓是牟宗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杨教授的新著体大思精,对专业研究者来说,是必读的参考文献,但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起来则显得不便。故我与杨教授商议,将其著作压缩出一个简写本,这样就有了《走下神坛的牟宗三》一书,它虽只有10余万字,但更为概括、凝练,更便于读者理解杨教授的主要见解和观点。
杨泽波教授年长我10余岁,据他讲,当年曾经深受牟宗三的影响,是通过阅读牟先生的著作而走上儒学研究的学术道路的,而他现在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出对牟先生思想的反省和检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杨泽波教授身上,同样也存在于我们这些六零后学者身上,可以说反映了内地(大陆)儒学研究的基本趋势:从阅读牟先生等港台新儒家的著作开始接受和理解儒学的基本价值,又从反思牟先生等港台新儒家的学术观点开始尝试建构内地(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范式。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毕竟内地(大陆)学者与牟先生那一代学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故而问题意识、所思所想自然会有所不同。牟先生他们当年生活的港台社会,西风日盛,民族文化花果飘零,故其所要论证的是儒家文化仍然有不过时的恒常价值,这个他们认为是儒家的心性,同时他们深受五四时期科学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认为传统儒学的缺陷在于没有发展出科学和民主,所以他们对儒学的思考便集中在“老内圣”如何开出“新外王”、心性如何开出科学和民主的问题上。但这样一来,就在有意无意中将儒学自身的问题和逻辑打乱了。我多次强调,儒学的基本问题是仁与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在理学家那里又表现为天道性命与礼乐刑政的问题,今天讨论儒学仍不能回避儒学的这一基本问题,所以我们与其问儒学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和民主,不如问儒家的礼乐刑政为什么没有或如何完成现代转化。发展仁学、改造礼学,才是儒学发展的根本所在。牟先生由于受五四礼教吃人观念的影响,视礼学为儒家过时之糟粕,避之唯恐不及。这样,完整的儒学思想便被砍去一半,所缺的这一半只好用科学和民主来填补。但既然我们不要求基督教、佛教发展出科学和民主,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求儒学发展出科学和民主?似乎不如此便不具有合法性。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对儒学这一古老精神传统必要的尊重。而且,引发出另外一个后果:既然可以不顾及儒学的内在理路和逻辑,片面要求其适应所谓的科学和民主,那么反过来也可能促使人们以儒学独立性的名义反对民主,认为完整的儒学与民主恰恰是对立的、不相容的。这在当前学界竟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尤其为许多民间学者所信奉,不能不说与牟先生对儒学的片面理解有关。牟先生对荀子评价不高,对儒家的礼学传统重视不够,其实也反映了这一点。不过,虽然我们与牟先生在对儒学的具体理解上有所不同,但牟先生所强调的儒学需要经历现代转化则无疑是需要予以充分肯定的。2017年我在“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与启示”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提出“回到牟宗三——大陆新儒学的发展方向”,即是要突出、强调这一点。“回到”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回到追求儒学现代性的起点,以更尊重儒学的基本问题和内在理路的方式探讨儒学的现代转化。这应该是内地(大陆)新儒学既继承于港台新儒学,又不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内容和特点所在。牟先生曾自称“一生著述,古今无两”,是当代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和儒学大师,他的一些具体观点、主张,我们或许可以不同意,但绝不可以轻易绕过,今后新儒学的发展仍需要充分继承、吸收牟先生的研究成果,并有所突破和发展。杨泽波教授研究牟宗三儒学思想多年,对牟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都提出了独到的分析和看法,给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相信他这部新著,对于我们理解、消化牟宗三的儒学思想会产生积极的借鉴作用。 本套丛书收录的《新四书与新儒学》一书,是我近年关于重建新儒学的一些思考,包括新道统、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对孟子、荀子人性论的重新诠释,统合孟荀、创新儒学,以及自由儒学的建构,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新四书与新儒学》一书的内容只是我目前的一些思考,虽然奠定了我今后儒学建构的基本框架,但还有更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不断涌入我的头脑,使我每日都处在紧张的思考中,而要将其梳理清楚,还要补充大量的知识,付出辛勤的劳作。故该书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尝试,是我下一本更为系统、严谨的理论著作的预告。由于这个缘故,该书有意收录了一些非正式的学术论文,这些文章或是随笔、笔谈,或是发言的整理稿,对读者而言,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观点鲜明,使其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我目前的思考和想法。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将主编本套丛书的重任交付于我,使我有机会学习、了解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思考。我也要感谢各位责任编辑,由于你们的辛勤付出,本套丛书才得以如此快地呈现给每一位读者。 梁涛 2018年9月27日于世纪城时雨园
中国哲学新思丛书 已出版: 杨泽波《走下神坛的牟宗三》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镇,著作等身,代表着20世纪后半叶儒学的最高水准,在海内外有着重要影响。其思想涉猎广泛、艰深曲折,是一段时间以来儒学研究最困难的题目,没有之一,因而一部分人有将其神化的倾向。 《走下神坛的牟宗三》力图将牟宗三从神坛上请下来,作为一个哲学家,与之展开对话。本书分别从坎陷论、三系论、存有论、圆善论、合一论五个方面,扼要介绍牟宗三思想的主旨,汲取精华,指明缺陷,一同在哲学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即将出版: 刘又铭《一个当代的、大众的儒学——当代新荀学论纲》 唐端正《荀学探微》 梁涛《新四书与新儒学》 延伸阅读 2018年度学术套系图书回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