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只有“公共”而无“知识”,社会关怀不免于惺惺作态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波鸿大学全是中国人吗知乎 › 彭国翔:只有“公共”而无“知识”,社会关怀不免于惺惺作态 |
彭国翔:只有“公共”而无“知识”,社会关怀不免于惺惺作态
 学人简介:彭国翔,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兼任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会长以及多家国际学术期刊编委。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以及世界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与访问学人,荣获“2016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2009 年度贝塞尔研究奖”、“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等。著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2003,2005,2015)、《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2007,2019)、《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2009)、《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2012)、《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鈎沉》(2013,2015)、《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2013,2018,2019)、《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2016),以及中英文论文近百篇。 文 | 李怀宇,学人scholar受权转载 第一次和彭国翔先生见面是在北京大学。2012年12月14日,未名湖畔白雪皑皑,在彭国翔的研究室里,我们做了访谈。2015年再会时,他已转任浙江大学,我们在杭州吃饭谈天。2017年4月他到广州中山大学讲学时,我们又相聚吃传统粤菜,谈学林趣事。 彭国翔1969年11月生于江苏徐州。他的祖母同时受过传统与西式教育,七十岁时还可以背诵《大学》,并信奉佛教,对他的人生观有很大影响。彭国翔上初中时,帮祖母去书店买过《金刚经》和《心经》。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家人希望他学理,但他从小对理科兴趣不大,自己要学政治学,以为可以治国平天下。 1988年,彭国翔考入南京大学政治学系,大一时听过高华的课。他回忆道:“那时候高华还是年轻教师,我曾到他住的地方去过。当时他住在一个筒子楼里,就一间屋,没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门口摆着煤油炉子。这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因为我小时候在南京上过幼儿园和三年小学,当时我父亲是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年轻教师,我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过。大学毕业第二年,有一次出差南京,我去看过高华。傍晚在南园散步时,他谈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他是一个性情醇厚、正直的人,这样的人在目前学界不是特别多。”  高华先生 当时南京大学港台阅览室不对大一、大二的学生开放。彭国翔请高华帮忙写了一个条子给管理员,称写论文需要,于是就可以进去看书了。后来他每天都去,跟管理员熟了,就不用条子了。他较早接触到海外学者的著作,其中既有牟宗三、唐君毅等人这条哲学的线索,也有从钱穆到余英时这条史学的线索。所以,除了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历史文献学日后也成为彭国翔耕耘的领域。 念大学时,读书只是彭国翔的爱好。1992年毕业后,他按照家长的意愿到南方工作,但很快发现高校之外完全无法读到文史哲等人文方面的著作。于是在1994年底,他临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那时距考试只有一个月,而他根本不知道考试的程序和科目。结果他考上了,硕士和博士的导师都是陈来教授。“我毫无疑问继承了北大中国哲学从冯友兰、张岱年先生到陈来先生的传统。这个传统一方面重视文献的考镜源流,另一方面重视思想的辨名析理。” 彭国翔的硕士论文研究王畿的“四无论”,博士阶段则以王畿为重点,拓展到整个中晚明阳明学的思想面貌。他说:“王畿见证了整个阳明学从兴起到顶峰、再到开始衰落的全部过程。当时阳明学几乎所有的思想论辩,都以他为中心。当然,这跟他高寿八十六岁有关系。”其博士论文在2004年成为北大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获得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的首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篇。 2000年,彭国翔念博士最后一年,获得赴台北访问四个月的机会,在几所重要的图书馆查找资料。那年正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在台北召开,他去听了余英时的主题演讲。会议休息期间,余英时跟陈来谈论撰写中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彭国翔在旁倾听,却不插话。余英时看到旁边这个年轻人一直静立,就很客气地说:“将来也送你一本。”彭国翔很感动,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致谢,未料余先生说:“那中午你来,我们一起吃饭。”那是彭国翔和余英时初次见面,他感觉受益匪浅,以后凡赴美都一定去向余英时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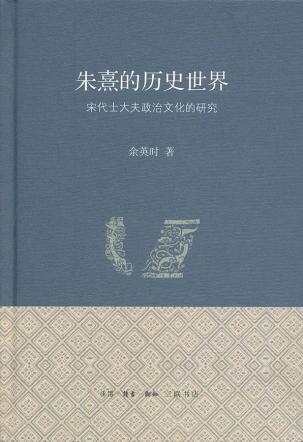 2003至2004年,由安乐哲(Roger T. Ames)提名,经一个专门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彭国翔受聘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安德鲁斯讲座客座教授(Arthur Lynn Andrews Chair Visiting Professor),该职位是为了纪念夏威夷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安德鲁斯而设。“我当时很惶恐,刚毕业两年,他们就给我这样一个客座教授的位置。后来我有一次写译稿,在后记说夏威夷大学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因为那个职位是应给资深学者的。” 后来,彭国翔多次在欧美、香港和台湾的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担任过客座教授和访问学人,做过演讲。2009年,他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担任洪堡学人(Alexander von Humboldt Professor)时,获得洪堡基金会和德国教育部颁授的贝塞尔研究奖(Friedrich Wilhelm Bessel Research Award),是中国人文学领域获得此奖的首位中国学者。2014年,他又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聘任,担任2016 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Kluge Chair in Count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North),成为该讲席自2001年设立以来的第九位学者,也是首位来自中国和亚洲的学者。 在我们几次的谈话(2012-2017)中,如何从事中国文史哲等人文学研究是彭国翔最关注的议题。他每每强调两点:“其一,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对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研究与阐发,需要放在世界文明和国际学术界的整体之中;其二,中国人文学的不同学科如哲学、历史和宗教等之间,需要相互配合与融合,尤其是哲学和史学,彼此之间要‘相济’而不是‘相非’。”此外,在谈话之中,彭国翔也常常流露出深切的社会关怀。显然,虽然以从事纯粹的学术思想工作自任,但他也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文化意识。这一方面在他的《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中有着鲜明的反映。 一、西方学术研究对中国人文学的意义 李怀宇:你的学术生涯中,国际经验很丰富,对于研究中国的学问,你觉得这种经验的意义在哪里? 彭国翔:我从事的研究是中国人文学,具体包括中国的哲学、思想史和宗教。但是,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思想创造,中国人文学早已是世界学术思想共同体的一个部分。二十世纪初现代中国学术建立以来,无论是知识的分类系统还是整个教育制度,都已经无可避免地西方化了。作为“学科”的“哲学”、“历史”、“宗教”等等,都是西方学术分类体系之下的结果。因此,从事中国哲学、历史和宗教的研究,不可能与世界的学术共同体绝缘。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学问早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专属,在中国之外,世界各地几乎都有从事中国人文学的同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如果不能放眼国际,不能充分吸收和消化世界范围内相关领域的既有成果,学术研究上真正的推陈出新,是很难甚至无法做到的。另一方面,即使从思想创造的角度来说,如果无视中国之外、世界上其他文化传统中不断累积和发展的思想成果,不去对话、吸收和消化,是否能够创造出真正既创新且有价值的思想,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孔子曾说“温故而知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故”就绝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过去的传统,也应当包括世界上其他文明发展出来的人文成就。无论是了解国际范围内研究中国人文学的同行的研究成果,还是吸收其他文明在人文学方面的结晶,比如西方、印度的哲学、史学、宗教学等,对于中国人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在我看来都是有益的。 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了解国际上的同行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了解其他文化传统中那些一流学者在哲学、历史和宗教等人文领域的研究和思考,对于我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和宗教的研究与思考来说,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产生极大的触动,构成有益的助源。我经常说,以古今中外人类的经验和知识总体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井底之蛙,庄子所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每一只蛙各自井口的大小并不一样,知识人总有这样一种心智的追求,即不断扩展自己的井口以尽可能扩大自己所能看到的天空。我的体会就是,在读书思考的过程中,具备国际的经验和视野,自觉地将中国人文学置于世界人文学的整体之中予以观察和思考,是让自己看到更大天际的一个重要保障。从一个人在知识、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成长来说,国际经验常常给予新的挑战和刺激,我觉得既是磨练,也是乐趣。  当然,在已经西方化的现代学术体制中进行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和思考,也需要具备一种高度自觉。即中国的传统学问往往不能纳入到某种单一的学科之中。比如说,儒学在中国大陆一般是哲学系的科目,在台湾就有所不同,很多情况下是中文系讲授和研究的科目。而到了北美,儒学的课程和学位培养主要不在哲学系,而是在东亚系、历史系和宗教系;至于欧洲,则大都属于汉学系研习的领域。西方的学术分类系统注重专业分工,同样是从事儒学研究,哲学系、历史系、东亚系、宗教系和汉学系的学者彼此差别很大。我的经验是,只要是从事儒学研究的,都是我的同行,都可以交流。但是有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在西方分别属于不同系科的同行,彼此之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交流,他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也是差别很大。事实上,儒学是一个包含很多面向的丰富传统,并不是哲学、历史、宗教学和区域研究等任何一个科目所能够单独涵盖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充分的自觉,不同学科训练出身的学者之间,有时就不免会“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彼此相轻。对于理解儒学传统来说,这当然无益有害。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显然是西方学术分类系统应用于中国学问的一个负面后果。当然,有些中国学者在看到这一点后,试图通过彻底清除如今“中学”里面的“西方”因素来避免那种负面后果,这显然不是一种健全的思路。我在本世纪初即指出,中国学术思想主体性的建立,不能寄望于和西方学术思想的绝缘,而恰恰需要在与其深度地交融之中,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方式方可实现。 李怀宇:你在2016年到美国任克鲁格讲席后,在学术研究上有什么新发现? 彭国翔:担任2016年度克鲁格讲席对我的研究帮助极大。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拥有极为丰富的收藏。我担任讲席期间,除了要进行一场公开的克鲁格讲席学者学术讲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义务。克鲁格中心(John W. Kluge Center)给我提供了专门的研究室以及调阅各种资料的便利,我可以充分利用国会图书馆的丰富收藏专心从事自己的研究。我每到一处图书馆,一定会尽可能全面了解其中的收藏,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比如,2003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就发现了被认为是佚失了的黄宗羲的《理学录》,该书是黄宗羲作《明儒学案》前的准备之作;2004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则发现了牟宗三先生的一部佚著。这次在国会图书馆,也自然不期而遇地看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以亚洲部的中文收藏为例,对我来说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数千册的善本古籍和一大批1958年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资料:善本古籍中不乏一些对于儒学史研究极有价值的明清文献;1958年前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中则有很多国内罕见的资料,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想世界和社会面貌,可以说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有不少有趣的课题可以让我将来慢慢研究。当然,除了中文资料外,由于国内图书馆西文资料的收藏尤其是最新出版的西文著作仍然不足,我不会错过收集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一流学者著作的机会。这里面既有那些西方一流学者有关中国人文学研究的著作,更有那些虽与中国研究毫无关系、但代表西方人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西方学者在哲学、历史、宗教等人文学领域出版的著作。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只要我们承认人类的经验以及文明的发展有着不可否认的某种共性,这些纯粹的西方经验,或者说基于西方经验而对人类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刻反省,仍然会对我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研究中国人文学构成极为有益的助源。 二、中国人文学的断裂与重建 李怀宇:中国人文学在1949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冯友兰曾经说过,1949 年以后,他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你如何观察这种学术的发展趋势? 彭国翔:很清楚,1949年是一个分界线。现代学术建立以来,中国最好的时代就是二十世纪20到40年代,期间出了一大批大学者,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没有丢掉,另一方面可以直接接触西方的学术,这两者结合得很自然。这本来是一个很健康的方向,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很可惜,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这边断了,台湾则继续了大陆1920到40年代这样一个现代学术的学统。留在大陆的学者,基本上不能够从事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工作,被当时的极左思潮裹挟而去。台湾则没有受到这种影响,当时国民党对文化学术不是没有控制和渗透,但基本上没有能够把学术的自主性取消掉。 1949年后中国的人文学传统被迫转到海外去了,主要包括台湾、香港和北美;新亚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十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逐渐开始重建人文学的学统,其实也是接着以前的路走。从1949年到1980年代,虽然不能说一片空白,但学统基本上是荒废了。老一代很好的学者基本不能说话,像贺麟先生去做翻译了,他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写的很多文章都很有创造性。还有像周一良先生这么好的学者,后来进了“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他没有办法,学术研究不能做了。这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文学的再出发,只能接续1920至40年代开辟的学统,在此基础之上发扬光大。今后中国人文学的发展,只有对此具备高度的自觉,沿着融汇中西的方向不断开拓,才会继往开来,从而真正推陈出新,有所建树。 李怀宇:回顾1950年代以后到美国留学的华裔学者,像张光直、余英时、张灏、林毓生、刘述先、杜维明等先生,现在看起来好像群星璀璨,为什么会出现留美这种现象?  余英时(左四)杨联陞(右六)中央研究院第六届院士会议合影 彭国翔:我想这当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杨联陞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来没有想到要留在美国。当时大部分中国学者还是打算“叶落归根”,几乎没有想要“落地生根”的,但变局让他们很多人不得不采取那样一个选择。林毓生、张灏、杜维明这几位先生是在台湾接受或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去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那边,这一点余英时先生又跟他们不同。余先生念大学之前,在大陆基本是自修,后来分别就读东北的中正大学和北京的燕京大学,1950年才由燕京大学历史系转到香港的新亚书院;1955年由香港赴美,先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哈佛大学,然后转为博士生;在哈佛完成博士学位,继而分别在密歇根、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有人以为余先生是台湾学者,其实他每次去台湾最多不超过一个月,说他是台湾人完全是误会。台港两地比较之下,余先生在香港的时间更长,除了1950至1955年在新亚书院之外,1970 年代还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过新亚书院院长。由这几位所代表的一代华人学者,基本都在上世纪40年代以前出生。他们的中国人文学基础很好,尤其像余先生,不仅功底深厚,后来又受教于钱穆、杨联陞先生,并长期从事中国人文学研究,其造诣足以代表当今中国人文学的最高水平。同时,这一批学者又在海外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对西学也很熟悉。所以我觉得你说的这些老一辈海外学者“成群而来”,除了他们个人的天赋与勤恳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特殊时代造就的。 李怀宇:萧公权在《问学谏往录》最后一章“万里寄踪”中回忆道,1949年以后留在美国,并没有长住的打算,时局变化后,决定“且住为佳”。而后来愈来愈多的中国人赴美留学,情况就不一样了。 彭国翔:对,他们当时就是面对这个际遇,“寄”字就反映了当时的心态:没有想到要落地生根,觉得中国面临巨变,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只能寄居国外;一旦玉宇澄清,还是愿意回来的。后来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像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之后再出去留学的人,心态完全不一样:理工科的占主流,人文学科还是少数;并且,由于中国人文学传统在大陆一度中断,1949年以后出生的一代,无法接受传统文化的薰陶,遑论训练。在这样的背景下赴美留学,基本上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学者学习了。 当然,华人学者在西方能够进入人文学一线之列者凤毛麟角,也跟人文学的特点有关。以我自己的看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语言文字。为什么华人学者在理工科更容易有成就?因为理工科对语言文字的要求不可能跟人文学科相比,人文学科往往是一门修辞的艺术,对语言文字的要求非常高。从理工科到社会科学,即使是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学、人类学等,还是不如人文学科对于语言文字的要求高。文史哲、宗教和艺术对语言文字的要求非常高,不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尤其华人,就不太容易跟西方学者在人文学(尤其是西方的人文学)领域中以英文“华山论剑”。作为一种文明的反映,英文背后也有千余年的传统,登堂入室绝非易事。像故去不久的余国藩先生西学造诣之高,在华人学者中是屈指可数的。当然,科学毕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较容易客观化、普遍化,拿出来的东西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人文学则与之不同。这也是西方世界或者说英语世界中科学领域的华人学者比人文领域的华人学者更容易成功的一个原因。 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与视角 李怀宇:我发现你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你既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容易看到你的研究不限于哲学,还有历史和宗教。比如你2007年曾经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叫《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书,里面很多内容似乎都是宗教方面的。另外,2013和2015年,你的《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一书,也在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中华书局分别出了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这本书属于历史研究的类型。对此,可否请你谈一下你的自觉? 彭国翔:我这两本书一本属于宗教学和比较宗教学的领域,另一本则是历史文献学和思想史的领域。至于我2003和2005年分别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是我的博士论文,主要属于哲学和哲学史的类型,当然,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历史文献和思想史内容。我迄今为止发表的论文也有这一特点,即大致可以划分到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哲学、历史和宗教。之所以如此,我想大致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与我的研究兴趣比较广泛有关。我觉得一个以学术为终生志业的人,就应该自觉地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就像我前面说过的,要不断扩大自己井口的口径,看到更大的天空。当然,扩展研究领域需要“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还没有掘井及泉,就跑到另外一个领域去。学界也有这样的学者,看起来涉猎广泛,但每一个点都不深入,浅尝辄止;这样不是真正的学识渊博,只能贻笑大方。只有在彻底解决一项研究课题,在一个领域深耕并切实取得建树和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之后,才可以移师其他的研究课题和领域,开辟新的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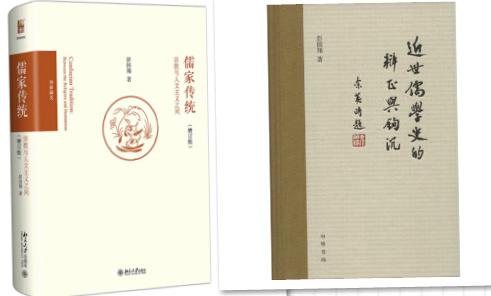 其次,在欧美、台港等地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客座或访学经验,对于拓宽我的研究领域、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2012年我曾经应邀到位于德国哥廷根的马普研究院宗教与民族多样性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Diversity)担任研究员(事缘2009 年我在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担任洪堡学人时,应哥廷根大学东亚系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之邀去举行讲座,当时刚刚接任研究所所长的范彼德[Peter van der Veer]教授当即向我发出邀请,但到了2012年我才得暇前往)。去了之后才发现,除了我是人文学专业,所内所有的研究人员,几乎都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专业背景。范彼德教授原是从宗教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印度的专家,之所以邀请我,大概与他晚近这些年来转而对儒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关。对我来说,宗教原本是兴趣所在,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的取径,则是新的方法和视角,我很乐意从中受益。如此一来,我自然在自己的研究中汲取了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不过,我对于不同方法和取径的“所见”与“所蔽”有着高度的自觉,所以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不会“从人脚跟转”。比如说,如今西方从事中国宗教研究的学者有相当一批有着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的背景,受其影响,国内很多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亦步亦趋,这对于以往中国宗教学研究流于空疏、不太注重田野调查的偏颇,当然有纠正的作用。但是,我也始终认为,宗教人类学究其实是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现象,宗教社会学究其实是以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宗教现象,并不能涵盖宗教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宗教之所以为宗教学最核心的部分,甚至根本无法化约到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领域,这也是西方学界中神学、宗教哲学领域始终未被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这一趋势所取代甚至掩盖的一个原因所在。 当然,我注重不同学科的彼此结合,归根到底取决于我对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与中国人文学传统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认识。我在《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鈎沉》的〈前言〉中曾有这样的比喻: 我多年以来一直认为,人文学术中的不同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等,其实都是观察与思考人文世界的不同角度,彼此之间非但并无高下短长,更需要相互配合,方可掌握人文世界的整全。任何一个学科有所“见”的同时也都有所“蔽”。恰如一个手电筒,在照亮一个局部的同时,不免无视其余而在周围留下阴影。因此,这些学科只有彼此配合,各条光束相互汇聚,方能形成“无影灯”,使得人文世界的整体尽可能得到完全的照明。现代学术早已如庄子所谓“道术为天下裂”,分工日益细密。在没有专业和擅长的情况下以“通人”自居,妄谈打破学科界限,只能流于掩盖浮泛与空疏的遮羞布。但学者的学术训练不限于一门学科,掌握一门以上的研究方法,恰如武学高手可以精通一门以上的武艺,虽然能“至”与否有赖于个人主客观的诸多条件,但却应当是“心向往之”的目标。当然,兼通一门以上的武艺,是必须以先通一门武艺为前提的。同时,兼通一门以上的武艺,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武艺由于可以集于习武者一身而泯灭了各自练法的不同。恰如武学高手可以兼擅内家的太极拳与外家的谭腿,但太极和谭腿各自的习练法门却不会因此而混同一样。(〈前言〉,载《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鈎沉》,繁体版,页11-12。) 因此,对于无法化归于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系统中某种单一门类的中国传统人文学,包括儒、释、道等,就更不能单纯地以某一种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加以研究。如前所述,儒学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中基本属于哲学系的科目,在台湾则往往属于中文系的科目,而在美国又往往设在东亚系、历史系和宗教系。这并不奇怪,只能说明儒学本身包含许多不同的面相,需要从不同的学科入手来加以研究,这样才能揭示其整全的内容。  彭国翔先生 李怀宇:你早期研究的主要是宋明理学,后来慢慢涉及到当代儒学,而你的一些研究似乎又在宋明理学和当代儒学这两个领域之外,请你谈谈这种情况。 彭国翔:从我出版和发表的文字来看,如你说的先是宋明理学,然后是当代儒学,比如我关于牟宗三先生政治与社会思想的研究《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就是最近出版的。但是,从我的阅读经验来看,我接触现当代儒学反而更早。事实上,我在大学时代已经开始阅读现代儒家学者包括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冯友兰等人的著作,对现代新儒学这一脉络可以说当时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当然,那时我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泛,即便以海外的研究为例,除了这几位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其他如钱穆、方东美、余英时、刘述先等人,甚至像罗光这样具天主教背景的学者的著作,也在我的阅读范围之列。中国大陆方面,如李泽厚、陈来等先生的著作,我也已经系统地阅读了不少。所以,不能说我是后来才涉及当代儒学,只能说我关于当代儒学的文字,较之宋明理学的研究,正式发表得较晚一些。我关于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的研究,其实问题意识很早就有。晚近这些年中国大陆有所谓“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这种奇怪的两分法,一些不读书的人声称牟宗三只有“心性儒学”而无“政治儒学”;我关于牟宗三的书出版后,就有学者认为我对这种说法做出了有力的回应。当然,我的书全面呈现和分析了牟宗三政治与社会思想各个方面,客观上可以说是对那种错误的说法进行了回应,但我的研究并不是要回应那种在我看来毫无理据和价值的两分法。因为我开始留意包括牟宗三在内的现当代儒学的政治与社会取向时,那种两分法还根本不曾出现。 四、学术研究与时代气息 李怀宇:在这样一个大的变动时代,时代气息会影响到你的学术研究吗?在你的《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一书中,反映了你的文化关怀和价值立场,这是不是时代气息的影响? 彭国翔:每个人都无法生活在真空之中,影响是难免的,但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自觉。一方面,我们要知道自己跟时代息息相关,不可能置身于时代之外;而且这个时代整个文化氛围的风吹草动,对自己一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在做一个客观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必须保持不为这个时代的思潮所裹挟,不能随大流。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个古代的东西,要尽可能设身处地进入到当时的世界当中,如果带着太强烈的现实关怀,有可能对自己的研究产生不利的影响。当然,在我看来,一个好的学者和知识人,即使面对具体的时代课题,也总会思考一些超越于特定时代之上的问题。同时,如果对自己研究和思考的资源能够不为这个时代所局限,那么相信对于这个时代的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就可以更为周密和深入。比如说,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一些思想家以及中国宋明时期若干哲人的智慧,很可能就有助于我们思索当今时代的种种问题。  你提到我的《重建斯文》,的确,这本书是我的文化关怀和价值立场的集中体现。其中涉及的许多问题,当然可以说是时代气息的影响,不过更准确地说,是我对于时代问题的观察、分析和反省。中国的知识人历来有关心政治、投身文化和参与社会的传统。传统社会解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知识人关心政治、投身文化以及参与社会的方式就不再像过去那样了。但是,即便是纯粹的学院知识人,只要以人文学为“志业”,而不仅仅是谋生的“职业”,就不可避免地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问题产生忧患意识,甚至“以天下为己任”。这大概不仅是儒家文化的薰陶所致,更是人文学的特点所致。古今中外的人文学者,只要不是把从事人文学作为纯粹的生计,几乎莫不如此。事实上,正如余英时先生引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余英时:〈自序〉,载《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页3)。这一点也许就是“知识人”和“知识从业员”的区别所在。当然,知识人对于时代的关注,又必须严格建立在自己所学的基础之上,不然就像如今的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公共”而无“知识”,其社会关怀就不过是表演性质的惺惺作态;以此为基础的各种言论,也很难有什么真知灼见。我对于儒学与当今世界的一些看法,是否有真知灼见取决于读者的判断,但确是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对于如今中国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关键和当务之急,我多年前提出“重建斯文”这句话加以概括,也正源于此。 作者:李怀宇:广东澄海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问和研究,著有《访问历史》、《世界知识公民》、《知人论世》、《访问时代》等。 原文以“彭国翔:国际化的中国人文学者”为题刊于《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第180期 (2020 / 08 / 01) ,P128-138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