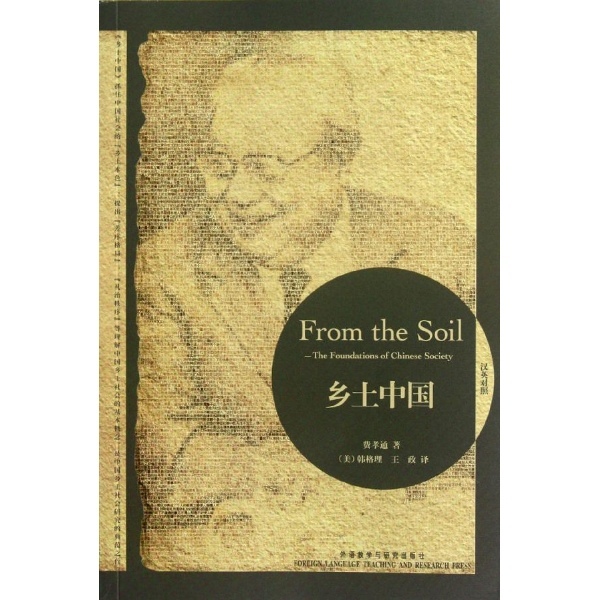梁鸿:是乡土中国真的愚昧落后 还是我们站“错”了位置看待它?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梁鸿的作品是什么类型 › 梁鸿:是乡土中国真的愚昧落后 还是我们站“错”了位置看待它? |
梁鸿:是乡土中国真的愚昧落后 还是我们站“错”了位置看待它?
|
编者按:继《“灵光”的消逝》、《外省笔记》之后,梁鸿文学评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作品《作为方法的“乡愁”》于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该书试图通过对阎连科代表作《受活》核心词语和象征符号背后所涉及到的词义变迁、历史语境和种种社会生活冲突性存在的分析,寻找叙事的秘密、探寻社会生活的精神内核。重返“乡愁”,其实也是重新思考“乡”在中国生活中的独特意义。“乡”既是广义的“乡”,家乡,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小城,民族,也是实际的乡村、大地、山川、河流、树林、花草,还指中国独特的文化意义上的“乡”,乡土、农业文明、亚洲文化、东方生活等等。人们要思考的是:这一“乡”内部有怎样的生活样态,这些样态哪些应该属于“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哪些则是属于“不停变化着的过渡的未来的那一半”。而在当代的中国,“乡”逐渐只剩下政治经济学层面的乡村,而文化、道德和“家”的层面的乡村正在丧失,“永恒和不变的那一半”正在被摧毁、扭曲或彻底消失。下面这篇文章节选自该书第二章《“乡土中国”:起源、生成与形态》,经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从中,我们或可看到“乡土中国”是如何在知识分子以“西洋的原理为基础的”审视之下变得“异质化”甚至“耻辱化”的,同时或可反省,我们在有意无意中把“乡土中国”塑造成为一个与“现代中国”对立的存在,这样的做法使我们遮蔽、误解或错过了什么。
“黑格尔把缺乏精神之内在性的中国作为没有历史进步的停滞大国而排除在世界史之外。黑格尔认为中国缺乏‘属于精神的所有东西,如自由的实体精神、道德心、感情、内在宗教、科学、艺术’,相信象形文字·汉字是符合缺乏精神自由之发展的中国社会的文字符号。‘中国民族的象形文字书写语言,只适合于中国的精神形成中静止的东西’。象形文字·汉字正是中国社会停滞性的象征。”“停滞的帝国”, “穿蓝色长袍的国度”,“难以捉摸的中国人”,“帝国的没落”,这些西方人类学短语勾勒出了“中国”的基本形象,这些可以说近代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基本描述和基本定位。 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必须要到遥远的热带去考察“野蛮人”的生活、语言那样,在20世纪30年代前,欧洲人类学一直是以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野蛮人”的族群作为研究对象的。当年费孝通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使其导师马林诺基看到了人类学对“文明民族”研究的可能性。并且认为“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 但是,有一个小花絮恰恰证明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已经类似于“古老的、野蛮的”民族,正是黑格尔所言的“停滞的、静止的”形象。在马氏给《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写的序言里,这样写道“It is the result of work done by a native among natives”,由于害怕费孝通误解,马氏特意向费孝通说明“native”指的只是“本地人”,并没有“野蛮人”之意。因为在当时的西方语言中,native一词已经包含着某种贬义,特指殖民地上的本地人或土著人,也是当时人类学最常用的一个词语,西方殖民主义已经深入到民间的语言感觉之中。马氏的特别解释反而证实了当时中国在西方的基本形象。
中国人生,中国文明是业已完成、即将消失的人生,是属于过去的时间和空间的。在这一考察视角下,中国人的生活是如此原始,如此蒙昧。中国的语言、风俗、礼俗、性格,还有那被西方人认为是“过于成熟因此走向衰弱”的病态的美的文化,建造出丑陋、怪异和残酷的中国生活,而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由黑格尔所言的“东洋的专制”造成的。“在黑格尔那里,‘东洋’的构成处在作为西洋原理的世界史发展之‘外’,在时间、空间上都是与西洋异质的世界。构成‘东洋’的乃是‘我们西洋’的原理。”在“世界史”的视野内,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这一“异质性”,并以此来评价、判断中国文化的优劣。换句话说,近代以来,知识者一直以“他者”的身份来审视自身民族的种种。种种问题的发现既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觉醒、民族国家的诞生和现代性思维的渗透,但同时,它的起点和前思维也决定这一审视的非主体性和价值偏向。
以此角度,再看“乡土中国”的诞生,它是在观照视野下的产物,是自“天朝中心主义”被打破之后就开始慢慢被呈现出来的“自在物”。这一“自在物”悬浮于民族的观念之中,与新生的思维、新的文明方式形成对峙。它有着来自于久远历史和时间所塑造出来的坚硬和愚昧,但又充满悲伤,因为它是古老中国的象征物。 这一“自在物”和“象征物”一旦被固定化和抽象化,它与现实时代精神之间的冲突会被强化,并且多强调它作为一种固定模式的负面因素,而可能的融合的那一部分,即它作为一个运动着的生活的可塑性则会被忽略。于是,我们看到,“乡土中国”一直是愚昧、落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形象,而它所拥有的“乡土文化特征、道德礼俗、儒家思想”则是“停滞大国”的精神根源。这是拥有了新思维的五四知识分子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去审视自己“故乡”的结果,因为有了距离,有了新的视野,才有可能反过来观望原来的自我,这时,是一个全新的“自我”去审视“过去”的自我。很显然,此时的“乡土中国”是完全“异质性”的,这背后的“审视”是以“西洋的原理为基础的”。这是视野的起源问题,它造成二元对立的观念和线性历史发展观,但并非涉及对错,因为中国的“近代”,中国有“变革”的可能性正是从这样的视野开始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直致力于进行乡土中国的构建与想象。想象“乡土中国”的方式,也是他们想象现代性及现代性所代表的意义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性想象”与“乡土中国”并非两个对立的名词,从晚清时期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生活内部起,譬如传教士的大量进入对乡村民众思想的影响,譬如工业进入乡村内部对中国手工业生产方式的冲击,这在许多作家作品那里都有体现。“现代性”一直与“乡土中国”融合、排斥、纠缠,它们已经互为一体创造出新的中国生活,但也正是在逐渐深入的渗透过程中,它们各自顽固地呈现出自己的根性。
但是,因为“世界史”的视野始终占据上风,“乡土中国”一直是处于被批判被否定的位置。在文学史上,虽然有废名《竹林的故事》、沈从文《边城》这样的作品,但它被看作是纯文学和纯粹理想的存在,与现实的乡土不发生关系。这一状况到了延安文学时期和“十七年文学”略有改变,农民、乡村形象第一次变得高大、幸福、欢乐,他们朴素的阶级情感和温柔敦厚也被“发现”,这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创业史》等作品中都有体现,但是,这一“发现”背后强烈的政治意图使其与乡土中国纯粹的自性发掘还有很远距离。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又一次把“乡土中国”陌生化和“异质化”,《爸爸爸》《棋王》《厚土》中的人物无一不是具有“原型”意味的乡土中国和传统文化形象,它们如同肿瘤,永远附着在民族的躯体内部。 从另一层面看,中国作家对自己的文化,对“乡土中国”始终有一种“耻辱”心理,这也是乡土中国他者化的重要表现。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在谈到他自身的土耳其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时,这样说道,“向西方看齐,意味着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文化持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完全,甚至是毫无价值。这种冲突是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传统的冲突。这些冲突还会导致另外一种混乱———耻辱。当我们在土耳其谈论传统与现代紧张关系的时候,当我们谈论土耳其与欧洲含糊其辞的关系的时候,耻辱总是悄悄潜入。”“耻辱”,这一词语非常恰切地表达了当现代性引入东方时,东方民族最基本的情绪和心理基础。因为有压迫性,所以感到耻辱,因为耻辱,故此更深刻地批判自身文化的缺陷和弱点,这是强势文明和弱势文明交锋时所共有的不自信。 随着当代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整个乡村被摧枯拉朽般地摧毁,这一摧毁不只是乡土中国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政治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举摧毁了整个民族原有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基础。即使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批判”和“质疑”,乡土内部道德结构和文化原型仍然保持着一种均衡性和神圣化的意味,儒家道德主义仍然对每个人有基本的约束力,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会结构都仍在这一底线之内。当经济的驱动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和发展方向时,一切曾经神圣的事物都被变为世俗的,工作、生活很难再为人们提供终极意义和终极信念。“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对于中国生活来说,那“坚固的东西”是什么呢?尽管那“神圣的东西”(如中国传统的道德结构)同时也阻碍了民族自由个性和健全政治之发展,但它毕竟是全民族的心理无意识,它类似于宗教,具有一种约束、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当整个社会被“经济的解放力”所控制时,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撼动了民族最深层的文化结构和道德观念,曾经为之自豪的、骄傲的事物变得一文不值,如“教授不如卖茶叶蛋的”;曾经具有天然的神圣契约的关系也开始破碎,譬如父母和孩子,医生和患者,教师和学生,等等。191990年代中国人在精神和人的本质存在层面所发生的精神嬗变并不亚于世纪之初王权坍塌带给中国人的影响。 在这样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思潮中,“乡土中国”的命题似乎不再只是“劣根性”的问题,而涉及到它是否还应该存在的根本问题。因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乡土中国”始终是“异质性”的,是线性发展的过去阶段,必须被取代。所以,今天,我们在任何地方重提“传统”、“本土”、“儒家”或与这些词语相关的具体生活时,都首先要面临着被质疑的眼光,这一“被质疑”不只是基于质疑者对自身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批判视野,而是世界史视野对“乡土中国”定位的结果与外现。  鲁迅《狂人日记》插图
对“乡土中心主义”的反思
鲁迅《狂人日记》插图
对“乡土中心主义”的反思
实际上,当以“世界史”的视野把“乡土中国”作为一个“不变的抽象物”来思考时,在有意无意中,我们在把“乡土中国”塑造为一个与“现代中国”对立的存在,就像《爸爸爸》中的“丙崽”。“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代表着过去与未来,要想达到“现代”,必须去除“乡土”,当然,也包括在“乡土”上形成的种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结构。这样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也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基本模式。 诚然,中国的确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乡土性”是它的基本特性,但它是否就是一个纯然的“不变的抽象物”?当“世界史”、“近代”、“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之时,在面对冲击时,它是否唯有“抵抗”、“溃败”,而没有“接受”?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它的“不变的抽象”存在,是否忽略了“乡土中国”的包容性和自我嬗变的能力,并由此形成新的“传统”的能力?进而,忽略它在中国未来生活中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正如丸山真男讲所谓“传统”和“外来”思想时所认为的,“以传统与非传统的范畴来区分两者,有可能会导致重大的误解。因为外来思想被摄取进来后,便以各种形式融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中,作为文化它已留下难以消除的烙印。从这种意义上讲,欧洲的思想也已在日本‘传统化’了,即使是翻译思想,甚至是误译思想,也相应地形成了我们思考的框架。” 其实,所谓的“乡土中国”也是如此,尤其是进入“世界史”以后,它的存在形态、文化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并形成新的特质。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费孝通在进行《江村经济》考察时就认为,江村传统经济方式的衰败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乡村工业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各种传统工业的迅速衰亡,“完全是由于西方工业扩张的缘故”,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的共同体中,西方的政治、经济压力是目前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而上文所提到的现代文学作品也都不约而同地书写到世界经济的进入对乡土中国生活和精神的影响,如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林家铺子》、《春蚕》、《秋收》,叶紫的《丰收》等都小说都有典型的体验。但是,在观念层面,知识分子总是倾向于把“乡土性”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抽象物来理解,这也直接影响到具体的科学考察和文学写作。 社会学家王铭铭在考察了现代时期著名社会学家许烺光的“喜洲”调查时发现,许烺光有意忽略掉喜洲作为一个曾经的都市所拥有的多元经济和多种文化,忽略了喜洲“都市/乡村”的双重面貌,而是倾向于把它形容为“乡村中国的一个典范村庄”,“急于表白自己对中国的乡土性之看法的许烺光对此没有任何表示,而埋头梳理这个地方在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的‘类型学典范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讲,他的著述与其说是民族志,毋宁说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村庄志表述。王铭铭认为,这一“乡土性”的界定恰恰是以“西方视野”为中心下所产生的。而1949年进入中国的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在经过考察后却有另外的看法,“施坚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认为恰是那些被我们想象为乡村的对立面的事物,才是‘乡民社会’的特点。在一生的学术追求中,施坚雅坚持了这个观点,指出中国乃是以城乡这个结构性的‘连续体’为特征的。”这一结论无疑对“乡村中心主义”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它暗含着一种观点,中国的乡村并非就是封闭的、纯粹农业的社会构成,它本身也包含着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活的因子,譬如每一个农民在农闲季节可以随时变为小商贩,而日常的集市、庙会都在村庄的周边,它也是乡村的大型经济场所,传统乡村中已经具备有非乡村因素,“城市”和“乡村”在某种意义上是共生于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但是,在“乡村中心主义”的观念下,“乡土”被作为“过去”的中国特征被确定下来,而被施氏(施坚雅)和沃氏(沃尔夫)当成欧亚农民社会重要特征之一的城市,则总是以必然取代乡村的“未来”——而非它的共生物——为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也可以使我们略微觉察到当代“城市化”发展思维的基本来源。 “知识分子那一‘乡村即为中国的缩影’的观念,其政治影响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得多(至少可以说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起到关键影响的思想之一)。将传统中国预设为乡村,既可能使国人在处理国家事务时总是关注乡村,又可能使我们将乡村简单地当做现代社会的前身与‘敌人’,使我们总是青睐于‘乡村都市化’。”当然,政治的驱动力并非只是因为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以此为起点,来重新反思这一百年来关于“乡土中国”的思想,它如何被“发现”,在这一发现过程中,我们又遮蔽了什么? 反思“乡土中心主义”立场,并非是要否定“乡土中国”的存在,更不是要否定中国作为具有独特文明方式的个性的存在,而是试图把“乡土中国”作为一个生成物,一个随着社会变迁内涵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的生成物,在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它同样具有包容与吸纳的力量,这样,才能够摆脱非此即彼(消灭乡村,建造城市)的二元对立发展观念,并且,使之与现代世界具有对话能力。 在现代化视野中,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被描述为一个静态的、没有生命力的,甚至是虚弱、怪异、荒诞的一个低级文化模式,它里面的人际关系是多么复杂可笑,人们的观念道德迷信低下,礼仪习俗更是落后。在科学、民主的涵盖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腐朽、脆弱又充满着病态美感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它也渐渐为我们所接受、认同并在此基础上,以全然“革命”的方式进行新的国家建设。中国古老文明的创造力,中国乡村和传统文明所具有的容纳力和包容性,它对美的感受,它的宽阔,它的因为与政治、与天地之间复杂混合而产生的思想、哲学观和世界观都被抛弃掉了。“世界史”的视野能帮助我们找到自身所处的坐标和在星空的位置,但同样,也可能会因为被吸引、被占有而遮蔽了自身的光芒和价值。 但是,文学又与社会学、政治学的实践不一样,文学中的“乡土中国”往往是一个强大的象征物。当作家在想象乡土中国的生活、观念与行为,甚至塑造一个桃花源的乌托邦时,他是否真的就认为这一“乡土中国”是最完美的,人类应该重回那样的时代?或许还不应该如此简单理解。今天,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站在全部事物商品化和经济化的时代,再返回来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并非只是二元对立的好与不好,而是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本源问题: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人、民族与世界、科学与自然、技术与人性等等本质性问题。在此视角上,我们再重新理解乡土文明的衰落、乡土中国的沦陷,它并非只是本土性失落的问题,它是整个人类生活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一切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