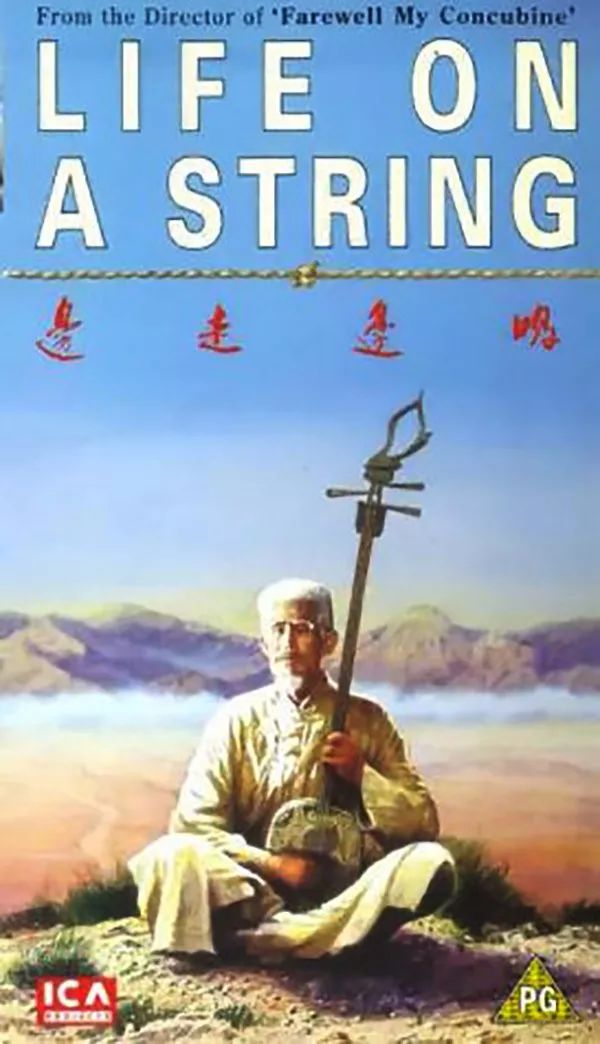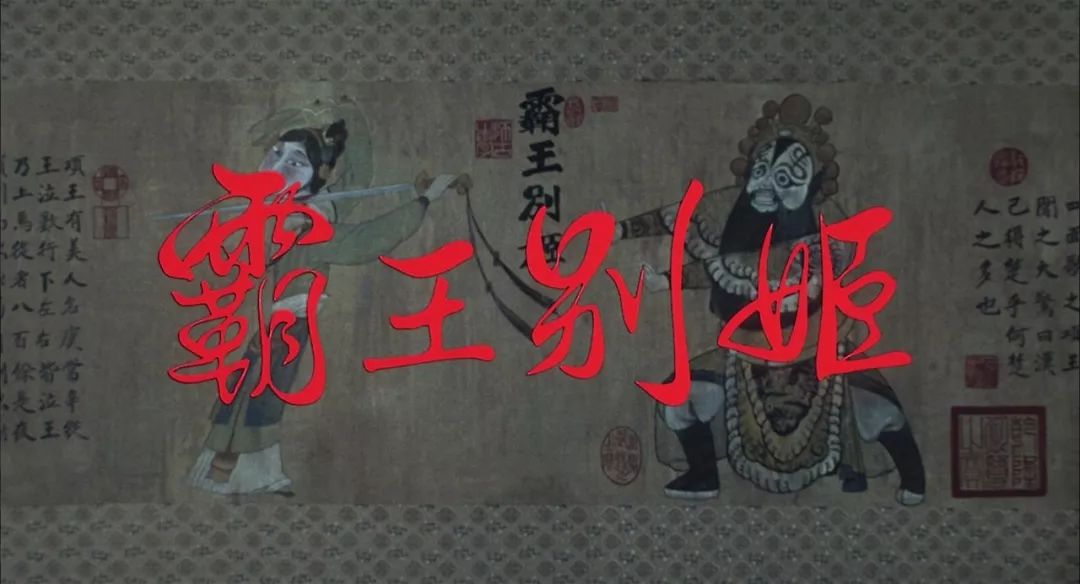戴锦华:程蝶衣是历史暴力写成的诗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张国荣的夫妻几个孩子啊 › 戴锦华:程蝶衣是历史暴力写成的诗 |
戴锦华:程蝶衣是历史暴力写成的诗
|
《霸王别姬》剧照 陈凯歌对老中国历史暴力的痴迷集中呈现在关师傅形象及戏班子的诸多场景之中。事实上,影片最为成功与迷人的,正是戏班子中的若干段落。勿庸置疑,关师傅的戏班子成功地充当了老中国/元社会的象喻与指称,而关师傅无疑是这个大舞台、小世界的灵魂,一个和谐“家庭”中的严父。
《霸王别姬》中的关师傅 关师傅/理想父亲形象的出演,正是陈凯歌对第五代之文化初衷的又一重背叛。八十年代,第五代之初,其对历史暴力的控诉与反思,同时呈现为对父子秩序的拒斥,笔者曾将其称之为“子一代的艺术”。甚至在陈凯歌迷途之始《边走边唱》中,“神神”师徒,同样被呈现为辗转于父子秩序与历史暴力之下的“子”的形象。老神神终其一生:七十年、千弦断,实践著师傅的许诺,换来的只是一张白纸,使他成了历史谎言的蒙难者与牺牲品,同时他仍试图延续这历史的链条:将历史的谎言传递给石头。
《边走边唱》电影海报 而在《霸王别姬》中,在关师傅及其戏班子的场景里,对父子秩序的控诉已全然消隐在一幕不无血腥、但毕竟和谐迷人的情境之中。在戏班子这一元社会情境中,关师傅无疑是一位绝对的权威者、一个名符其实的父亲形象、甚至不再有“母亲”来柔化这一情境。他对戏班子中的孩子们不仅授业解惑,而且生杀予夺。和影片中那个萎琐、施虐狂的师爷不同,关师付无疑是一位理想之父,是老中国迷人景观中的核心人物;同时,他也正是一个秩序的执掌者和更为残暴的暴力的执行人。 甚至在他狂怒与施暴之时,他仍然是尊严的:孩子们必需自己搬来行刑的长凳,递上木刀,还有人站立一旁,大声地宣读班规,以印证这一惩罚的合理性。似乎围绕著关师傅,陈凯歌失陷于历史暴力的二难推论之中。其中小癞子之死是颇为典型的一幕。 小癞子无疑是历史暴力的牺牲品,他显然被戏班子里无尽残酷的惩罚吓破了胆。尽管他也会在“名角”的舞台前热泪滚滚:“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个角儿啊?”,但,“那得挨多少打啊?!”终于,在关师傅的狂怒和无节制的毒打面前,他吞下了最后的糖葫芦,悬梁自尽了。在射入镜头的、眩目的阳光中,小癞子瘦小的身体在空中可怜而无助地晃动著。而关师傅显然是这幕无血之虐杀的元凶。
《霸王别姬》中的小癞子 但是,没有控诉、抗议;接下来的一场,是关师傅更为威严又颇为痛心(不是因小癞子之死,而是因他如此的“不成器”)地站立班前,为孩子们上了最为重要的一课:关于《霸王别姬》的真义;从虞姬从容赴死,引申出“做人道理”:“从一而终”,“人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于是,小癞子成了不懂得“成全自个儿”的范例,似乎付出了死的代价,仍无法洗去他的“污点”——他是无法被赦免的,但关师傅与暴力却得到了无保留的赦免。似乎那施虐狂的师爷宣称的正是真理:“您要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残酷的惩罚正是一种“成全”之术。
围绕著关师傅和戏班子中和谐而残暴的情境,陈凯歌建立起程蝶衣、段小楼这组彼此对称的人物形象。小石头/段小楼作为戏班子里的大师兄始终是这一景观中默契而虔诚的协作者。这不仅表现为他的投入和忠勇:在头上“拍板儿砖”为师傅解围、勤学苦练;而更多地表现为他深谙其中的“游戏规则”,并胜任甚或愉快地配合其完成。他总是“欢天喜地”地为师傅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惩罚搬取刑具、戏谑式地或真或假地喊疼并大声为师傅叫好、一次再次地在严冬的雪地里受跪罚,视其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与似乎天生成“个中人”的小石头相比,小豆子/程蝶衣则始终处在历史暴力的摧残与“改写”之中。是他的反抗与忍受将戏班子中的规矩显影为暴力,而不是和谐的游戏。降落于小豆子的这一暴力改写过程,以生母遗弃、并亲手执刀切去胼指开始,而后集中呈现在《思凡》一出戏的排演之上。
《霸王别姬》中小豆子与生母 显然,在陈凯歌所结构的叙事过程中,发生在小豆子身上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生角、旦角的派定,而是一个施之于他的暴力的性别改写。《思凡》中的一句对白:“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在小豆子那里被固置为“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这是意识与无意识间一次绝望而痛楚的反抗(一如小石头所言,“你就想你是个女的,可别再背错了!”),一次再次的毒打也无法使他改变。 而当他听说被打伤的手一旦进水就会残废,他立刻将手浸入水中:他宁肯残废,也不愿接受历史暴力的改写。他与小癞子一起出逃,但终因那迷人的舞台、和舞台上威风凛凛的霸王返回之时,他是屈服于舞台与扮演的诱惑,却没有完全屈服于师傅、暴力与改写。他不告饶、不出声的忍受,终于使关师傅狂怒地大施淫威(那残暴的场景直接导致了小癞子的死。事实上,也只有程蝶衣始终没有忘记小癞子。当他成了一个名角之后,影片中两度出现在远处传来悠长而凄凉的“冰糖葫芦”的叫卖声时,程蝶衣脸上闪过一片迷茫)。但改写仍没有实现与完成:“女娇娥”、“男儿郎”的“错误”仍在延续,直到小石头作为暴力的实施者、抄起师傅的烟袋锅在小豆子的嘴里一阵狂搅。
无论在影片的视觉呈现、还是在弗洛依德主义的象征意义上,这都无疑是一个强奸的场景。但这次暴力实现了改写的最后一笔,在鲜血由小豆子的嘴角淌出的镜头之后,他似乎带著一种迷醉、幸福的表情款款地站起身来,仪态万方、行云流水般地道出了:“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 此后,来自张公公处的强暴,则固置了这一暴力的性别改写,并将这一暴行的发出者清晰地标示为历史。小豆子遭张公公强暴一场,是陈凯歌所迷失的暴力迷宫中最为朴溯迷离的一笔。白色的帐幔垂绦、迷蒙的金色的逆光,晶莹的水晶钵,如魔怪、似巫妪的张公公,使这暴力的一幕,呈现为东方镜城中邪恶迷人的一景。显然易见,小豆子并非为张公公所强暴,而是为已成为历史的“历史”暴力所玷污——因为张公公“没有菲勒斯,他本身就是菲勒斯”。
《霸王别姬》中的张公公 事实上,自三度暴力/阉割行为之后,在小豆子/程蝶衣身上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裂隙、或曰意义的反转。相对于小石头/段小楼,程蝶衣更为深刻、彻底地将他始终反抗、却不断强加于他的权力意志内在化了。他不仅接受了暴力的改写,而且将固执于这一改写过的身份,并固守著这暴力的秩序。是他,而不是段小楼成为关师傅得意的弟子。 同时,他固执著为暴力所派定的女性角色,固执于“从一而终”的训令,固执地置身于真实的历史进程之外。因为他是一个“女人”,一个镜象中的女人,只有舞台上、镜象中才有他的生命。而段小楼则置身于历史的涡旋之中,忠贞或背叛、反抗或屈服。程蝶衣是《霸王别姬》中的诗,而这诗行却是为历史暴力所写就的。
而程蝶衣这首似乎可以无限复沓、绵延的诗行却再度为历史的暴力所打断。影片关于历史和暴力的话语再一次出现了裂隙。而关师傅之死则名符其实地预示著一个时代的终结与一个世界的沉沦。关师傅死在一个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戏班子情景之中,死在为孩子示范《林冲夜奔》中“八百万禁军教头”(楚霸王之外的又一个末路英雄)的英武造型之时。 此后,便是蝶衣、小楼与张公公的巧遇,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幻之年。历史将以一种新的方式改写个人的生命,程蝶衣将黛玉焚稿式地焚毁斑斓的戏衣,再次拒绝被改写。这一次,暴力将显现出它的酷烈与血腥,不再为镜象中的迷离与和谐所柔化。
如果说,李碧华的小说是一个关于背叛的故事;那么,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则正是空间化的历史/没有年代的历史与时间化的历史/编年史的并置之中,在历史的政治场景与性别场景的同台出演之中,背叛了第五代的文化及艺术初衷。 在这幅色彩斑斓、浓烈而忧伤的东方镜象中,陈凯歌们曾爱之深、恨之切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已成了真正的缺席者。纯正而超载的中国表象,已无法到达并降落于当代中国的现实之中。于是,中国的历史成了单薄而奇异的景片,中国的现实成了序幕和尾声里为一束追光所烛照的空荡的体育场,成了片尾空洞的黑色字幕衬底。
陈凯歌失落了他对历史与暴力的现实指认与立场。空荡的(非)舞台上,程蝶衣、段小楼出演了似是而非的一幕:先是程蝶衣玩笑式地反转了那一被改写的时刻:“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此后则是他抽出那柄宝剑,在虞姬刎颈的时刻自杀身亡。
如果这是颠倒、声讨历史的时刻,那么这又是完满历史镜象的时刻;如果这是历史延伸向现实的一瞬,那么现实却是一片空白。在陈凯歌的影片中,当历史与叙事再度联袂之时,叙事与现实却砰然脱榫。继戛纳之后,陈凯歌和《霸王别姬》进军奥斯卡。迷途的胜利者不再漂泊。 end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