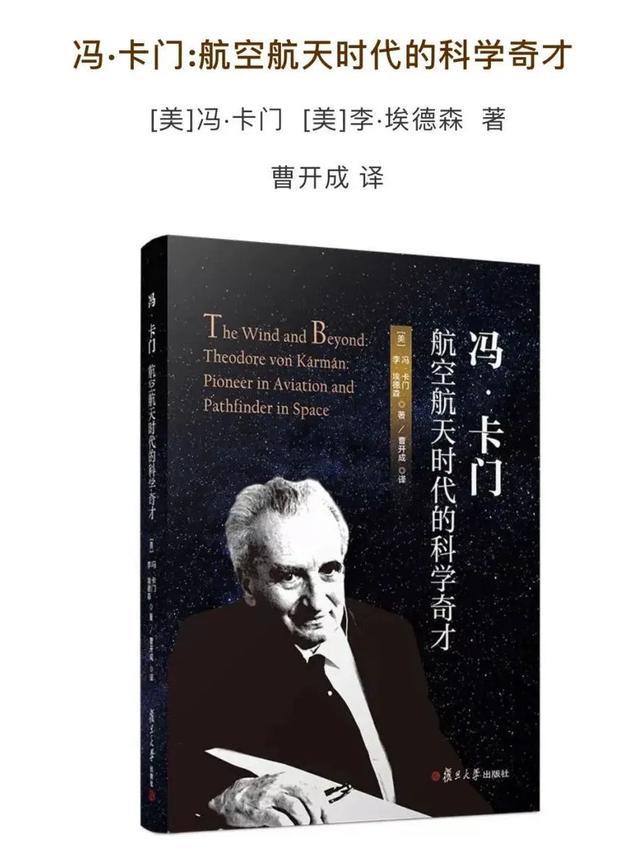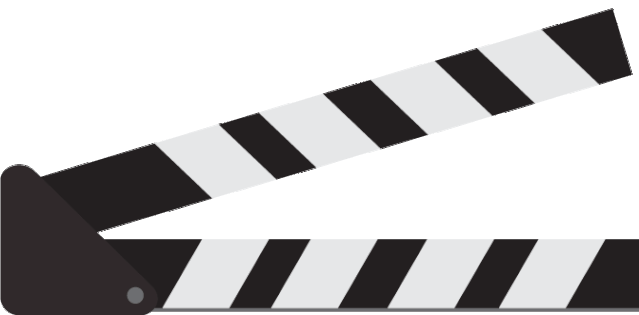卡门涡街:让“世界单跨桥之王”坍塌的罪魁祸首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华盛顿大桥属于什么桥 › 卡门涡街:让“世界单跨桥之王”坍塌的罪魁祸首 |
卡门涡街:让“世界单跨桥之王”坍塌的罪魁祸首
|
1940年11月7日,塔科马海峡大桥坍塌 11月8日,美国的各家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塌桥事故的报道,“塔科马海峡大桥坍塌”的大标题引起了冯·卡门的注意。细看新闻报道,他本能地意识到,一定是某个特定的空气动力现象导致了大桥的坍塌。 接着卡门看到报纸上说,华盛顿州的克拉伦斯·马丁州长说塔科马大桥的设计没有问题,州政府打算按这座桥的基本结构重新造一座新桥。这下冯·卡门坐不住了,内心极度不安的他当天就从学校带了一个橡皮模型桥回家,拿一台小电风扇开始做起了实验,并最终得出结论,让塔科马大桥坍塌的罪魁祸首就是“卡门涡街”。 由于大桥有一部分实心侧壁,强风连续吹打壁板,终于形成了周期性涡流。正是这股涡流强迫大桥振动,最后摧毁了大桥。 第二天,冯·卡门马上给马丁州长发去一份电报,强调指出,如果他批准新桥按老桥样式建造,那么新桥也会像老桥那样坍塌。冯·卡门还在《工程新闻纪录》杂志上发表了短文,说明了大桥遭破坏的原因,以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热烈讨论,并同时将文章抄送华盛顿大学的法夸尔森博士,后者当时正负责指导大桥运动的研究工作,桥塌时他就在现场。
西奥多·冯·卡门1920年代在德国亚琛工学院任教 虽然马丁州长当时并没给卡门回电,但一个月后,冯·卡门终于接到联邦工程局局长的电话,联邦政府请他加入塌桥事故专门调查小组。小组成员有著名桥梁设计师,还有分别代表桁架和大梁的土木工程师,他戏谑自己只能代表“风”。 面对桥梁工程师深重的门户之见,凭着精心准备的实验数据和大桥坍塌资料,冯·卡门据理力争,终于说服调查小组同意在新建塔科马大桥之前先要进行各种模型试验,华盛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因此还都获得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合同。 研究的结果是,给桥面的实心侧壁开孔,以防止涡流脱落,并在桥面上增开许多槽,使桥面顶部和底部表面不会产生压力差。重建的塔科马大桥于1950年通车,被称为“强壮的格蒂”;2007年,新的平行桥通车,屹立至今。
1950年10月14日建成通车的新塔科马海峡大桥 西奥多·冯·卡门,20世纪最伟大的航空航天科学家,美国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的获得者,开创了数学和基础科学在航空航天和集体技术领域的应用,被誉为“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才”。冯·卡门一生桃李满天下,国人所熟知的著名科学家、“中国火箭之父”钱学森先生就是他的得意弟子,还有钱伟长、郭永怀、林家翘等也都是。
左起:普朗特、钱学森、冯·卡门(摄于1945年) 先睹为快
1940年,华盛顿州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大事故:塔科马海峡大桥突然坍落。后来查明,破坏大桥的凶手竟是涡流。这是涡流在近代扮演的最神奇的角色。关于“卡门涡街”研究的来龙去脉,书中有表,在此先睹为快(向上滑动阅览)。 我在哥廷根应用风洞解决流体运动问题的过程中,对风洞的兴趣与日俱增。其实,我也觉察到自己的注意力正从其他力学分支渐渐转移到成长中的航空科学上来。在那激动人心的岁月里,空中的高度冒险活动和实验室的重大发现正齐头并进。 不过,当时人们对飞机飞行原理的理解尚处于初期阶段。虽然古希腊人对飞行现象就感到好奇,一块石头在空中掠过时,他们常常问道:“是什么东西推动石头向前飞的呢?为什么它的速度又会慢下来?”当然,他们是无法得出任何科学结论的。亚里士多德曾经试图运用逻辑推理来阐明石块飞行现象:石块后边的压力大于前边的压力,前后两边压力差推动它向前飞行,但他无法解释石块速度怎么会慢下来,最后落到了地上。 一直到16世纪,这个奥秘才被伽利略揭示出来。伽利略解释说:“飞行的石块因受到一个力的作用产生了加速度。如果石块是自由落体,这个作用力就等于石块的自重。飞行的石块又受到空气阻力作用,所以它的速度才逐渐慢下来。”这样,原先的问题就转变为空气阻力怎样使石块减速的问题了。 又过了一个世纪,这个问题才由牛顿系统地作出解答。牛顿从探讨阻力从何而来出发,引进了“惯性”概念。所谓惯性,就是被抛物体保持沿抛射方向运动的一种属性。他说,作用在运动物体上的阻力是由物体和空气分子碰撞产生的。空气分子受压变形产生了两个力;一个力推动物体向上或者向下运动,另一个力则阻滞物体前进。 最后,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飞行物体,若前端向上倾斜,空气分子就冲击它的底面,从而使物体受到一个向上的推力,这个推力叫作升力。阻碍物体运动的那个力就是空气阻力,若无外力克服它,它将使物体运动速度渐渐慢下来。当物体开始运动时所具备的初始能量消耗完,就落到了地面。牛顿运算后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像掷铁饼那样向空中抛出一块平板,那么,作用于平板上的阻力与平板和抛射方向之间的夹角平方成正比。 不久前,我重读牛顿的这段论述时仍觉得他的推理方法很合逻辑。但是,若用牛顿的升力—阻力理论去设计一架飞机,马上就能断定:人类飞行几乎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要想从空气得到最大升力,机翼的倾角应该大,这样阻力就跟着增加;要克服这个阻力,就得装备一台硕大笨重的发动机。反之,如果机翼倾角搞得小,为了产生需要的升力,机翼的面积就得很大。结果,机翼会重得无法起飞。正因为如此,后世许多持牛顿观点的物理学家都宣称,人类不可能靠机翼支撑来飞行。 由于这个升力—阻力理论,牛顿受了多少年的批评。有人指责他阻碍了人类飞行的发展。照我看,牛顿的影响并不像指责的那么严重。因为从前渴望飞行的那些人并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不进行什么计算。所以说牛顿实质上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梦想。何况,根据牛顿的升力—阻力理论,人们立刻就能断定鸟儿也不能飞行。因为根据计算,鸟滑翔时产生的升力也只能承担1/4—1/5的体重。 我敢断定,善于思考的人很快就能意识到牛顿错了。我在本世纪初攻读力学时就知道牛顿错了,还明白错在哪里。 在航空发展过程中,许多飞行员和滑翔爱好者连续不断地去制造各种原始飞机,这是值得庆幸的。从达·芬奇时代以来,这种活动就从未中止过。由于人类渴望能像鸟儿一样飞翔,这种愿望使他们的想象力和天才达到了神奇高度。开初,许多人尝试模仿蝙蝠、鹰和其他飞禽翅膀的模样制作飞机,在机身上安装了由驾驶者操纵的可扑动的翅膀。这种飞机叫做扑翼飞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飞行人员又在滑翔机上装了发动机进行试验。葡萄牙人德·古斯纳克试用过几块安装在一个球体内的强磁铁做飞行动力,外备一台人工鼓风的大风箱,在需要的时候由人力鼓风。法国人勒布里斯用一辆马车拖飞机作为起飞动力。英国人莫伊根据风车原理造了一艘飞船,在船翼中间位置装了空气螺旋桨。1872年,阿方斯·佩诺造了一架以橡胶绳索为动力的飞机,佩诺此后又取得了不少有用的发明。不幸的是,他30岁时便自杀身亡,令人痛惜。 1890年,法国发明家阿达驾驶第一架有动力的飞机上了天。这是一架鸟形单翼机,飞了150英尺1后在着陆时坠毁。1882年,俄国的莫扎伊斯基进行了成功的飞行。俄国人声称那是历史上最早的动力飞行。德国的奥托·利林塔尔是滑翔机先驱者,在空气动力学方面有不少奇特的理论。他造的一架滑翔机可升高到约75英尺,滑翔距离为1/4英里。 利林塔尔说得好:“设想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造出一架飞机也容易,把一架飞机飞上天去,这才是一切!”后来,莱特兄弟在1903年把这种哲学推到了顶峰。他们首次驾着重于空气的飞行器进行了连续飞行。 但是话说回来,航空史上这些冒险活动,我认为只是飞行发展图景的一个方面。从任何实际意义上讲,为了推动航空事业迅速前进,飞行科学必须赶上人们的设想和试验,而且还要替今后发展创建一套理论基础。在这方面,英国航空之父乔治·凯利爵士将牛顿的升力理论拖出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1840年凯利指出,一块平板向前飞行时,作用在板上的升力只与板的升角成正比,而不是与升角的平方成正比。这样,飞机机翼就不需要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大了。凯利是当时最富于幻想的科学家。他还进一步阐明了现代飞机飞行的原理:飞机重量由升力承担,用发动机驱动的推进装置克服空气阻力。从凯利时代以来,尽管飞机越造越大,愈飞愈快,外形逐渐流线型化。从螺旋桨推进过渡到了喷气推进。然而,上述飞行原理却始终没有变。 人类飞行的原理一经问世,科学家们便纷纷起来研究各种物体的外形,以便确定哪种形状能产生更大的升力。比如,凯利指出过,鳟鱼在水里的运动阻力很小,于是人们对鳟鱼体形曲线在空气里运动的阻力情况做了大量研究。结果,情况还真不错。德国利林塔尔的滑翔机试验也表明,若用面积相等的一块平板和一块曲面板做机翼,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曲面板机翼的升力大于平板机翼。这一来更加引起人们对曲线形状的重视。那时候,有志于研究飞行与流体运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急于想搞清楚曲面飞行性能良好的原因。这种研究终于产生了一门新的科学分支——空气动力学,它成了我毕生从事研究的主要学科。 在航空发展初期,飞行理论几乎与实用技术并驾齐驱。这种罕见现象使我比较容易地确定了自己今后的专业方向。在科学史上,像航空那样理论与实践平行发展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比如,热力学基础理论问世后多年,才造出热力发动机;电磁理论发表后,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有人想到运用它来搞电气工程。原子理论的出现也比它的实际运用超前了几十年。 然而,航空方面情况却大不一样。1903年莱特兄弟划时代的动力飞行与升力基本定律的发现几乎是同时的。升力基本定律不仅让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类能够飞行,而且为日后航空的飞跃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升力特性的发现应归功于德国科学家库塔和莫斯科大学数学教授儒柯夫斯基。儒柯夫斯基到哥廷根来讲学时,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在俄国接过了英国瑞利爵士于1887年开始的研究工作,进一步用数学证明了运动物体受空气环流作用,或者说,一个在空气中旋转的物体,由于受升力作用,这个物体的运动将产生变化。 我们凭日常经验完全可以理解这一点。拿一只在空气中旋转着向前运动的网球来说吧,要是用球拍削一个上旋球,球边向前运动边旋转,与不转的球相比,从转球上部通过的空气速度快、压力低,从下部通过的空气速度慢、压力高。结果,转球就受到一个向上的推力作用,从而使球上飘。这个向上的作用力就是升力。同理,如果削一个下旋球,那么,它就比不转的球下坠得快。 早在库塔和儒柯夫斯基之前半个多世纪,炮兵工程师已经懂得这个道理:环绕运动物体旋转的空气会产生升力。他们管这种现象叫“马格努斯效应”。这种力是炮弹的干扰力,它会使旋转的炮弹偏离弹道,不能命中目标。不过,在飞机设计上,“马格努斯效应”却是升力理论的基础,因为机翼外形必须能产生与旋转物体引起的同类型空气环流才行。这样,当飞机作直线飞行时,机翼四周的环流将产生向上的压力,推动飞机上升。这种压力与网球旋转产生的压力完全相同。 空气环流和升力之间的关系是英国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发现的。他是出色的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以惊人的洞察力提出了升力理论的要点,从而在理论上作出了与莱特兄弟的实际飞行同样重要的贡献。从时间上讲,他比库塔和儒柯夫斯基还早6年。不料伦敦皇家学会和物理学会竟以兰彻斯特的论文毫无科学根据而予以拒绝。 结果,这一科学巨篇就这样被两个权威学术机构所摒弃。两个学会之所以铸成这一大错,与兰彻斯特的表达方法大有关系。 在数学上,他不如同辈人普朗特训练有素。由于他运用正规数学形式表达思想的能力较差,因此很难让同行们理解。此外,他又有随意杜撰科学术语的习惯。他把“涡漩运动”叫做“回绕运动”,管“涡流”叫“压力波”。科学家也是人嘛,用他们不熟悉的术语表达的概念,他们自然也会加以排斥。所以说,兰彻斯特同时遭到两个学会的断然拒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这件事,他多年来一直把两个学会贬得一钱不值。令人欣慰的是,若干年后他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承认。现在,人们一致认为他是英国空气动力学发展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但这对他本人来说未免有些为时过晚了。 1908年和1909年,兰彻斯特两度来哥廷根讲学,向我们阐明他提出的那些概念。当时,甚至普朗特对他讲述的内容也感到难以理解。一方面,因为他使用的术语和数学形式异乎寻常;另一方面,他又不会讲德语,而普朗特又听不懂英语。不过,卡尔·龙格完全不一样。龙格的母亲是英国人,所以他英语很好,能和兰彻斯特进行流畅的交谈。龙格是我的好友,因此我从兰彻斯特提出的概念中获益不浅。从那时起,我觉得兰彻斯特的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 1957年,我在伦敦第一届兰彻斯特纪念讲座上讲话时指出,能够分享这位被忽视的天才重新得到重视的荣誉,我感到非常高兴。借此机会,我把他的富有想象力的见解重新复述了一番。兰彻斯特还是运筹学的创造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筹学已经成了组织军事行动的重要手段。他还预见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对飞机发展作出了令人惊异的准确预测。兰彻斯特的著作于1916年公开出版。这本书要求推进世界航空研究;直到1952年,我指导组建北约航空研究和发展顾问团的时候,依然对它感到异常亲切。 到了1904—1905年,人们对升力基本特性已经相当了解。它已成为工程技术人员理解阻力来源和进行阻力分类的必要依据。对飞机发动机推力的合理设计来说,各种类型的阻力已是不可或缺的知识。从此以后,科学家和工程师一直搞了几十年的空气阻力研究。 显而易见,最大的阻力来自空气摩擦,即空气分子从飞行物体表面上擦过去产生的摩擦。但是,当时表达这种摩擦特性的数学方程极其复杂,根本不可能用于机翼设计。这时普朗特跨进了这一领域,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出色的解决方法。他假设计算空气对飞机任何部分的摩擦总效果时,只考虑贴近机体表面的薄薄一层空气。这层空气叫做“边界层”。边界层之外的空气对飞机运动的摩擦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环流理论对边界层空气的流动同样适用。普朗特简化的边界层概念是飞行理论关键的进展之一,按今天五角大楼的流行说法就是一项重大“突破”。 普朗特另一重大贡献是阐明了一种起因不明的阻力(称为感应阻力,或升力的派生阻力)。空气环绕机翼一旋转,必然会引发出这种阻力。普朗特明白,从机翼下方转向机翼上方的空气,在绕过翼梢时就分解成两股涡流(现在称为翼梢涡流或马蹄形涡流)。飞机向前飞行时,这两股涡流就向后延伸,从而诱发出这种阻力。其实,在扬谷时,人们都能看到在空气里形成的这种涡流。 我在哥廷根时及离开那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普朗特一直在全力以赴解决这种涡流的特性问题。事实上,在1914年底我重返哥廷根时,他告诉我说还没有找出解决办法。然而时隔不久,普朗特来了灵感,终于找到解决翼梢涡流的数学根据。他指出,涡流中包含着很大的阻碍飞机飞行的能量,同时还提出飞机设计中处理这种涡流的方法。 运用这一研究成果指导机翼外形设计,就能把翼梢涡流损耗降低到极小,从而在第一批动力飞行后的几十年间使航空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在哥廷根期间就知道他们在研究涡流。最初,我只是感到好奇;过了一段时间,周围同事们的紧张工作不仅把我也卷入思考,而且我还亲自动手为自己的假设做了一系列试验。最后,这项研究终于推动我写出了生平最著名的论文来。 我在1911年的发现阐明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阻力源。它叫作型面阻力。当气流和物体之间附壁作用失效,并在物体后面乱成一股尾流时,就会产生型面阻力。后来,这个发现定名为“卡门涡街”。从那时起,每当我讲解涡流时,总爱借用我的哲学导师庞加莱的一段话作开场白。他讲学经常以“有幸附上敝人名字的这一理论”来开头,借以表明理论比附上名字的那个人更重要。我有些朋友总认为涡流是我发现的,其实并非如此。我这样说倒不是故作谦虚。事实上,在我之前很多年,就有人对涡流进行观察和记录了。记得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博物馆,我看到过一幅油画,画的是圣克里斯托弗掮着幼年耶稣涉水过河。他的脚跟后面就有一排涡流。或许历史学家会问为什么圣克里斯托弗要掮着耶稣过河,而我感兴趣的却是为什么会有涡流。 虽然我思考涡流问题由来已久,但实际推动我着手研究的是实验室里一件偶然事情。那时,普朗特正专心致志测定在稳定流动的水流中圆柱体表面各点的压力,他派一名跟他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希门茨做测量工作。不幸,希门茨发现测出的压力总有波动。不管做得多仔细,水流总是波动不止,压力一直无法稳定。 一开始,普朗特以为压力波动是因试棒表面粗糙引起的。于是,希门茨以日耳曼人那股傻劲,将试棒磨了又磨,量了又量,直到把试棒磨得滚圆为止。然后,他将试棒小心翼翼地放进水槽后开始放水,准备测量。 尽管如此,通过试棒的水流照旧顽固地波动着,使试棒不停地晃动。这时,有人就提出波动可能是水槽本身不对称引起的。于是希门茨再对水槽进行精确磨削和测定,将它牢牢地固定住。结果,这一番改进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每天早上我上班经过实验室时总要停下来问一声:“希门茨先生,还晃动吗?” 他总是失望地回答说:“唉,还是一个劲地晃啊。” 记得某个星期五,我也憋不住了。到周末,我就下定决心来探索晃动原因。我插这一手并非出于同情希门茨,而是纯属好奇,因为我有种预感,觉得用数学可能揭开这个奥秘。要真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够使人激动的。解决这类问题,第一步先要作些假设。我假设水经过圆柱体后一分为二,一股从上边流过,一股从下边流过,经过圆柱体后形成涡流。接下来我考虑了两种可能性:先设两股涡流完全对称,即上下两股涡流在同一时间形成,并同步向前流动。但是,水流运动的数学方程表明流动是不稳定的。因为,涡流位置哪怕有微小差异就会不断扩大,直到流型被破坏为止。 其次,我假设涡流从圆柱体顶部和底部交替出现。顶上那股涡流先形成,底下那股涡流后形成,接着重复交替出现。一想到涡流按这种形式运动,问题的通解便从我头脑中脱颖而出。我清晰地想象到,若两股涡流按一定几何图案排列,其外形就会稳定。不过,只有当两股涡流之间的两个距离保持一定关系,才能出现上述排列:一个是每股涡流中单个涡卷之间的距离;另一个是两股涡流的涡卷之间距离。打个比喻说,两股涡流的涡卷必须像道路两边的电线杆那样排列着向前流动。 到了下个星期一,我就把自己的解法拿给同事们过目。我心里明白已经解决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问题。老实说,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奇妙过程我自己也觉得惊异。我到普朗特那里谈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口气非常平淡地说:“那么,你是有所发现了。很好,把它整理出来,让我送去发表吧。” 1911年,普朗特将我的论文转呈哥廷根科学院。科学院审阅后满意地接受下来。俗话说,人以文传,这篇论文终于使我在国际空气动力学界享有声誉。 文章发表后,还剩下一个小小的问题有待解决:用实验来验证我的理论计算。为此,普朗特派了一名博士研究生鲁巴希来协助我。我俩用水槽和风洞进行试验。结果和理论计算非常吻合。涡流一旦达到我们计算出的距离比例,其运动始终保持稳定。 毋庸讳言,在这篇论文中我采用的计算方法过于简化。因此,我又作了比较精确的计算。接下来的一系列试验结果都证明理论计算正确无误。这样,我便成了论述空气动力学粘滞阻力原理这两篇论文的作者了。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学报上。 自从这个发现被实验证明之后,很多国家都进行了试验。最近几年,威勒教授和西柏林工业大学的一个小组对涡流又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发现理论和实验完全吻合。威勒教授还拍了许多非常瑰丽的卡门涡街照片。我75岁生日那天,他馈赠我一张有75个涡卷的照片,上面书写着:永无止境。 人怕出名猪怕壮,尽管我从未要求涡流理论挂上我的名字,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名字还是挂上去了。这类事情往往会招来风险。1930年,我的论文问世已有20多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名叫亨利·贝纳德的法国教授拍案而起,声称他研究涡流比我要早得多。在我之前,他已经拍下了交替涡流的照片。 事实上,他并非妄言,而我呢,也无意与他争名。于是我回答道:“行啊,如果在伦敦叫Kármán Vortex Street(‘卡门涡街’),在柏林名为Karmanche Wirbelstrasse(‘卡门涡街’),那么,我赞成在巴黎称做Boulerard d’Henri Benard(‘亨利·贝纳德涡街’)吧。”与会者听了这话都真诚地大笑开来。从此,贝纳德和我成了好朋友。 涡街有什么重要意义呢?首先,它为在一定条件下运动的物体提供了一幅尾流结构的科学图形。其次,了解了尾流结构之后,才第一次能对球、圆柱体之类曲面物体的型面阻力进行精确计算。借助于算出的数据,科技人员就明白了如何利用流线型来最大程度地减少型面阻力。因此,它成了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 此外,涡流理论还有其他用途。用它能将从前许多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解释清楚。比如,拿无线电发射塔、大烟囱、潜望镜及其他细长物体在中等风速下的颤振来说,现在才明白,这种颤振是其尾流中交变涡流引起的。瑞利勋爵(后来我在剑桥幸会过他)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里,还运用涡流理论解释风弦琴的各种音调。 我有个颇具才华的学生名叫卡尔文·冈维尔,现在航空喷气公司任职。他发现涡流理论对解决水雷和潜艇的“螺旋桨振鸣”问题很有用。由于螺旋桨在水下以某一频率振动时会发出啸声,很容易被声呐发现,甚至美国最新式核潜艇“鹦鹉螺”号也有这个毛病。我和冈维尔一起研究后提议改进螺旋桨结构,以消除这种招惹麻烦的啸声。 1940年,华盛顿州发生了一件离奇的大事故:塔科马海峡大桥突然坍落。后来查明,破坏大桥的凶手竟是涡流。这是涡流在近代扮演的最神奇的角色。后文中将有专章对此事详加解释。 从哲学意义上讲,我发觉涡流是科学史上有名的现象。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曾断言,每个天体都是宇宙中一个巨大旋涡的中心。开尔文勋爵则着眼于微观世界,提出一种用涡流解释原子结构的理论。由于涡流的稳定性极难计算,他跟笛卡儿一样,最后只好放弃了这一理论。过去有一段时间,涡流甚至被认为是宇宙间一切实体的构成要素。 毫无疑问,古代人就发现涡流中潜伏着某种危险,对男人特别有威胁。《圣经》上讲:“当心陌生女人的眼睛,她的眼睛就像个旋涡。” 他帮助中国建立第一支现代化空军,他也是钱学森敬重的老师 纪念 | 钱学森: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张生 | 我仍然坚信让思想自由敞开为好
END 本期编辑 | 陈丽英 图书编辑 | 曹珍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