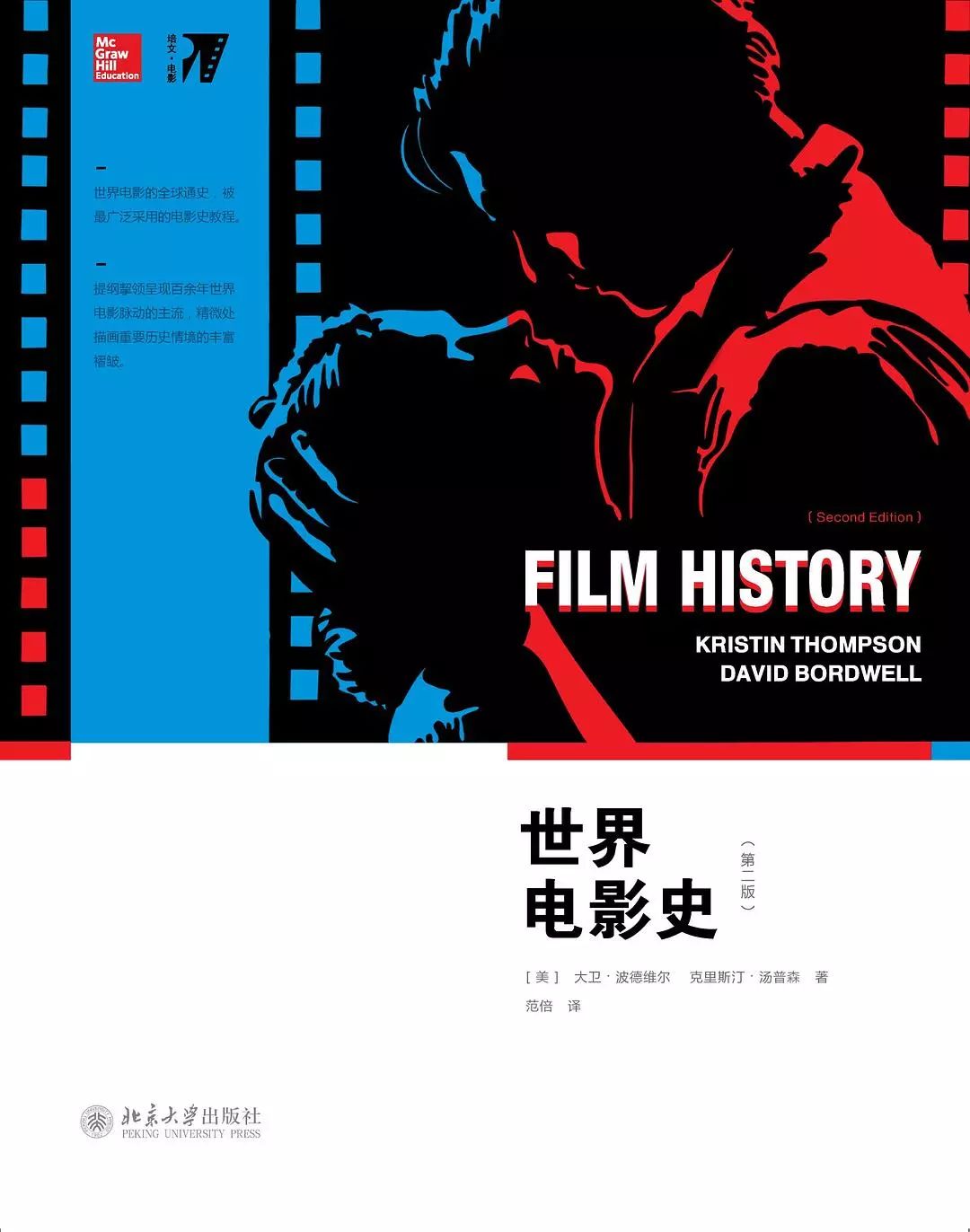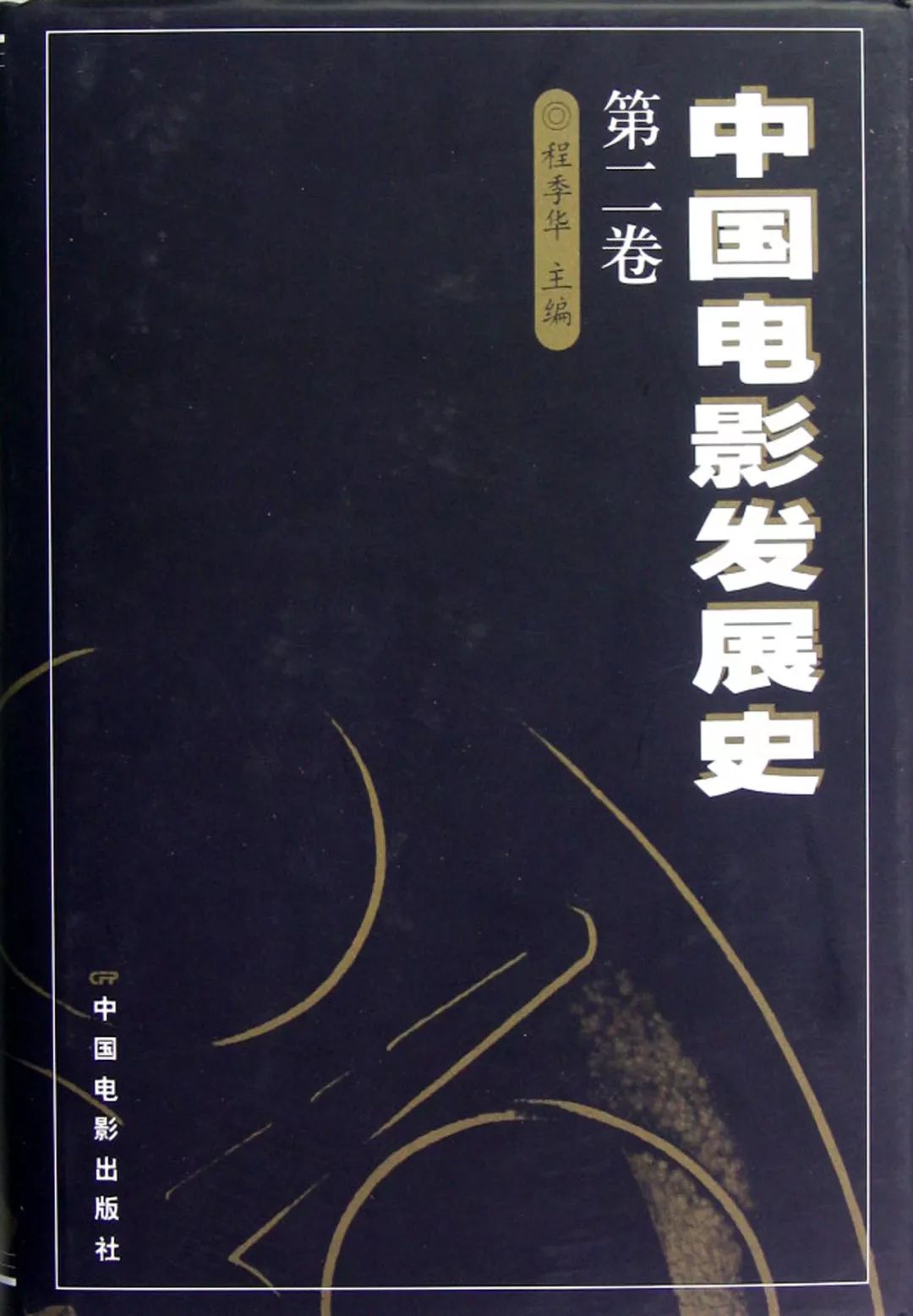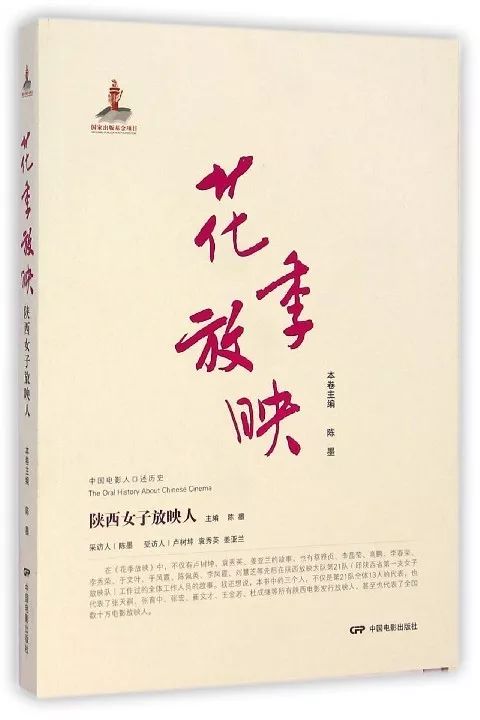《当代电影》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冷战题材的欧美电影 › 《当代电影》 |
《当代电影》
|
一、全球电影史里的中国电影: 欧美视域里的“非连续”性
《世界电影史》(第二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史视域里的电影史书写,亦即全球电影史的理论与实践,在欧美各国的电影史研究中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非美国电影”或“非欧美电影”亦即亚、非、拉电影或“第三世界电影”,也正在日益显露其电影史的重要性。(5)其中,较具代表性并被翻译成中文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美国学者克里斯汀·汤普森(Kristin Thompson)与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合著的《世界电影史(第2版)》(Film History,2nd Edition,McGraw-Hill Education,1994,2003)(6)、英国学者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Geoffrey Nowell-Smith)主编的《牛津世界电影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World Cinem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7)以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rmery)与荷兰学者克拉拉·帕福-奥维尔顿(Clara Pafort-Overduin)合著的《世界电影史(第2版)》(Movie History:A Survey,2nd Edition,Routledge,1991,2011)(8)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牛津世界电影史》仍以“世界”(World)一词表明电影史所涉的“世界”或“全球”范围之外,其他两部“世界”电影史著述,均在书名中直接省略了World或Global。 早在美国学者罗伯特·C·艾伦(RobertC.Allen)和道格拉斯·戈梅里合著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Film History:Theory and Practice,McGraw-Hill,1985)一书里,便讨论过在英语世界的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之所以倾向于以美国电影为主要线索和内容取代世界或全球电影史的原因和动机。作者指出,尽管好莱坞霸权或“好莱坞风格”会被一些学者称为“文化帝国主义”,但也不得不承认,要想获得电影史“全部”事实的工作,其实都是“徒劳无益”的;另外,电影史虽然是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开放的系统,但基于好莱坞电影在工业、美学和文化等方面的主导地位,任何电影史研究都会不可避免地侧重于美国电影。(9)这样的理解和认知,虽然是一种立足于电影知识生产与传媒经济力量的权宜之计,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全球电影史观念及其写作实践中的欧美中心倾向找到了“开脱”的依据。 大卫·波德维尔与克里斯汀·汤普森的《世界电影史》就是如此。在其专门探讨“电影史和做电影史的方法”的“引论”中,作者自述其“核心意图”,就是要探讨“电影媒介在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使用方法”,并且试图凭借对国际和跨文化影响怎样起作用的观念,来平衡对于“重要国家”的电影贡献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追溯“跨文化”和“跨地区”的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已经存在的一个“全球化”的电影市场。 不得不说,在所涉国家(地区)的多样化、研究视域的深广度与具体论述的生动性等方面,大卫·波德维尔与克里斯汀·汤普森的《世界电影史》均令人耳目一新。然而,由于电影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开放性”,《世界电影史》仍未从整体上突破传统电影史中的“影响-接受”模式,无法从“交互”经验和跨国(跨地)行为的角度重新考察世界各国的电影关系。至于中国电影,则在第三部分“有声电影的发展:1926—1945”第十一章“其他制片厂制度”中第一次出现,并以“中国:受困于左右之争的电影制作”为题跟这一时期的英国、日本和印度电影并列在一起。按作者观点,在制片厂体系的电影制作所可能采用的“多种形式”之外,中国的电影业则“努力仿效西方的样板”,“最终却被政治环境摧毁”(第335页)。然而,根据已有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将会发现这些论述往往不够准确,其观点也大多似是而非。 这种试图将中国电影与其他国家(地区)电影尤其好莱坞电影进行简单比照的论述方式,在第四部分“战后时期:1945年—1960年代”第十八章“战后非西方电影:1945—1959”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节,以及第五部分“1960年代以来的当代电影”第二十三章“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政治批判电影”中“中国:电影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节更是得到集中体现。特别是对《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小城之春》(1948)、《三毛流浪记》(1949)、《祝福》(1956)、《舞台姐妹》(1965)以至《红色娘子军》(1971)等冷战时期经典影片的阐释,大多仍在与相应的“好莱坞风格”或欧洲电影的联系中肯定其历史价值。(10) 或许,正是因为无法对中国电影的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及其风格变迁予以整体性观照,《世界电影史》才会将其对中国电影的分析和评判,始终定位于对好莱坞或欧洲电影,而非苏联电影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影响所作的反馈之中,并在对冷战及其前后中国电影的“非连续性”表述中,将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描绘成一种相对稳定并渐趋僵化的风格样态。这样的论述,显然无法满足中国电影学术界对“世界电影史”或“全球电影史”的期待。实际上,在“引论”中,作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明确表示:“尽管本书是要勘测世界电影的发展历史,但我们却不能以‘什么是世界电影史’这样的问题开始我们的工作。它不会给我们的研究和组织我们找到的材料带来任何帮助。”(第14页)——并以此延宕甚至拒绝对“世界电影史”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探讨。大卫·波德维尔与克里斯汀·汤普森的电影史观,因此遗憾地止步于“宏大理论”的构架面前;但问题已经提出:基于全球电影史和民族电影史相互交汇的视角,回答“什么是世界电影史”这样的问题,恰恰应该是研究工作的开端。 相较而言,作为一个对电影史理论进行过专门研究的电影史学者,道格拉斯·戈梅里的“电影史”写作反而更加直接甚至不无偏激,也同样无法满足电影史学界对“世界电影史”或“全球电影史”的期待。因为以电影史的“经济”维度为核心,《世界电影史》决定以“征服了全球电影市场”的好莱坞为全书的主线,但也并不想把所有其他国家的电影史都简单地看做是“对好莱坞的回应”;在道格拉斯·戈梅里看来,法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电影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历史之中,探讨的是不同主题,具有独特的外貌和风格;它们有自己要讲的故事,并用自己的方式讲述,并不一定是要与好莱坞分庭抗礼,但它们也不得不应对美国电影的经济实力并想方设法在这个行业立足。基于这样的认知,《世界电影史》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均以好莱坞和欧洲的“西方电影”为主,只是在第三部分“电视时代(1951—1977)”的最后一章,才开始纳入“电影工业的不同选择:苏联、澳大利亚、日本及东欧、南美洲”。中国电影第一次出现在“电影史”中,是在第四部分“从视频到数字时代(1978—2010)”第十三章“1978年以来的当代世界电影史”,跟“丹麦的道格玛95”和“印度电影”并列在一起;1978年以前的中国电影史,基本付诸阙如。尽管作者指出,印度、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丹麦道格玛电影“将来”会被写入电影史,是因为他们的“叙事方式”和“摄影技巧”越来越吸引西方学者的注意;但作者并不相信某种“全球化”的电影世界,而是坚持认为,“民族电影仍然会抵抗好莱坞,并努力保持其民族身份”(第356—357页)。在经典的“影响-接受”与“霸权-抵抗”电影史模式之下,民族电影仍被处理为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电影史”个案;中国电影也基本没有过去的历史,或者只是“电影史”的“将来式”。 这样,在“电影史”中克服或隐或显的欧美中心主义,或者在全球电影史(“全球电影机制”)与民族电影史(各地电影特性)之间寻找“平衡”,便成为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主编的牛津版《世界电影史》遇到的最大挑战并取得的显著成绩。 为了在“世界电影史”写作中“平衡”好莱坞单一的全球性与民族电影多样的差异性,牛津版《世界电影史》不仅“有幸地呼召了一个作者团队”,试图从专业知识和多种视角层面,展现一幅“复杂的世界电影图景”,并努力辨析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电影在不同方面的“互相牵制”和“互相影响”的特征。这便使世界电影史中的“民族电影”,得到了专业的民族电影史学者相对深广地关注和阐发,避免了一般世界电影史中“民族电影”叙述普遍出现的知识错漏和意图谬误。在对中国电影的观照中,裴开瑞(Chris Berry)之于“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丘静美(Esther Yau)之于“革命之后的中国电影”、李焯桃(Li Cheuk-To)之于“香港流行电影”与叶蓁(June Yip)之于“台湾新电影”,显然都是不可多得的一时之选。尤其丘静美的部分,对“革命之后的中国电影”亦即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内地电影,予以较为简略却也颇为深入的考察,要言不烦却又切中肯綮。例如,在讨论1956—1959年“百花齐放”和“反右”时期的电影时,丘静美便从中外互动、比较生发的综合视角进入,可谓独辟蹊径。 毫无疑问,牛津版《世界电影史》为全球电影史里的“民族电影”叙述提供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成功范例;尤其当它将20世纪60年代前后以来的“世界各国电影”(包括上述丘静美、李焯桃与叶蓁撰述的中国电影部分)全部纳入“无声电影(1895—1930)”和“有声电影(1930—1960)”之后的“现代电影”框架之中,便在最大限度上为“民族电影”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预留了巨大的阐释空间。这也是世界/全球电影史写作中最值得重视的进展。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还从观念和经验的层面探讨了“世界电影”与“民族电影”的关系,冷静分析了牛津版《世界电影史》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利弊得失。在他看来,在“民族电影”或“世界电影”的名目之下,牛津版《世界电影史》对“世界电影”的分类,尤其是以类似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或第三世界这样的概念为基础进行的分类,都有“高度的不利之处”。因为按照这种分类法,“民族电影”或者“世界电影”只是简单地、粗略地从西到东的一种“地理秩序”。(“全书导言”,第1—7页) 确实,牛津版《世界电影史》对“世界电影”或“民族电影”(中国电影)的整体观念及其内部的丰富复杂性,仍然缺乏理论的准备和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例如,在“1949年前的中国电影”之后,附上弗雷达·弗赖伯格(Freda Freiberg)撰写的“李香兰(山口淑子)”作为“特别人物介绍”,反而容易造成读者对“民族电影”的巨大迷惑;也是在这一部分里,有关中国电影三个“黄金时代”的观点,也明显承袭单一美学维度的历史判断,并在美学上将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电影置于尴尬的境地;正是在“黄金时代”的价值观念导引之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电影及其现代性,被描述成对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经典的革命现实主义惯例”)的“瓦解”和“重新定义”。作为“民族电影”的中国电影,在牛津版《世界电影史》中,仍然无法获得其本应具有的整一性。 二、社会主义中国电影: 国族视域里的“断裂”论
《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 作为“民族电影”的中国电影整一性的缺乏或丧失,不仅是世界/全球电影史里中国电影的普遍命运,而且是中国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较难跨越的“黑洞”或“阴影”。尤其在对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历史阐释中,有必要正视并深入反思国族视域下的各种或隐或显的“断裂论”。 “断裂”论始于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1963)。《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电影史观及其出版后在海内外的各种遭际,深刻地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史观念与中国电影史写作。 其实,基于其初版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史》本身即可被视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电影历史建构的一部分。其电影史观,自然也是这一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明确体现。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引言”部分,编者花费较多篇幅,高度赞扬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电影思想与苏联电影的辉煌成就,并将其与“世界各国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进步电影的发展”以及“我国进步电影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值东西方冷战时期,《中国电影发展史》当然不可避免地表达了极为鲜明的“电影冷战”或“冷战电影”意识,并以此总结出世界电影史与中国电影史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规律”。(11) 正是在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这种电影史观的指导下,《中国电影发展史》将1896—1962年间的中国电影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初稿定型的1963年,第四个时期(1949—1962)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中国电影发展史》里并未真正地展开论述,而只是作为一个电影史阶段的构想,留存在全书“引言”和最后一章的结尾部分。现在看来,第四个时期的影史构想,并非可有可无的提议,更不是解决通史问题的折衷方案。相反,对这一时期亦即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伟大成就”予以充分的肯定,才是《中国电影发展史》得以写作并获得出版的内在原因。实际上,通过“崭新的发展时期”“无可比拟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以及“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电影史写下了最为光辉灿烂的篇页”等表述方式,《中国电影发展史》已将这一并未真正展开论述的电影历史,跟此前三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划清了界限(“引言”第1—16页)。 只是在该书重版时收录的“重版序言”里,陈荒煤才在对《中国电影发展史》在“文革”中被打成“毒草”的遭遇予以反思,并在对曾被否定的“建国十七年来的人民电影事业”予以“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更加明确地为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接续”了一部分电影历史的脉络。在这样的表述中,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内蕴,确实变得更加丰富,但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史里非“革命”、非“进步”的部分(如占全部出品最大多数的商业电影,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下的“沦陷电影”等等),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和理性的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学术界开始反思以往电影史观的局限性,并提出了“重写”电影史的各种观点与方法。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便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亦即1949—1984年“当代中国”的电影历史,并被纳入《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12)在某种程度上,《当代中国电影》是《中国电影发展史》分期构想中未能具体展开的“第四个时期”的最终完成,并在时间向度上延展到了1984年。尽管两者初版时间相差二十多年,但对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总体描述和基本评价,应该还是一致的。 当然,相较于《中国电影发展史》,在电影观、历史观和电影史观等方面,《当代中国电影》仍然有所拓展,甚至不无突破。在第一章“当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渊源”里,撰述者尽管同样强调了“当代中国电影”作为“人民民主革命电影的延续和发展”的“新型艺术”的特征,却也第一次提出了将“旧中国”的“民族电影”纳入“当代中国电影”历史脉络的主张;在第二章“当代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概况”里,甚至描绘了一幅电影艺术家“向现实生活学习,向古典、民间学习,也向外国学习”,逐步走上“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的宽广道路”的美好图景(第48—49页)。但遗憾的是,基于对“旧中国”的“腐朽没落”、好莱坞等外国电影的“倾轧”以及电影经营者在“赢利目的”下形成的“粗制滥造之风”的一般性理解,在具体的论述中,《当代中国电影》仍然从整体上否定了“旧中国”的“民族电影”;作为替代,只是将“古典”“民间”和“外国”列入“民族新电影”需要学习的对象和传承的序列之中。 同样,基于对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从“资本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这种“根本性变革”的认定,《当代中国电影》从“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对象和“新”的选择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当代中国电影创作的“新”气象及其“除旧布新”的巨大成就。这也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电影》所张扬的“民族新电影”,是在有意克服旧中国“民族电影”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冷战结束之前,中国电影史写作实践里的社会主义中国电影,始终没有在“民族电影”的视域里跟1949年以前的中国早期电影联系在一起。 1985年9—12月,美国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应邀在北京大学开设当代西方文化理论课程并引起轰动。1989年底,杰姆逊的《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也在专业电影理论刊物《当代电影》上译载。(13)杰姆逊有关“电影在现代社会中和文学的地位是有相似之处”的观点,以及“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等判断,对姚晓濛、戴锦华、张颐武、王一川等文学、电影学者产生较大影响。正是在第三世界批评以及第三世界文化、第三世界电影等学术话语的促发下,他们集中讨论了跟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与电影等相关的第三世界电影和文学命题,并以“民族寓言”“文化权力”和“他者话语”等概念,“验证”或“重构”了杰姆逊有关“第三世界本文”的表述。(14) 其中,戴锦华的《新中国电影:第三世界批评的笔记》,可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第三世界批评”讨论社会主义中国电影(20世纪50—70年代)的代表作,但也充满各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语裂隙。(15)戴锦华指出,按弗·杰姆逊首倡的第三世界批评的“寓言”本文的读解模式,从潜在于本文中的复调对话层面来读解经典的新中国电影(“十七年”电影,或曰第三代导演的创作),还不能构成第三世界批评视野中的寓言式本文。第三代导演的叙事行为是一种充分自觉的,并为主导意识形态话语所规范的政治及社会象征。它是高度政治化的、亦为主导意识形态话语规定为“民族化”的,但这一“民族化”之民族,并不是第三世界批评视域中的“民族”内涵。 在戴锦华看来,“十七年”电影艺术产生的时代,中国社会首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严酷斗争,继而由于中国与苏联及东欧的决裂而处于一种被封锁、被隔绝的“闭锁”状态,资本主义世界、帝国主义势力作为敌对势力是主导意识形体话语的主部;但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十七年”的社会文化本文中资本主义世界(第一世界)只能是一个麦茨所谓的“想象的能指”、一种神话式的在场与缺席。在跟弗·杰姆逊的第三世界批评及其“民族寓言”展开协商对话的过程中,戴锦华充分强调了“新中国电影”作为“民族独白”的特定内涵,及其作为一种冷战时期“被封锁、被隔绝”状态下的“独立、自足的文化”而呈现的“连续性与整一性”。作为对弗·杰姆逊观点的肯定性呼应,戴锦华认为,一种狭义的、第三世界批评视域中的寓言本文与本文中的复调对话只可能出现在197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中国的电影本文,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起跳、蜕变、发展,渐次充满了“裂隙与异质”,并在前工业社会的现实与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之间,挣扎于“历史无意识的重轭”与“他者视点的俯察”之中。 在这里,戴锦华基于文化理论与电影实践的全球性互动,以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对作为“民族电影”的中国电影的“连续性与整一性”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主要从知识取向的层面,对此前以政治为尺度和价值为导向的电影史观念予以批判性反思,并为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历史建构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新中国电影真是一种具有“连续性与整一性”和独立、自足文化特征的“民族独白”,那么,它到底跟1949年以前的中国早期电影和1979年以后的“当代”中国电影构成怎样的关联性?在戴锦华的文章里,1949年以前的问题被悬置,1979年以后的问题则被表述为“渐次充满了裂隙与异质”。不得不说,正是在新的建构之中,历史再次发生断裂。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借助2013年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对“中国十七年电影研究”的关注,戴锦华也意识到了此前论述存在的问题,并开始重新思考书写新中国电影史的原则和方法。(16)戴锦华强调,不能仅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理解和思考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必须瞩目或意识到20世纪50—70年代历史自身绵延中的“差异与裂隙”;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剧变与新时期初年的中国电影,无疑是这一历史结构的“有机连续”。尽管以第四代、第五代登场为标识,中国电影的确经历了一次“断裂性的变革”,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另一个意义的“变异和绵延”,将其视为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电影的“最后辉煌”。 至此,戴锦华发现并解决了社会主义中国电影历史建构中的几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基于全球化与冷战史的分析框架,在新中国电影与197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电影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关联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民族电影”整一性的缺乏或丧失带给中国电影历史叙述的整体焦虑。毋庸讳言,由于1949年以前的问题始终被悬置,更由于中西语境中对“民族”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各个历史分期里的“民族”电影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全面考察和深入辨析;在对新中国电影的讨论中,也较少涉及其历史自身绵延中产生“差异与裂隙”的内在原因及其动力机制。在戴锦华的判断中,一方面将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民族电影”看作一次“伟大却无功而终的尝试”,另一方面又将其当作在“绝无先例可援引”的情况下,“试图创生全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的努力”。跟陈荒煤主编的《当代中国电影》相比,戴锦华之于新中国电影历史价值的评判,由于更加强调断裂、展示差异,反而显得更加游移不定甚至言过其实。对新中国电影研究而言,这样的“全新”表述,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族电影”价值观的困惑,又无异于思想掘进中令人猝不及防的一次急速撤离。 三、冷战全球电影史 与跨国民族电影的生成
《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 尽管如此,除了第二届中国电影史年会组织的“中国十七年电影研究”以外,从新世纪以来迄今,对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电影的研究,在海内外华语电影学术界,以及国内组织的各种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的各种电影史著述中,都得到了更加集中并愈益深广的分析和探讨。(17)随着史料的挖掘、视野的拓展与史观的转型,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电影之于1949年之前与1979年以后中国电影的内在关联性,也逐渐得到更加明确地体验和认知。同样,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电影(20世纪50—70年代)历史建构的次第展开,中国电影史也正在其具体的历史分期之间,以及各个分期内部的冲突与张力之间,努力超越“非连续性”造成的支离破碎感,并试图克服“断裂”带来的认同困惑与价值对立,逐渐形成一种跨国意义上的“民族电影”的主体性与整体观。一种跨国民族电影史的生成,正在中国电影学术界的期待之中。 在此过程中,作为新中国电影的“亲历者”和“过来人”,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2002)到《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2011),孟犁野对新中国电影艺术的两次历史建构,不仅能在“近距离观察”和“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以“冷静”“客观”的治史态度,提出了一些很有“思想深度”的见解,(18)而且通过两次写作的比较和反思,对“新中国电影”的历史撰述提出较具启发性的观点和结论。在《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结束语”里,作者曾认为“在1949年前中国电影史上影响不小的武侠片、侦探片、恐怖片、言情片等,基本上绝迹”(第375页),但在《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后记”里,作者便就此做出了自我反省,认为上述类型片的“遗迹”并未断绝,“只是进行了一次顺应新时代的变异”,至于电影语言层面上的延续“更为明显”,“不仅出自于20世纪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本土电影,其源头还在于西方电影尤其是美国好莱坞经典电影这个‘舶来品’的深层影响”(第507页)。 这种现身说法式的观念转变,也就意味着,从21世纪开始以来,包括孟犁野在内的一代中国电影史学工作者,已经从主要强调国家意志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新中国电影的影响,到更加关注新中国电影的历史渊源及其跨国因素和全球视野。尤其随着全球冷战史的展开,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全球电影史里的跨国民族电影,将会在更多的电影史研究中,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阐发。 现在看来,从冷战全球史视野观照社会主义中国电影,需要重新回到具体而微的历史“现场”,进一步从国家制度、政治权力及其相互沟通、彼此借鉴的显在层面,在“复调对话”而非“民族独白”的意义上,考察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影片交换、集中展映与交流互访、合作拍摄,外交使领馆之间的电影招待、例行放映与影片赠予、影人联欢,以及在卡罗维·发利、莫斯科、洛迦诺、戛纳、塔什干等国际电影节的出场亮相,这都是社会主义中国电影在冷战时期的跨国经验和全球想象,值得更进一步地分析阐发。(19)在此基础上,再深入考察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与以苏联电影为首的,包括朝鲜、越南、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古巴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中国观众从《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乡村女教师》《牛虻》《奥赛罗》《海之歌》《一个的遭遇》等苏联电影,《游击队的姑娘》《春香传》《卖花姑娘》等朝鲜电影,《山鹰之歌》《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像》等阿尔巴尼亚电影中“看”到了什么?中国电影又从这些电影中“学”到了什么?反之,国外观众从《白毛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祝福》《革命家庭》《红色娘子军》《神笔》《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等中国电影中“看”到了什么?海外电影又从这些电影中“学”到什么?等等,都是有待探索的话题。另外,以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为分界线,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与苏联电影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电影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自我期许中,中国电影开始取代曾经亦步亦趋学习效法的苏联电影,成为社会主义及世界各国进步电影的“良师益友”。这种“师友”关系的“翻转”及其复杂性,正是社会主义中国电影历史建构中值得讨论的重要议题。 第二,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与日本、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进步电影之间的沟通与共鸣。基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分野,在社会主义中国,象征性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工业绘制了一幅介于生死之间的两极化图景。这是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影业的“垂死性”(“萧条景观”)与其进步电影“生命力”(“蓬勃发展”)之间不可移易的神话。“神话”一方面阻挡了这些国家的商业类型电影、现代主义电影和艺术探索电影等进入社会主义中国,但也因其具备进步电影的“生命力”而将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带到了中国观众面前。其中,《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米兰的奇迹》《罗马11点钟》《她在黑夜中》等意大利电影,《箱根风云录》《没有太阳的街》《二十四只眼睛》《浮草日记》《裸岛》《松川事件》《啊,海军》等日本电影在中国的放映和传播,成为西方电影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中国银幕上极为难得的经历和养分。 第三,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与印度、埃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和巴西等亚非拉各大洲第三世界电影之间的关联性。将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纳入进步电影与电影外交的版图,是社会主义中国电影“国际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中国电影里,既有《两亩地》《暴风雨》《流浪者》《旅行者》《章西女皇》等印度电影带来的观影热潮,又有《革命的故事》《战斗的古巴》《十八号封地》等古巴电影引发的不同思考。在冷战全球史的框架中,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不仅是独具特色的“民族电影”,而且是并不“闭锁”的跨国民族电影。 从冷战全球史视野观照社会主义中国电影,还需要重新回到纷繁复杂的冷战“语境”,进一步从电影冷战的时代征候、冷战电影的风格选择以及好莱坞的全球化战略与同质化工程等隐在层面,在“拒纳”亦即“排拒”与“接纳”双向流动的意义上,考察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内在关系。毋庸讳言,在电影冷战的时代里,如果没有好莱坞以“敌对”一方的代表资格而存在,那么,作为冷战电影的社会主义中国电影,自身也将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诚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电影银幕上,为了清除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以及好莱坞的“毒素”,只在1960—1961年间向全社会公映了一部“在战斗中诞生的美国进步影片”《社会中坚》,这也是从20世纪50—70年代公映的唯一一部美国电影。然而,好莱坞对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影响,其实并不可能消失,而是一直以潜隐的方式作用于中国电影的题材选择、影音运作和风格样式。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全球体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开始,好莱坞的电影语法与“好莱坞风格”即已“镌刻”于包括中国电影在内的世界各国电影之中,甚至成为世界各国电影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走上影坛的中国电影人(以第三代导演为代表),他们大多也是在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熏陶中获得了电影感知,习得了电影技艺。诚如孟犁野所言,新中国电影的源头,仍在于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经典电影这个“舶来品”的深层影响。 从冷战全球史视野观照社会主义中国电影,还需要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在多国交互与个人经验的意义上,更多关注电影活动里的非国家行为与非民族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将对“民族电影”的一般理解转换为跨国民族电影。为此,除了国际电影节的交流沟通以外,多国组织或参与的国际电影会议,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一些制片合作、电影工作会议、电影技术工作会议等等,都能为理解和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提供新的角度、带来新的发现,也应成为其历史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例如,1957年9月,在波兰华沙举行了共有15个国家近四百名代表参加的第三届国际电影技术会议。会议的主要成就是成立了由英国、保加利亚、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南斯拉夫、民主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苏联和波兰参加的(印度和日本也准备参加)电影技术协会国际联合会,并选举法国人莱德·奥兰担任联合会主席。该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电影界科学、工程和技术工作者的联系,彼此交流技术经验和思想。在这届大会上,讨论了宽银幕电影技术的统一问题。电影技术工作者认为,必须确定一种广泛承认的,并使现有影院都能放映宽银幕影片的标准。(20)正如当时的报道所言,这种国际会议,能够相互交流电影技术新成就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对电影技术落后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会议次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即拍摄了中国第一部35毫米彩色宽银幕立体声故事片《老兵新传》,在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技术成就银质奖。将《老兵新传》以及其他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纳入全球电影(技术)史的脉络,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举措。(21) 除了多国交互之外,口述史、编年史与个人经验也是社会主义中国电影历史建构的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此前的历史写作,较少将口述史、编年史与个人经验纳入历史叙述,尤其是针对以国家意志和政党意识形态为主要脉络的社会主义中国电影,更是缺乏个性的感知与个体的丰富性。全球电影史里的跨国民族电影,迫切需要在口述史、编年史与个人经验的层面,重建电影的感性维度与历史的具体化图景。值得庆幸的是,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组织编撰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便为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留下了大量属于个人经验的历史文献。其中,陈墨主编的《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22)通过采访记录陕西省第一支女子放映队全体工作人员的故事,深入挖掘陕西女子放映队的个人命运、性别遭遇、地域特征与历史细节。这样的工作,不仅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历史建构,而且有助于在全球电影史的框架里,生成一种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的跨国民族电影史。 (李道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100871) 注释 (1)任东波《全球史观与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史学集刊》2013年第6期,第50—53页。 (2)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第26—37页。 (3)陈拯《全球史视角下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兴起、特征与挑战》,《国际观察》2015年第2期,第139—157页。 (4)在《冷战史研究与中国电影的历史叙述》(《文艺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1—110页)与《跨国构型、国族想象与跨国民族电影史》(《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第101—109页)等论文中,笔者尝试对相关问题展开过讨论。 (5)在美国学者杰拉德·马斯特(Gerald Mast)所著《电影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Movies,1971)一书及其此后的各种版本里,尽管也意识到了不能忽略“非美国电影”的“表现力”,但仍以“最多的篇幅”讨论美国电影的实况;有关中国电影,全书始终只字未提。参见[美]杰拉德·马斯特《世界电影史》,陈卫平译,台北:“中华民国”电影图书馆出版部1985年版。 (6)[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世界电影史》(第2版),范倍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2009年和2018年,McGraw-Hill出版了该书第3版和第4版。 (7)[英]杰弗里·诺维尔-史密斯主编《世界电影史》(第1-3卷),杨击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美]道格拉斯·戈梅里、[荷]克拉拉·帕福-奥维尔顿《世界电影史》(第2版),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 (9)[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李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序”第1—3页。 (10)例如,针对桑弧导演的影片《祝福》,《世界电影史》指出:“这部影片除了故事的冷酷悲惨之外,像1950和1960年代的大部分中国电影一样,展现了通常是与好莱坞联系在一起的华丽流畅的制作风格,包括精心制作的室内景和色彩丰富的摄影技术。”(第524页)针对“样板戏电影中最著名的一部”《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电影),《世界电影史》仍然表示:“中国的电影制作者从未采用过直接电影的方法,更愿采用长期实践的摄影棚方法,让人想起1930年代的好莱坞。《红色娘子军》中,表演就像是拍摄于一个剧场舞台上,使用了人造的大树和幕布。”(第179页) (1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引言”第1—16页。 (12)陈荒煤主编《当代中国电影》(上、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3)[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译,《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第45—57页。在此后中国学术界,对此翻译文本存在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过批评。 (14)在《中国电影批评史(1897—2000)》(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695—716页)里,笔者介绍过杰姆逊的著述和观点及其对中国电影批评的影响。 (15)戴锦华《新中国电影:第三世界批评的笔记》,《电影艺术》1991年第1期,第46—55页。 (16)戴锦华《序二:治史时代》,载李镇主编《中国“十七年”电影研究》(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17)出版的主要成果包括:尹鸿、凌燕《新中国电影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洪宏《苏联影响与中国“十七年”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傅红星主编《社会变迁与国家形象——新中国电影60年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电影博物馆编《新中国电影与观众的变迁——中国电影博物馆2009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年版;王广飞《十七年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年版;牛颂、饶曙光主编《全球化与民族电影——中国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李道新《中国电影:国族论述及其历史景观》,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年版;金丹元等《新中国电影美学史(1949—200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李焕征《银幕上的乡土中国:十七年(1949—1966)农村题材电影中的民俗与日常生活方式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史静《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内外的身体话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硕果《“十七年”上海电影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柳迪善《新中国译制片史(1949—1966)》,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年版;余纪《国家建构的一个侧面:“十七年”电影中的边疆叙事与国族认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8)孟犁野的这两部著作,分别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和2011年出版。在后一部著作“序”里,李少白还指出,这部著作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中,“蕴含着他对这段影史独特的审美经验与价值判断”。 (19)还有从国外引进而未公开放映的“内参片”和部分译制片等之于相关影人和观众的影响。 (20)《华沙举行第三届国际电影技术会议》,《电影艺术译丛》1957年第12期,第97页。 (21)另外一个例证,也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会议对社会主义中国电影的影响。据《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第6版)报道,1960年11月,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了第三届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苏联、中国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讨论了关于社会主义电影现代题材的创作以及提高作品思想性问题。中国代表张水华、林杉和陈荒煤在会上就电影艺术必须迅速而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新的英雄人物形象和正确反映革命战争等问题先后作了发言。会议期间,与会者观摩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影片,其中也有中国影片《万紫千红总是春》。经过六天讨论,会议闭幕时,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指出,当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日益蓬勃发展,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运动,以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时刻,社会主义电影应该更深刻全面地反映现代题材,创造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新的英雄形象。公报中说,在创作实践中,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对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思想。——1963年1月,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22)陈墨主编《花季放映:陕西女子放映人》,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版。 编辑:谢鹏翔 校对:李佳蕾 d d d y z z 公众号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