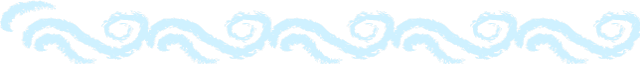你真的了解翻译吗?看完这些问题再回答也不迟!(二)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你了解它吗翻译 › 你真的了解翻译吗?看完这些问题再回答也不迟!(二) |
你真的了解翻译吗?看完这些问题再回答也不迟!(二)
|
译者的翻译动机也是一个棘手的概念,其既可以是译者自发形成的,也很有可能是外部强加的。如果是译者的主动选择,不妨归之为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如果是外部力量(如出版社、赞助人等)强加的,就可以认为是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所以要辩证地看待翻译动机到底是属于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这个问题,当然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也要通过内部因素发挥作用。翻译批评要充分考虑译者的翻译动机,不考虑翻译动机的翻译批评是盲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我觉得,针对译者个人而言,只要其翻译动机实现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其翻译就是成功的。如把《红楼梦》改编为英文版的儿童文学,只要接受效果好,实现了翻译目的,就是好的翻译。
2. 译者的翻译能力也是影响翻译的重要因素,请问你对翻译能力是如何理解的?如果从构成论来谈翻译能力,那么它有哪些具体的子能力? 翻译能力在国内外都有很多探讨,大多学者认为翻译能力由一些子能力构成,如A. Neubert(2000)将其分为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苗菊(2007)将其分为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在众多翻译能力模型中,PACTE Group的影响最大,将其分为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策略能力、工具能力、对翻译的认识以及生理心理要素(PACTE Group 2003)。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工具或技术能力视为翻译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如PACTE Group(2003),王树槐、王若维(2008),冯全功、张慧玉(2011)等。技术已成为翻译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相关理论模型与框架中如果不考虑技术因素,只能意味对翻译是如何运作的理解过于片面(Olohan 2017:279-280),有学者还专门提出了“译者技术能力体系模型”,包括技术知识、工具能力和技术思维三个层面(王少爽、覃江华 2018:94)。上述研究基本上都属于翻译能力的要素观,其他还有自然观、最简观、认知观等(李瑞林 2011)。笔者倾向于认同影响最为广泛的要素观。从历时而言,(职业)翻译能力的要素无疑是一个动态的构成,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受机器翻译以及各种翻译技术的影响最大。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技术转向重新定义了翻译能力(张成智,王华树 2016: 113)。这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技术能力与技术思维对现代职业翻译实践日趋重要的作用。换言之,职业翻译能力=历时翻译能力+共时翻译能力,前者如语言能力、文化知识、文本知识、认知能力等,后者如技术能力(如CAT、MT、PE等)、信息素养(搜商)、职业知识、团队合作能力、快速学习能力等。 3. 翻译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矛盾,除许钧老师在书中指出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异与同、形与神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重要的矛盾? 许钧老师指出的三对矛盾是非常重要的,也不妨视之为翻译的核心矛盾,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哲学层面的,异与同是文化层面的,形与神是诗学层面的。除此之外,还有翻译方法的直译与意译、翻译策略的归化与异化、翻译主体的人工与机器、翻译过程的理解与表达、翻译风格的再现与创作、翻译补偿的过分与不足等等,都可以构成翻译的矛盾。我觉得要辩证看待翻译中的矛盾,不要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矛盾双方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相互转换,比如异与同的矛盾,不同文化之间相异的东西随着跨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也会慢慢趋同的,很多外来表达方式的植入就是典型的例证。再如,形与神的矛盾,很多时候形式是承载核心意义的,形式本身就是意义,所以有学者提出过“形式(形)与内容(神)相互推移的原理”(张今)以及“还形式于生命”(刘宓庆)的论题。 4. 第七章在讲到异与同的矛盾时,许钧老师提到了归化与异化的概念?请问归化和异化是翻译方法,还是翻译策略,抑或是翻译伦理?归化和异化与文化差异有什么关系? 异与同和归化与异化是紧密相关的,但不能直接等同,其间的关系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针对的都是异的部分,如果处理的是同的部分,也就无所谓异化和归化了。试想,把英语中的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 翻译为“趁热打铁”是归化还是异化呢?我觉得不妨给它起一个名字,如“等化”,毕竟其中的概念与语言表达都是完全相同的。针对归化与异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词汇、短语、句子层面,归化和异化为翻译方法;在文本(语篇)层面,为翻译策略,体现在翻译方法的统计趋势上;在对待文化差异的态度上,则为翻译伦理,是译者翻译观的外在表现。在文本层面,任何翻译都是归化与异化的杂合体,只是主导倾向不同而已(这个看似是常识的问题,却也引发了不少争议)。我认为,文化差异(这里又要界定什么是文化了,不妨宽泛理解)是归化与异化产生的根源,如果没有文化差异,就无所谓归化和异化。 5. 许钧老师认为,翻译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请问你是如何理解翻译的创造价值的?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翻译本身是具有创造性的,尤其是文学翻译,没有译者的(再)创造,就不会有出色的译文,更不会有翻译经典的形成。我非常欣赏罗新璋《释“译作”》(《中国翻译》1995年第2期)中的一些言论:“译而不作,多半缘于认为译不该作,有种心理障碍,便一味跟着原文走,机械地,甚至笨拙地照搬,但搬过来的往往是一堆文字瓦砾。照搬,毕竟不是创制。”“假如原作是件艺术品,翻译过来,也该还它一件艺术品。译而且作,不认为信字当头,美即在其中矣。——美需要创造,译作之美需要翻译家去进行艺术创造。”“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创造。译者的创作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不是拜倒在原作前,无所作为,也不是甩开原作,随意挥洒,而是在两种语言交汇的有限空间里自由驰骋。”由霍克思翻译的《红楼梦》中的各种修辞就有很多典型的“再创作”的例子,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中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在此仅举两个小例子,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被汉学家翟里斯英译为 “My whitening hair could make a long long rope. / Yet could not fathom all my depth of woe”,张九龄的“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被翟里斯译为 “My heart is like the full moon, full of pains, / Save that ’tis always full and never wanes”,仔细体味,妙在其中矣。 6. 许钧老师在第九章中说翻译批评的功能分两个层面,即实践层面的监督功能和理论层面的理论研究与建构功能。你是如何理解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功能的?能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国内是否需要强化“批评理论化”的意识? 我认为,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功能主要指从具体的翻译现象出发,尤其是从翻译文本出发,在翻译批评过程中发现其中值得研究与思考的地方,然后对之进行系统地分析与归纳,再对之进行理论升华。一般而言,基于翻译批评的理论建构具有较强的原创性,如黄忠廉提出的变译理论,王宏印提出的“无本(根)回译”、冯全功和候小圆提出的“瘦身翻译”(thin translation)等。批评理论化基于翻译现象的归纳与总结,但不止于感性总结,还要有学理升华,需要有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入的学理思考。目前国内翻译界大多是学习或套用西方的理论,或对之进行修修补补,原创性翻译理论并不多见,需要强化“批评理论化”的意识。 批评理论化和理论批评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强调对相关现象的描述与归纳,然后进行理论提升,后者更强调对相关现象的解释与说明,进而验证或强化已有的理论。目前学界更多的是理论批评化,常见形式就是“某理论视角下的某研究”。这两个概念在文论中已有比较深入的探讨,不妨参照。 7.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是同一的吗?信达雅是翻译标准还是翻译批评标准?如何理解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标准之间的关系? 翻译的标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翻译批评的标准(译界往往如此,不加区分)。翻译的标准是译者对自己的要求,翻译批评的标准则是批评者对译文、译事与译论进行批评时所参照或遵循的原则。虽然两者不同,但多有重合,换言之,翻译的标准有时也可作为翻译批评的标准,也就是看看译者是否达到了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首先是翻译标准,也就是严复所谓的“译事楷模”,后来也经常被视为翻译批评的标准。辜正坤曾提出过“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翻译批评的标准也应该是多元的,互补的,还要考虑译者的翻译观与翻译动机。周领顺“译者行为理论”中提出的“求真-务实”连续统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批评标准,而非翻译标准。用“求真-务实”来评价翻译是非常有解释力的,但以此作为翻译标准就有待商榷了。换言之,“求真”(类似于忠实、信、等值)经常被作为翻译标准在文本层面操作,但鲜有把“务实”(更多受外部因素限制)作为翻译标准的。 8. 许老师认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存在重技轻道、重语言轻文化和重微观轻宏观等倾向”,这种总结符合当下的现实吗?青年学生或青年学者在技与道、语言与文化、微观与宏观之间如何取舍?如何才能把握好其间的关系? 我自己的感觉是不完全一致的,目前的“重文化轻语言,重微观轻宏观”的趋势似乎更为明显,至于“重技轻道”好像是道的体悟还远远不够,就把技远远抛在脑后了。这也许是期刊发文导向的使然。当然,许老师提出译界的这个倾向时是近20年前的事了,至少引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20年前的。如今翻译的发展速度太快,倾向不同也是极有可能的。换言之,思考问题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语境! 至于如何取舍,以下节选自我对许钧老师的访谈(未发表),不妨作为参考。 冯全功: 还记得您于2010年去南开大学做讲座,讲座结束后我问了您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从文本间性、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等“间性”视角来研究翻译?您说这个话题可以做出三个博士论文。我当时有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打算,听了您的建议后,我开始转到《红楼梦》翻译研究。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治学理念:青年学者开始不妨多精读一些经典翻译作品,在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再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对之进行分析与解释,或者基于阅读过程中发现的相关翻译现象进行理论思考与学术提炼;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之后(这也往往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再进行宏观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尤其是哲学或学理层面。换句话说,就是走“先微观后宏观、先文本后理论”的学术道路。不知您是如何看待微观文本细读与宏观理论思考的关系的?这样的治学思路是否适合大多数的青年翻译学者?如果说文本细读还包括自己从事的文学翻译实践的话,您的学术道路是否也是这样的? 许钧: 治学思路没有固定的模式,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微观的文本细读,有些人喜欢宏观的理论思考,还有些人喜欢翻译实践本身。当然,如果能够结合,多管齐下,这是更好的事情。针对大多数青年学者,你提到的“先微观后宏观、先文本后理论”的治学思路也不无启示,因为宏观的理论思考需要深厚的学术积淀,广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学术眼光,大部分青年学者会觉得难以驾驭。从微观的文本细读入手,似乎相对容易一些,但也需要能坐得住冷板凳。对照细读文学经典的翻译,如中国四大名著外译、莎士比亚作品汉译等,没有大量的时间投入能看完吗?不看完就对之进行匆忙评论可行吗?或者匆匆忙忙看完了能写出真东西吗?所以对照阅读译文与原文的过程中一定要做有心人,带着研究意识,遇到了值得研究的话题马上记下来,尤其是别人还没有发现的问题,看看译文前后或其他翻译文本中有没有类似的翻译现象。文本对照细读,包括原文与译文以及不同的译文之间,不仅可以发现翻译问题,还有利于培养我们对双语的敏感性,激发我们对双语的热爱。对语言文字的迷恋正是引我进入翻译领域的神秘力量,一进来就是几十年,激情更是有增无减。文学翻译可以说是最细致、最深刻、最全面的文本阅读,更有利于培养自己对语言、对文化的热爱。我自己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就会带着强烈的研究意识。基于自己与别人的翻译实践,也写过一批相对微观的翻译研究论文,如“文学翻译的自我评价——《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汉译札记”“句子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形象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风格与翻译——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等。也可以说我早期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文本细读与文本翻译的,随着我对翻译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转向了更为宏观的层面,对翻译作为文化与思想交流方式有了更多的探索。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围绕文字、文学、文化和思想这四个层面展开翻译研究与从事翻译事业的,只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而已。青年学者如果还没有自己翻译实践的话,也不妨带着研究意识从研读文学经典的翻译入手,或者从经典译者的经典译文着手,如傅雷、林语堂、杨宪益、许渊冲、葛浩文等,从微观的文本分析慢慢拓展到宏观的理论思考。 9. 强调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翻译学者主要有哪些?特色派的特色在何处?这种提法是否有道理?为什么中国特色翻译理论或者说中国特色翻译学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中国学者提出的独创性翻译理论(如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等)是否有区别? 罗新璋、张柏然、张佩瑶、刘宓庆、潘文国、王宏印、郭建中、何刚强等,这些学者都比较强调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其中,张柏然还注意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如刘华文、张思洁、吴志杰等。特色派的特色主要在于译论的理论土壤不一样,也就是理论的建构与思考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文论、画论、文字等文化资源,这种特色论我觉得是有必要提出的,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观具有前瞻性,也很注重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具有很强的文化自信,值得我们系统学习!这方面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或者没有形成气候主要在于后继乏人,后来学者的中国文化素养相对不够深厚,再加上学界学风比较浮躁,各种评价机制很难产生这种需要长时投入的有价值的文章。试想,研究翻译的学者有谁系统研读过《文心雕龙》等古典文献呢?我自己对此虽很感兴趣,但并没有认真研读过。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中国独创性的翻译理论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等同,更不能与中国翻译研究的热点等同。中国特色翻译理论需要我们认真继承,发扬光大。2016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柏然和辛红娟合著的《译学研究叩问录——对当下译论研究的新观察与新思考》,作者在前言中强调我国的译论建设当“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沟通,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我们不妨好好地读一读这本书,从中不仅可以找到构建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的思路、方法与具体案例,还可以学习作者的问题意识与批评精神。 读者之前的提问 1. 教材7.1.2.3“择译而生”和“不译而亡”中,本雅明在《论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束处有这样一段话“意义陷入一个接一个的深渊,直到在语言无底的深度中遭遇失落的威胁为止。然而这种危险也有终止的时候,不过,只有《圣经》才可能避免这样的危险,在《圣经》中意义不再是语言流和意义流的分水岭。在那里,文本和真理或教义是统一的,它本身就应该是纯语言,而不需要意义这一中介,这一文本无条件地具有可译性。”如何理解这段话? 理解本雅明深奥的翻译思想一定要结合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尤其是巴别塔的故事。在本雅明看来,翻译就是为了寻找蕴藏在各种语言中的纯语言,也就是人类在建造巴别塔之前的语言。上帝把人类的语言打乱之后,这种纯语言就分布在各种语言之中了,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纯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瓦罐的话,不同的语言就是瓦罐的碎片,翻译旨在把这些碎片重新粘合起来,复现原来的瓦罐。或者说翻译旨在“解放囚禁在原作中的纯语言”,逐行对译(直译)则是不二法门。翻译是“纯粹的差异嬉戏”,意义也是差异的嬉戏,没有终止的时候(德里达的意义延异观也许就源自本雅明的差异观),所以本雅明才说意义的深渊,语言无底的深洞之类的话语。比如追问A的意思,我们可以用B来解释,B的意思用C来解释,C的意思用D来解释,如此如此,以致无穷,显然ABCD都是不同的,这也许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意义的延异与播撒,以至于虚无缥缈,就像剥洋葱一样,为了寻找意义,层层往下剥,剥到最后发现洋葱是无心的,是没有意义的。 2. 个人认为,9.5翻译批评的标准一节内容与翻译的标准一节有重复,并且9.5.2标题为翻译标准的新视野。那么翻译批评的标准等同于翻译的标准吗? 翻译标准与翻译批评的标准的确很难区分开来,书中(241页)有言,“就普遍意义而言,翻译的标准也就是批评的典律,翻译标准不仅是翻译主体在翻译实践中遵循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也是批评主体用以鉴赏、阐释和评论译作的尺度”,从这句话来看,许钧老师认为两者基本是等同的。我本人觉得还是要区分的,之前我对两者的关系也不敏感,去年傅敬民教授来浙大做讲座,提到了两者的区分问题,也就是不能把翻译标准等同于翻译批评标准,我还是很认同这种观点的,但具体如何操作,也没有想得特别清楚(周领顺提出的“求真-务实”翻译批评理论倒是可供参考)。感觉翻译标准主要针对文本层面(求真、忠实),翻译批评需要考虑各种因素,而不只是文本(语言),还包括主体、文化、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 3. 许钧老师这本书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讨论了翻译的很多基本问题,而作为刚刚踏入学术研究的新入门者,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在自己能力范围的研究课题,如何写研究论文和申报研究项目? 如何选课题是一个很宏观的问题,我觉得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持续不断地阅读与思考,尤其是跨学科的知识,从别人的研究中找到研究线索;第二,针对这个研究线索继续搜集与阅读相关文献,形成一个相对系统的研究思路,如果可能最好写一两篇文章,这样能深化自己的思考,还可作为课题的前期基础;第三,申报项目,多看看成功的案例,如黄忠廉老师的《人文社科项目申报300问》之类的书籍或相关推文,项目很难一审即中的,要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 4. 关于翻译批评,近年来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学界提出了一些翻译模式或者译者模式,请问老师如何看待“丰厚翻译”这一模式? “丰厚翻译”这一模式有不同的适用对象,我觉得中国文学与文化典籍用这种模式是挺适合的,也是译者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很多译者也是这样操作的,这种模式对传播中国文化是有效的,面对的更多的是专业读者,而非大众读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面对的是大众读者,更加注重传播效果,使用“丰厚翻译”的模式就未必合适,比如葛浩文的翻译就说不上什么丰厚,但传播效果还是不错的。 猜你喜欢: 2017“我来读文献”干货汇总 声明 本文版权归iResearch所有。其他任何学术平台若有转载需要,可致电010-88819585或发送邮件至[email protected]协商授权事宜,请勿擅自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