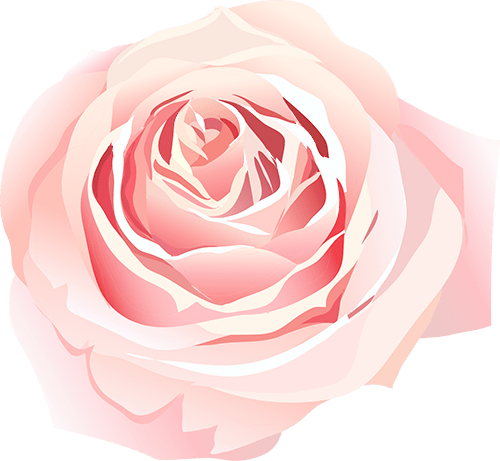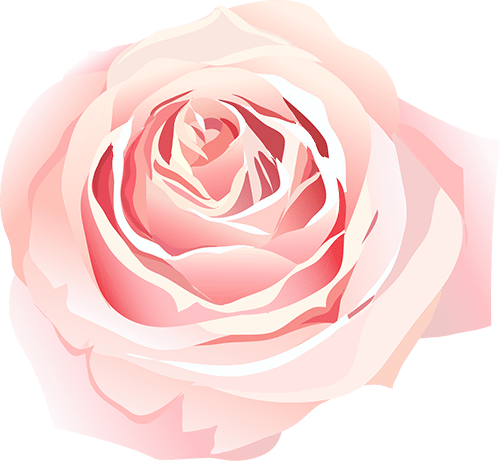翟永明:寻找女艺术家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锦明j13hk416c有单发 › 翟永明:寻找女艺术家 |
翟永明:寻找女艺术家
|
伍锦霞 (Esther Eng,1914—1970)
伍锦霞是幸运的,无论如何,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华裔家庭里,她有富商父亲支持她,因此能如愿地拍出颇有女性意味的电影来。虽然作为导演,她可以在片场上指挥那些年长于她的男性合作者,但事实上,这些合作者却一直忽略或有意回避她的存在。这也是她后来完全被电影史忽略的原因之一。无疑,她也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导演。虽然她本人如何看待性别问题,还有待商榷;但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拍摄了《民族女英雄》《女人世界》这样的电影,可谓是电影史上女性意识觉醒的先驱。 而另一位“连最勤奋的女性主义史学家”都没侦测到,由一位男性收藏家考古挖掘出来、如今登堂入殿进入摄影大师位置的,是传奇摄影师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1926-2009)。薇薇安·迈尔是一位单身保姆,终身以此为职业。如果不是她去世后留下了一皮箱底片,如果不是在拍卖场购得皮箱中底片的人,因为好奇冲印了几张照片,并从中发现她遗世独立的才华,她就只是一个默默来到世界上又默默辞世的保姆:一生乏善可陈,还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但是,迈尔来路不明的才华和对摄影的热爱,让她在人世间留下了一抹浓墨重彩的痕迹。虽然,这一抹痕迹也差点被历史和偏见的大手一把抹掉,但命运有时候却又是仁慈的。她在去世后竟然被一位陌生人发现和寻找了出来。说寻找,是因为收藏者、房产经纪人约翰·马洛夫从这一堆无主之作中,发现了艺术的高光时刻;从一个无名无姓的摄影师身上,他看到值得挖掘的价值。正因为收藏者只是一位圈外的年轻人,所以,他并没有去比照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摄影的上下文关系,也没有去横向比较那个年代纽约摄影师的作品,而是凭直觉发现了他用四百美元买到手的这些底片中,蕴藏着一个巨大的艺术之谜。这一箱资料,包含了十万张黑白底片、两万张幻灯片及无数胶片。这一切资料的背后,只有在相片纸带上出现的一个名字,薇薇安·迈尔。当他试图通过谷歌去搜索这个名字时,他没有任何收获,除了一则讣闻。但是马洛夫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说:“我买过一些关于街头摄影大师的书籍,心想,她如此特别,怎么没人知道她的存在?”这是一个奇迹般的用侦探手法寻访一位女艺术家的故事:借助一则讣告,借助互联网,借助摄影师照片中反复出现的人物,也借助民政事务署,年轻的马洛夫明察暗访,走街串巷,顺藤摸瓜。他沿着摄影师拍摄过的芝加哥街景,走进薇薇安·迈尔的内心,成功地将碎片式的信息,拼凑出一位保姆摄影师的传奇人生。试想如果没有马洛夫的好奇心,没有他的敏锐眼光,没有他的旺盛精力,尤其是如果没有薇薇安因为交不起房租,而被迫拍卖她那些并不值钱的底片,那么,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将永远不会被世人认识。就像几千年来,那些生不逢时的女性曾经做过的一样:她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命和时光,投射到一个终生热爱的事物上,日复一日地去努力做一件没有回报的事情,就像修行一样,让她们的生命充满意义。
薇薇安·迈尔 (Vivian Maier,1926—2009)
二〇〇八年,第一幅薇薇安的照片,被发表在网络上。这时,薇薇安·迈尔还在世,住在一家不为人知的养老院。当然,她不可能看到马洛夫的博客,后者这时也并不知道她为何方神圣。二〇〇九年,马洛夫为薇薇安建立了博客,公布了其大批照片,让世人初窥这位传奇摄影师的作品。这时,距她逝世刚过去几个月。她曾经照顾过的三个孩子,为她刊登了讣闻。这才使得马洛夫有了这个渠道,得以开始剥茧抽丝,去寻访她的人生。说到底,薇薇安也算幸运的,终于在临终之前,得遇一位陌生的知音,将她的一生积蓄——那个被默默搁置在阁楼上几十年的皮箱,贡献给了世人,让这个差点被掩埋的女艺术家得以重见天日。 当我第一次看到薇薇安·迈尔的自拍照时,我非常惊讶,因为我与她一样,也曾喜欢拍自拍照。差不多在二〇〇六年左右,我开始摄影,用一台朋友淘汰的单反相机。不过,我没有像薇薇安·迈尔一样走街串巷,前去芝加哥街头,把镜头对准街头百态,我只是在工作之余或利用工作之便,把镜头对准身边的朋友。又或是在旅途之中,拍摄那些陌生而又常见的风景与人群,偶尔,也对准自己。我曾拍摄过一些自拍照,应该说与薇薇安·迈尔的动机一样——当我们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时(事实上,我们只能从镜子中才能看到自己),这一刻,我们想要把它(自我形象)固定下来。我们按下快门,让它留在某个空间,或者让某个空间留下自己的影子。如果没有薇薇安在形形色色的镜面中,留下自己的影子,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没有迹象表明她去照相馆拍过照;但是在她的相机里,有别人为她拍摄的少量照片,但这些一并留在她从未冲洗过的底片上。
薇薇安·迈尔摄影作品 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出现时,人们倾向于制造神话,以满足人们对“天才”的想象。因此,当薇薇安的作品被不断地、汹涌地挖掘出来之后,人们开始啧啧称奇。尤其是“保姆”这样一个平庸的身份,与她那些珍贵的、成熟的摄影作品并列在一起,更让人遐思无限。于是,有人赞扬她淡泊名利、不重发表。事实上,薇薇安是希望能与他人分享照片的。无奈她连冲洗照片的钱都没有,也许菲薄的工资,只够她购买摄影器材和胶片。因此,她拍下海量的照片,但自己却从未见过冲印出来的照片,想想这也是非常怪诞的一件事。一生执着于拍摄的薇薇安,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既无亲人,也无朋友,当然,也就更没有进入摄影圈的机会。比梵高还要梵高的是,她终生离那个她应该有一席之地的艺术圈十万八千里。或许她连一个称得上是艺术家的人,都没有接触过。不排除她应该看过一些摄影杂志,也不排除她压根儿没看过。但她就是这样秉持天赋,依赖直觉;用一台相机,一扫就扫了几十年的街,一扫就扫出了“半部摄影史书”(芝加哥文化中心馆长如是说)。
作者在阿赫玛托娃之家自拍 (图片由作者提供) 如今,人们称赞她是“与哈里·卡拉汉(Harry Callahan)比肩的摄影大师”。 与薇薇安·迈尔命运相似的还有玛莎·伊凡辛特柯娃(Masha Ivashintsova),一位俄罗斯女艺术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她是活跃在圣彼得堡的戏剧评论家。二〇〇〇年,玛莎去世后,她的女儿在阁楼上发现了母亲拍摄的三万张照片。它们从未示人,连家人都不知道。玛莎的女儿阿斯雅(Asy)把部分底片冲印出来,展示在专门为母亲开设的网站上。同时,她也顺着照片寻找到了苏联时期一位“女性”“母亲”的日常生活轨迹。
玛莎·伊凡辛特柯娃 (Masha Ivashintsova,1942-2000) 与薇薇安·迈尔不同的是,玛莎一直生活和活跃在圣彼得堡的文艺圈,她经常参与诗歌和摄影活动。她一生中也与两位男人——诗人维克多·克里夫林(Viktor Krivulin)和摄影师鲍里斯·斯梅洛夫(Boris Smelov)关系亲密。为什么玛莎不曾向外界展示她的摄影才华?难道又是一位淡泊名利、隐士般的女性?不,通过玛莎留下的日记,我们至少可以窥见一点她的内心。她在日记中表露,与她身边的男人相比,自己的天赋微不足道。我们不知道这两位优秀的男性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对她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至少可以认为,他们并不了解玛莎,更谈不上对她的艺术、她的创作有所关注。这导致了玛莎热忱关注的创作——摄影,生前从未被人知晓。当然,这也与玛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个人境遇有关。她失业后,被迫进入精神病院。在长达十年的精神摧残中,她再也无法回到正常社会,直到二〇〇〇年去世,年仅五十八岁。
玛莎·伊凡辛特柯娃摄影作品 人们喜欢将玛莎·伊凡辛特柯娃与薇薇安·迈尔比较,因为二人都心无旁骛、随心所欲地长期街拍,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群、底层人士。玛莎的摄影,也为世人还原了她那个年代普通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及日常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在整个西方世界,也包括俄罗斯,摄影是被当作一种专业的艺术形象来看待的。“决定性的瞬间”是纪实性摄影的决定性理论。实验摄影、超现实主义摄影、艺术摄影,占据着摄影圈的半壁江山。在数码相机发明之前,后期制作、暗房技术、冲印成本等条件,也限制了薇薇安和玛莎这样的业余摄影师。她们那些数以万计的底片,有些仅仅是胶卷,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自觉卑微的她们,却在今天成就了“自我”。 阿斯雅这样评论母亲:三个男人的爱情“定义了她的生活,也耗干了她,让她支离破碎”。玛莎在日记中说:“我从来没有为自己留下记忆,但总是为别人留下记忆。”但是,玛莎不知道的是:当她为别人留下记忆时(多数时候是为俄罗斯人),当她把镜头对准她身边朋友时,她也留下了自己的。她那些与薇薇安一样、利用各种镜面留下的自拍像,给全世界都留下了她的形象和声名。同样,那些数量巨大的遗存照片,与时代相关的随手拍,对城市、人群,以及对动物、孩子的热爱,这些都是她们二者的相同之处。但一个是圈外保姆,一个是圈内人士,她们的经历也许预示着,还有更多的出于各种原因被遮蔽和被淹没的女性艺术家,她们的才华和人生经历,还有待时间之手去发掘。 点 击 “ 阅 读 原 文 ” | 购 买 2 0 2 2 年 1 0 月 号
《书城杂志》Kindle电子刊 每月5号上线 《书城杂志》豆瓣电子刊 每月5号上线 《书城杂志》当当电子刊 每月5号上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