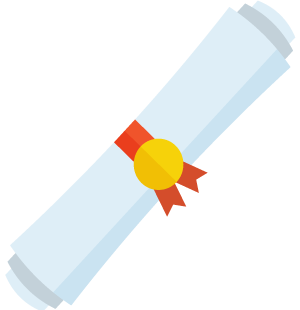读史识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针对美国历史提出三个问题 › 读史识 |
读史识
|
付成双 【摘要】在批判以特纳为代表的西进史学的基础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西部史逐渐形成。其新颖之处,就是用新方法、新视角重新定位和研究美国西部问题。而西部环境史是其中较为活跃和较具代表性的一派。受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影响,许多学者带着深深的使命感,利用全新的视角,考察美国西部发展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从而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关键词】环境史,边疆学派,西部史,西部开发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人类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如今,现代化和科技发展仍然是许多国家所推行的既定战略方针。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而对自然的控制和破坏而日益严重的历史,“几千年来,人类没有改变本性,却极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类了他所生存的环境”。英语中有一句民谚说道:“人类脚步所到之处,沙漠后面跟随(Man strides over the earth, and deserts follow in his footsteps.)”如今,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头号问题,环境保护的浪潮席卷全球。在这种背景下,环境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引导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思索人类社会发展。而美国西部环境史正是这股时代大潮的弄潮儿。 一、对传统史学的反动和当代环境运动的召唤:西部环境史的诞生 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类同他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所以,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环境史产生于美国的西部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在对传统西部史的修正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兴起的过程中孕育产生的。 1893年,年轻的历史学者弗雷德雷克·J.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的芝加哥年会上宣读那篇著名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标志着美国西部史的正式诞生。特纳在这篇论文里面,提出了著名的“边疆假说”,即:“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居民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在特纳看来,西部“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区域”。他的边疆假说,还包括所谓的森林哲学——美国的民主来源于美国的森林——和安全阀理论。边疆理论“奠定了美国西部史学的基础,而且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统治着美国史坛”。 然而,特纳的边疆假说带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弱点:第一,边疆概念过于模糊;第二,将西部史限定在19世纪,并把它当作一个过程,而非一个地区;第三,忽视土著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在西部开发中的贡献;第四,美国民主来源于美国森林的森林哲学和所谓的安全阀理论是错误的。美国的民主同样来源于欧洲传统,只是被当地环境所改变而已。1930年,哈佛大学教授莱特在《美国的民主和边疆》一文中公开指出“民主来自森林的”论断是错误的:“它的基本原则是装在苏珊·康斯坦号船上运到弗吉尼亚的,是装在五月花号上运到普利茅斯的,是由成千的接踵而来的船只运来的。”特纳的边疆理论在经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昙花一现的繁荣以后不久,就遭到了批判和指责。1931年,著名史学家沃尔特·P.韦布出版了《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打破特纳假说的旧框架,开展地区史研究,从而使西部史学从西进史学向着西部地区史的方向转变;50年代,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则突破了原来西部史只注重经济和政治史的狭窄范围,“他成功地把我们引回了对文化含义的研究”。因此,他被看作西部史的第一个修正派,是新西部史的先行者;1955年,著名史学家厄尔·波默罗伊(Earl S. Pomerroy)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西部史的重新定向:连续性与环境》(Toward a Reorientation of Western History: Continuity and Environment),认为东部文化与西部的环境对西部的发展同样重要,倡导对西部史的研究进行重新定向。1965年他又出版了 《太平洋斜坡》一书,“对美国西部史做出了开辟新途径的解释”。从《大平原》到《太平洋斜坡》标志着美国西部史学完成了从特纳边疆史学到新西部史学的转变,所谓“新异”之处,就是随着美国社会的转变,学者们用新的视角、新的观念去突破特纳的理论限制,重新定位和研究西部历史。
美国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一景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位于美国犹他州西南部,被誉为天然石俑的殿堂。 图中所呈现的天然石俑属于丹霞地貌的一种形态。 在新西部史的诸多派别中,环境史学派算是出现比较晚的一个派别。虽然韦布和波默罗伊等人在研究西部时也都注意到了西部的独特环境,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特纳本人也强调西部环境与东部的差别,认为西部边疆是文明和野蛮的汇合处。但他们对西部环境的解释是服从于其理论需要的,并没有真正站在环境的角度去审视和评价西部的发展和变化,在他们的著作中,环境充其量也仅仅是影响西部的诸多因素之一而已。 环境史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成为新西部史的活跃学科,还与美国社会中主流的环境意识的变化、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生态学的发展紧密相关。 首先是美国环境意识的变化,传统上,美国人的环境意识是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但到19世纪中期,美国人的环境意识逐渐发生了变化。浪漫主义学者梭罗、爱默生、华盛顿·欧文等都以欣赏的目光去对待自然,歌颂自然。著名画家吉特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关于美国西部的许多宝贵资料,也是美国历史上呼吁建立国家公园,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第一人:“在一个国家公园里,人和野兽都保留着他们自然的野性和美丽。”1864年,美国学者和政治家乔治·帕金斯·马什出版了他的著作《人与自然》,指出:“地球仅仅是给予了人类使用,不是消耗,更不是肆无忌惮地浪费的权利,人类把这一点遗忘的太久了。”马什被称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之父,其著作也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的源泉”。 其次,19世纪后期,资源保护主义兴起,美国逐渐进入保护主义时代。随着边疆的结束和各种环境问题的暴露,在民间保护人士和政府官员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地美国人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从而出现了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它“始于19世纪后期,在进步主义时期开花结果,新政时期走向成熟”。其重点主要是对西部资源和环境的保护,而成果就是一系列环保措施的出台和环保体系的基本建立。其中推动这一潮流的两位最著名环境主义者是约翰·缪尔(John Muir)和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他们两个虽然立场和观点不同,前者主张环境保护的目的是维护自然的生态多样性和自然之美,而后者则信奉功利主义的保护原则,认为保护的目的是供人类利用。约翰· 缪尔曾经领导了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活动,推动建立国家公园,1892年建立了著名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并长期担任该组织的主席。平肖则长期担任美国国家森林保护局的局长,将其主张应用到对国家森林的保护之中。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环境主义者阿尔多·利奥波德创立了著名的大地伦理学,他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其遗著《沙乡年鉴》中。“简言之,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意愿和公民”。“当某事物倾向于保护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之美时,它就是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正是看到了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博大精深,利奥波德才要求世人“像大山那样思考!” 第三,现代环境主义运动是环境史研究的催生婆。1962年,美国著名女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son)出版了当代自然保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该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证实:“人类正因对其他生物种类的傲慢轻率处置的态度而使自身生存面临威胁。”她写道:“控制自然是一个傲慢自欺的词组,始自生物学和哲学的最原始时期,当时人们认为自然界是为了人类的方便才存在的······如此原始的科学使用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在转而用来对付昆虫的同时,也转而来对付地球。这真是我们时代的令人惊恐的不幸。” 卡森的著作引发了席卷全球的环保浪潮。这一次影响远远大于第一次,环境运动不仅波及全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且与妇女运动、人权运动等多种社会运动合在一起,出现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新的派别。其中环境史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教育人们重新思考和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根据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的观点,在环境史出现以前,历史写作曾经依次出现了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等三种写作模式。 美国西部在历史上由于西部开发时期所引起的剧烈环境变迁,以及在现代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理特征,而自然成为环境史研究的绝佳案例。可见,西部环境史正是在对传统西部史的修正和当今席卷全球的环保浪潮中所孕育出的新生宠儿。 二、西部环境史的研究:主要成果与存在的问题 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环境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西部环境史。而且在当今美国的环境史学界,无论从学者的数量、研究的题目,还是从研究成果的质量上来看,大都以西部环境史为尊。因此,韦斯特声称:“环境史是以西部史为基础的,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史就是西部史。环境史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成为一个学科的过程中,西部史学家也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著名学者塞缪尔·海斯以进步主义时期的环境保护运动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保护与效率》(1959),以及罗德里克·纳什的名著《荒野与美国的思想》(1967)的出版可以作为环境史产生的标志。 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环境史已经经历了40个春秋,涌现了大量的优秀成果,许多问题都从环境史的角度得到了重新的阐释。那么,到底什么是环境史呢?根据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定义是:“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力求理解自然如何为人类行动提供选择和设置障碍,人们如何改变他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信念、价值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它属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科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汲取洞见。”默茜特认为,环境史是要“通过地球的眼睛来观察过去,它要探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总起来讲,环境史是研究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及其关系的一门学问。根据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观点,环境史主要包括以下三项内容:第一,发现和探索历史上自然的环境的发展和变迁;第二,研究人类的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是如何改变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 第三,考察人类对待自然的价值、观念和态度的演变。
大盐湖 大盐湖是北美洲第一大盐湖,属于犹他州,紧靠该湖的盐湖城是美国犹他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大盐湖形成于14500年前,古时称为Bonneville湖,是一个巨型咸水湖,目前的大盐湖位于古湖的东北部,为Bonneville古湖残留水体,目前大约仅有Bonneville湖面积的十分之一。 环境史研究作为新西部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出现到现在,吸引了一大批专业的研究人员,并涌现出了许多观点鲜明的力作。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在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形成以前已经成名的塞缪尔·海斯和罗德里克·纳什以外,前者的《保护与效率》是研究第一次环保运动的经典著作,后者的《荒野与美国的思想》则是研究美国环境意识的奠基之作。当今最著名的西部环境史学家当属唐纳德·沃斯特,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在美国西部史、环境史、科学和自然思想史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1979年出版的《沙暴》(Dust Bowl),获得了史学界最高荣誉班克罗夫特奖,该书批判了马林关于美国西南部30年代的沙暴是自然的循环而非人为破坏的观点,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疯狂开发才是西部30年代沙暴的真正根源。另一位著名的西部环境史学家是威廉·克朗农。他在《自然的城市:芝加哥和大西部》(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Great West)中探讨了芝加哥与西部的关系,以及这个地区经济与生态上的变迁。他的另一部专著《土地的变迁:印第安人、殖民者和新英格兰的生态学》(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则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新英格兰时期土著人和白人与环境的不同关系。卡罗琳·默茜特同样是近几年十分活跃的一位环境史学家,她以独特的女性主义的视角考察人类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其主要作品有《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生态革命:新英格兰的自然、性别和科学》等。另外, 她还主编了《哥伦比亚美国环境史指南》(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 History)《翠绿对金黄:加州环境史》(Green Verus Gold: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并参与编写《美国环境史百科全书》等重要的工具书。另一位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就是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哥伦布的交换:1492年的生物与文化后果》(The Columbia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等都是从环境史角度研究欧洲向世界扩张的优秀著作。另外,对于美国西部史上的典型问题,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环境史方面的力作,如安德鲁·伊森伯格的《野牛的绝灭》(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1750-1920)研究了北美野牛在西部开发的环境变迁中的命运;而杜安·史密斯的《美国采矿业与环境》(Mining America:The Industrary and the Environment 1800-1980)则研究了矿业边疆对环境的影响。 总之,美国西部环境史是一个异常活跃的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优秀著作和文章问世。《环境评论》(1987年第4期)、《美国历史杂志》(1990年第4期)、《太平洋历史评论》(2001年第1期)、《历史与理论》(2003年第4期)都曾经集中登载了关于环境史讨论的专门文章。另外,《环境史》《密西西比历史评论》等杂志也经常刊登有关西部环境史的论文。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西部环境史的研究代表了当今美国乃至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最早水平和主流趋向。 当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西部环境史同世界环境史一样,在研究成果日新月异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美国西部环境史同时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双重色彩。环境史产生于对过去人类历史发展中征服自然观念和近代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又是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潮中孕育产生的。不可避免地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批判现实的目的还是为现实服务,人类应该超越狭隘的自我、具有宏观的道德关怀意识,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自我,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境地。许多美国西部环境史学家和环境主义者在批判近三百年来西方占主流的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白人自然观念的同时,倾向于理想化白人到达以前的美洲自然环境和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及自然观念。诚然,白人到达以前美洲的自然环境和资源状况比现代要好得多,但并不是如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荒野,印第安人以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通过用火,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美洲的原始风貌,否定印第安人对美洲的改变,等于否认印第安人的历史作用,同样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印第安人生态研究的另一个趋向就是所谓生态的印第安人。许多学者和环境主义者把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想象为生态的、与自然和谐的,甚至认为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态观念为人类解决当今的环境危机指明了出路。而且随着当代印第安人民族意识的觉醒,许多印第安人自己也刻意地塑造“生态的印第安人”的观念。“哭泣的克迪”(The Crying Cody)就是此类题材的一个例证,这是一幅流传很广的环保宣传画,画面正中是一位流着两行热泪的印第安人,其背后则是干裂和荒凉的土地,最近的材料证明克迪可能是一位意大利人,根本不是印第安人!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前一段时间非常流行的所谓西雅图酋长的《神圣的大地母亲》的演讲,的确是一片优秀的环保宣言,但后来被证明是60年代的环境主义者伪造的一份赝品。虽然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与白人相比,具有朴素的自然崇拜观念,对美洲的改变比白人要轻得多,但并不能认为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就是生态的,其实有许多例证表明,印第安人的许多实践并不符合现在的环保和生态准则。人类要走向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之路,是需要借鉴历史上的优秀生态观念和文化遗产,但绝不能复古,而且印第安人的自然观念和生活实践是他们那个时代条件下的产物,在现在是行不通的。 第二,美国西部环境史研究的选题过于集中,视野还不够广阔。在20世纪90 年代以前,西部环境史的选题主要集中在印第安人与环境、森林史、水利史、荒野史等几个方面,的确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如:卡尔文·马丁的《动物守护者》以及批驳这一观点的克雷奇三世的《生态的印第安人?》、克朗农的《自然的都会》和《大地的变迁》、沃斯特的《沙暴》、海斯的《保护与效率》、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的思想》等。但西部环境史的选题总起来说主要“都属于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的范畴”。从族裔的角度来看,西部环境史对于非白人和非印第安人在西部发展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着墨较少;从地域来看,西部环境史所研究的主要是农村边疆的环境史,对于西部城市的环境史研究不够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之中;从产业结构来看,环境史主要研究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对于工业领域的环境变迁研究不够;从空间来看,美国西部环境史如同美国西部史一样,仅仅着眼在美国西部,缺乏空间联系的思路,对于同属一个进程和地域特征的北部邻居注意不够,其实,这也是中外学术界整个美国问题研究的一个缺点。其根源就是美国的绝对优势,离开了加拿大,美国自认为对它的发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加拿大却离不了美国,这就加拿大研究不能不考虑美国因素,而美国研究却从来不考虑加拿大因素的根源。殊不知,加拿大的西部发展同美国的西部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进程的两个方向。以加拿大为参照,许多美国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就如同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原来我们认为想当然的问题一样。 其三,环境史如今已经走过了初创时期,接下来的任务是从理论和体系上对这门学科进行规范和完善,否则必然影响其自身的发展。甚至有可能仍然被当作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后现代主义而遭到抛弃。环境史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和体系建设都迫切地需要加强,既要及时吸收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动态,又要建立自己的特色和体系。与环境史联系最为密切的两个学科一是环境伦理学或说环境哲学,一是生态学。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本身也构成环境史研究的部分内容。但环境伦理学和生态学毕竟不能等同于环境史的研究,环境史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直到今天,连一个可以被广泛认可的环境史的定义都还没有形成,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说:“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
波浪谷 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朱红悬崖的帕利亚(Paria)峡谷,其砂岩上的纹路像波浪一样,所以被称为波浪谷,与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的天然石俑一样,是丹霞地貌的一种。 美国西部环境史从很大程度上说代表了美国乃至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在过去的40年里出现了无数的西部环境史个案研究的优秀著作,但从整体上考察北美西部环境史乃至世界环境史的有分量的著作毕竟还不多,甚至在加拿大当今还没有一本像样的环境通史的著作。 三、从环境史的角度看美国西部开发 传统上,我们总是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美国西部开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人类要走向文明,他就必须改变他周围的环境。”然而,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的西部开发却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北美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数以千万计的旅鸽和野牛、海狸、白尾鹿等物种相继灭绝或濒临灭绝,大片的原始森林遭到砍伐,随之而来的是土壤的盐碱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结果,20世纪30年代西部大草原的沙暴(Dust Bowl)为北美西部开发划上了永远的终结号。正是由于剧烈的环境变迁和沉重的环境灾难,才使一向认为资源无限、机会无限的美国人幡然醒悟,率先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从环境史的角度审视美国西部开发,就会发现它所走过的实际上是一条从破坏到保护的U型曲线。 首先,美国西部开发史是一部新世界动植物资源遭到疯狂破坏的历史。北美大陆是一片资源极端富饶、物种十分丰富的地区。当17世纪初白人刚刚登上这片大陆的时候,这里简直就是动植物的宝库。东西两边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一些松树甚至高达250英尺,树龄在4000年以上 。据估计,当时北美东部一片10平方英里的森林里,可以生存5只黑熊,2到3只美洲豹,2-3只狼,200只火鸟,400只白尾鹿,20000只灰松鼠。中部草原上的野牛“其数量最少也有4000万头左右,很可能总数达到了6000万头”。然而,在美国向西部的开发中,这些动植物资源都遭到了疯狂的破坏,从而使得本地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遭殃的是美洲的森林。在北美历史上一度曾经出现过方木边疆。除了农民毁林开荒外,优质的木材不仅供出口,还供应本地取暖、动力和建设用木。1826—1827年冬天,仅仅费城一地就烧掉了11平方英里的森林。到1800年,新英格兰南部3/4的地区已经没有了森林。随着东部森林的消失和边疆向草原地区的推进,铁路用木、建设用木和工业燃料用木的数量都大幅增加,大湖区的森林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西部主要的木材源地。1856年,芝加哥取代阿尔伯尼成为全国的木材交易中心。在木材交易的盛期,芝加哥的晒木场上常年晾晒着500万立方英尺的木头,这些木头需要砍伐25万棵大树,覆盖上百英里的范围。到1886年,连一向乐观的《西北伐木者》报也不得不哀叹:“以前认为不可耗竭的白松和霍威松(horwaypine)木材的末日即将来到了。 随着森林一道消失的还有这里原来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到18世纪末,鹿在44度以南已经很难看到,甚至连旅鸽这种数量达到50亿只的鸟类,也在1914年灭绝。 丰富的毛皮资源和丰厚的利润曾经使得毛皮贸易成为北美历史上堪与农业开发并提的一种边疆开发形式。但由于疯狂的大屠杀,这些珍贵的毛皮动物也在多处灭绝:到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海狸几乎完全消失;到1831年,海狸在北部大草原上也灭绝了。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和草原上的野牛也遭到了几乎同样的命运。在贸易的盛期,每年大概要屠杀,100万只鹿。到19世纪末,曾经庞大的白尾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在1872—1874年,每年被杀死的野牛高达300万头。结果,在短短的数年内,野牛的数量从原来的上千万头锐减到200余头。
北美灰熊 北美灰熊需要较大空间觅食和生活,其活动范围可以大到500平方英里。但是,伴随着人类定居点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延伸,北美灰熊的自然生境受到极大限制,目前处于频临灭绝的境况。 其次,美国西部开发也是物种变迁的历史。“生态学上的偷乘者是随着最早的居民开始来临的”。在殖民者向美洲移民的船上就搭载了旧世界的动植物和微生物。除了老鼠、猪、马和牛等常见物种外,蜜蜂也是被殖民者从旧世界引入的新物种之一,在17世纪20年代,蜜蜂就随着移民们来到了弗吉尼亚,并迅速在北美东部繁衍起来。印第安人称蜜蜂为 “英国苍蝇”(English flies),“认为它们向内陆的推进是白人临近的前兆”。旧世界的植物也是在新世界安家的首批生命之一。除了欧洲人带到美洲的农业品种外,不经意来到的还有野草。据瑞典植物学家彼德·卡尔姆的研究,大多数欧洲野草早在1750年就在新泽西和纽约扎根了。在17世纪的后半期,至少有20种野草在新英格兰安家落户。车前草被印第安人称为 “英国人的脚”(Englishman’s foot),意即英国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可见到这种植物的影子。另外,像白三叶草、蒲公英、肯塔基六月禾、小檗属植物、金丝桃、麦仙翁、雀麦等也都在北美扎了根。除了这些动植物品种外,殖民者随身携带的旧世界的微生物和病菌也一道侵入美洲,如天花、伤寒、麻疹 霍乱等,其中以天花对印第安人的威胁最大,天花 所造成的死亡率一般在80%,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要65%左右。在天花的频繁打击下,许多部落惨遭灭顶之灾。 再次,美国西部开发也是一部人为的自然灾难的历史。物种变迁和本地动植物资源遭疯狂破坏仅仅是西部开发中的一个方面,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征服自然、文明战胜野蛮的错误观念的指导下,美国西部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生态悲剧。除了动植物资源外,西部的土地、矿产和水利资源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 几乎每个西部行业的兴起都伴随着对环境的巨大破坏。矿业边疆所信奉的原则是先到先得、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其中对环境破坏最为恶劣的当数一些大公司所惯常采用的水力采矿法。这种方法用高压水龙头洗去矿脉上面所覆盖的表土和沙石,然后再进行开采。而被水流冲刷下来的覆盖在矿脉上面的沙石则随着废水流进河道,污染水源,并使河流的沉积物增加,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地(Central Valley),水利采矿使得尤巴河的河床每年抬高1/3英尺,萨克拉门托河每年升高1/4英尺。据计算,到1890年代,水力采矿所带来的沙石在这里一共掩埋了39000英亩的农田,并对另外的14000英亩造成了部分损害。然而荒唐的是,当农场主状告采矿公司要求赔偿时,采矿公司的理由竟是:他们有权往河里倾倒废沙石,而且他们采矿在先,农场主应该意识到这种后果! 大草原是美国最后的边疆消失的地方,也是生态灾难最为引人注意的地方。野牛的灭绝和1886—1887年开放式牧牛帝国的崩溃并不是西部人疯狂破坏自然的结束,恰恰相反,更残酷的破坏和更严重的灾难还在后面。 虽然在科技进步和大好的外部环境下,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发西部草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30年代初期席卷全球的大危机和相对较少的降水和高温使传统的粗犷地以征服自然为特征的西部开发彻底走到了尽头。多种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终于出现了美国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30年代的沙尘暴。根据美国土地保护局的统计,整个30年代,能见度不到1英里的天数,在1932年,有14次;1933年,38次;1934年,22次;1935年,40次;1936年,68次;1937年,72次,1938年,61次。如此大规模的沙尘暴肆虐的结果是大草原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最后开发的位于堪萨斯、科罗拉多、俄克拉何马等五州交界之处的1000万英亩的土地是受灾最严重的沙暴中心(Dust Bowl)。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408吨表土被吹走,总共被吹走的表土达到8.5亿吨。1939年,《达拉斯农业新闻》哀叹:大草原,原先是鹿、野牛和羚羊的家园,现在则成了沙暴和联邦工程管理署的家。美国历史学家马林曾经将西部沙尘暴的原因归结为西部独特的气候,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批判了马林将沙暴归结为气候的观点,指出:“生态学家在30年代所辩论的尘暴,是美国在适应自然的经济体系上的一个最严重的失败。”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西部开发还是一部从环境破坏走向环境保护的历史。就在美国西部开发高唱凯歌之时,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所谓的”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生态变迁以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灾难性破坏,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呼吁政府制定措施保护环境,从而掀起了进步主义时期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从1872年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的建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在民间保护力量和民间保护者的联合努力下,美国出台了多项保护措施,设立了一系列森林保留区、国家公园和国家纪念地的建立,基本上奠定了美国保护主义的初步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开发战略的提出,原本十分冷寂的美国西部史领域一下子活跃起来,许多学者针对美国的西部开发,对我国的西部开发提出了许多建议。虽然美国西部开发的确有许多很好的经验,但它们却并不适应中国的情况,如果说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话,大概就是从疯狂破坏环境到走向环境保护这件事情了。美国西部开发是建立在资源极端丰富和对印第安人的无情掠夺的基础之上的,是殖民主义大扩张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美国人能够从破坏自然中醒悟,提倡保护自然,相信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的炎黄子孙也有能力在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采他山之石,从当前的西部开发中摸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之路。 总之,西部环境史是一片有待深入开拓的全新领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来,也期待着更多的关于西部环境史的优秀作品面世。
作者简介 付成双,男,山东惠民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世界近现代史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加拿大史、北美西部史和世界环境史的研究。
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美国西部史的新视角——西部环境史。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往往关注的是人类本身的历史,人类所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思想;大约在19世纪之前很少有人去关注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我们无限的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数人类世界的奇观;我们可以控制动物、植物······有能力随意的处置它们,但这一切背后对人类的发展造成的危害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批判现实的目的还是为现实服务的。人类应该超越狭隘的自我、具有宏观的道德关怀意识······”人类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为我们提供氧气、水等物质条件的大自然,对大自然的破坏只会阻碍人类历史的进步。从美国西部史中,我们反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国西部的环境史研究应该对如今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有着重大的意义。 ——蒋玉琪 特纳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一文将广袤的西部及其历史高调置于美国史研究的聚光灯下。本文主从环境史的角度切入美国西部边疆的研究,阐述美国西部环境史学的诞生过程、主要成果、存在的问题及环境史语境下的西部开发。作者认为美国环境意识的变化、资源保护主义的兴起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西部环境史兴起的三个主要原因,但作者并未对资源保护主义与现代环境主义加以界定、区分,二者在西部环境史兴起中的作用有何不同较为模糊。作者提出现实批判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双重色彩、选题过于集中、理论体系不完善是西部环境史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就笔者目前对环境史浅薄的了解来看,这三个问题似乎不仅存在于美国西部环境史的研究,世界环境史的研究亦有此现象。在文章主体的最后一个部分,从环境史的视角看美国西部开发,作者指出美国西部开发走过的是从破坏到保护的路,然而,随后的论述里破坏的内容占据绝大篇幅,对于保护的阐释不太多。 ——徐欣蕊 正如付成双老师在文中的观点,美国西部开发史是一部新世界动植物遭到疯狂破坏的历史,是物种变迁的历史,也是一部人为的自然灾难的历史。与此同时,还是从环境破坏走向环境保护的历史。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背后,出现在自然中的往往却是丑陋的一面,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和破坏日益严重。但所幸人们很快意识到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生态变迁以及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灾难性破坏,开始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曾经,人类给自然带来灾难,但同样地,人类也遭到了来自大自然的报复。相信通过人类认识的不断进步与升华,定能摸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发展之路。 —— 张欣怡
本期编辑:徐欣蕊
《自然的边疆:北美西部开发中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 作者:付成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