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帆:让关于丁真的辩论,打开看待藏地的可能性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评丁真爆火 › 对话张帆:让关于丁真的辩论,打开看待藏地的可能性 |
对话张帆:让关于丁真的辩论,打开看待藏地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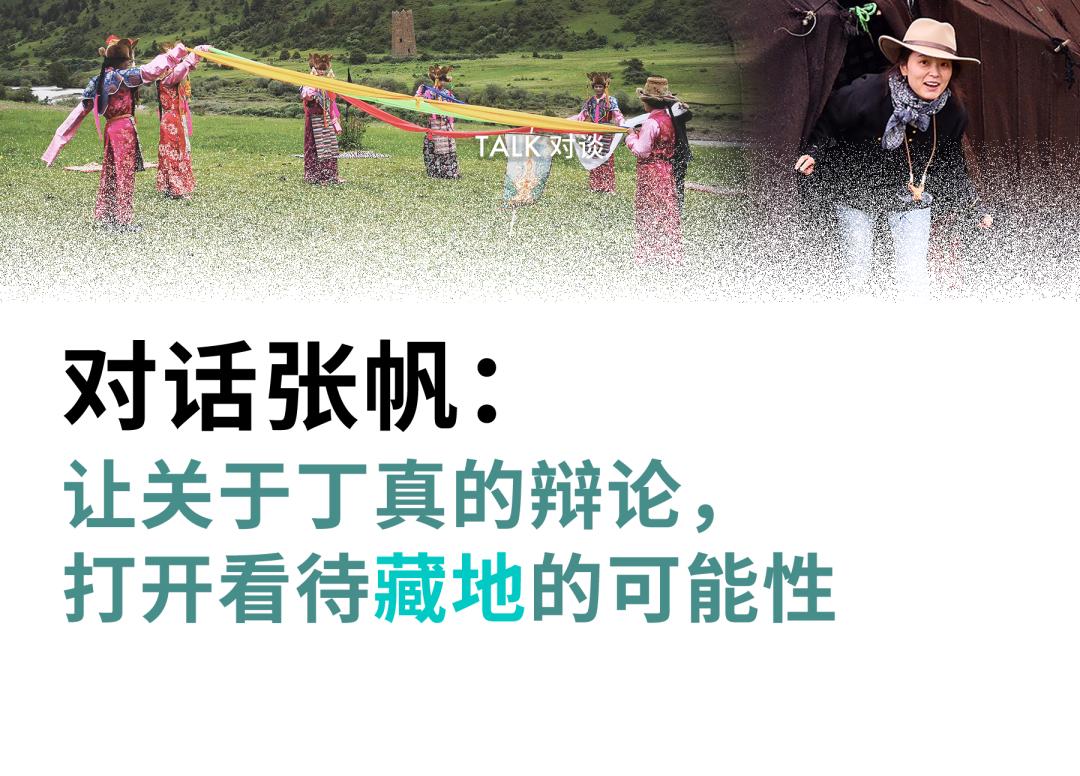 记者|戴汀屿 贾沁蕾 李佳润 朱晗宇 任书漫 编辑|张卓辉 夏泽君 丁真爆红,《气球》上映,藏文化的符号频繁地进入大众讨论的场域。与地方文旅事业结合起来的理塘丁真似乎为扶贫提供了新思路,万玛才旦镜头下的藏地景观则再一次引发人们对于现代化冲击的思考。 真实的理塘是怎样的?我们该用何种方式去切近藏区的真实,以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与交流? 接受访谈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她的研究领域是历史人类学、汉人民间信仰、汉藏关系、文明理论。张帆老师在博士期间的研究关注18世纪的清藏关系。她在两年前选取理塘作为田野点,并多次前往,展开与藏戏有关的研究。
 此间:在您的研究经历中,您具体是什么时候关注到汉藏关系,以及进入相关田野的? 张帆:我对于西藏的兴趣发生得很早。我本科期间的一次旅行到了青海那边。那种高饱和度的色彩,以及那种特别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都跟我的生活呈现出某种差异。我生长的环境是中原的一个小城市,色彩都是灰暗的。我的父亲是老师,对我的管教非常严格,我处在类似于“做题家”的这种成长经历里,跟大家很像。我在20岁前后的年龄,突然一下看到一个跟自己生长的世界很不一样的世界,就觉得非常喜欢,很着迷。当时我就觉得,以后如果能够找到机会长期在这边待着,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刚好在博士阶段,我有机会能把它做成我的一个研究。  张帆在毛垭草原,也就是丁真家乡的大草原 我在德国马普所读博时,他们有一个对于“文明“和”帝国”的研究。清朝作为一个所谓“多元一体”的这种帝国形态,尤其是她在18世纪的帝国建构过程中的措施、因素或是文化、政策,是可以跟更大的其他帝国做比较的。那时我才有了机会真正把西藏和清的关系纳入到我的系统研究里面去。 此间:今年11月,丁真偶然走红,他的家乡理塘也进入了大家的视野。理塘是您的田野点,当时您是带着怎样的关切进入的呢? 张帆:我的博士论文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历史的研究。因此我始终期待我能够做一个以田野为出发点的真正的民族志。 我再次回到西藏后,就选择了一个不在文化中心地区的田野点,就是理塘。理塘在四川,离我们所认为的藏文化的核心拉萨很远。那里被称为康巴地区。在藏人的直接印象里,康巴人很帅,但是没有文化。在藏文化里会有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比如他们对青海安多藏人的印象就是会出学者,万玛才旦就是典型的安多学者艺术家。 之前的民族研究多多少少给人这样的印象:到了一个地方,就认为这个地方存在着一群人,这群人体貌特征差不多,语言是一样的,有一样的历史记忆,有一样的生活习惯。我们就把它视为一个民族,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演变,诸如此类的。这样就把一个一个民族都孤立起来研究了。 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费孝通这一批学者就认为这样是有问题的,他提出了“藏彝走廊”的概念。我们如果回望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不同民族始终是在互动的。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恰恰把他们孤立开来了,这与事实背道而驰。“藏彝走廊“的概念就是要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人群怎么样互相影响。这对我一直都特别有吸引力。我就想,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去做以田野为出发点的民族志的话,我很想看一下这些所谓混杂的区域,看看不同的人群是怎么相互影响的。 于是我就选了理塘。理塘去的人不多,平均海拔都在4000多米,很多研究者出于高反或身体原因不会去那里。出于学理上的考量,它是一个有理论增长点的区域,而且先前的研究不太多,不那么火,我就觉得可以去看一看。结果今年一下就火了,我就在考虑我明年怎么去(笑)。 此间:在您看来,丁真身上的什么特质吸引了大众? 张帆:丁真火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康巴帅哥。我去年参加了理塘举办的康巴汉子选美比赛,全程观摩。他们对传统康巴帅哥的要求叫“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酒量一斤八”。这是当地人跟我开玩笑的,就是说这才是一个康巴汉子该有的气度,就是要高大、健壮,要野性。  康巴汉子选美比赛中的前几名 但丁真这个形象恰恰跟当地人所认为的帅哥的形象相差很远。他并不那么高大,也并不野性,他是个小孩嘛,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那种感觉,比较青涩。我觉得这可能跟内地这两年“小奶狗”这样的审美偏好刚好就对应上了。但他跟当地人所想的“康巴汉子”的形象是几乎完全相反的。 此间:丁真身上很多藏族的元素似乎都被浪漫化了,比如放牛、赛马。这跟您的田野经历有交叉吗?您有体会吗? 张帆:有的。每年的“八一赛马节”是理塘县举办的一个规格很高的比赛,号称是国际赛马节。其实基本上就是他们那儿几个县的人参与。有一年好像来了个蒙古的,大家已经觉得好国际范儿。我去参加了,我非常感动。 赛马节的第一个环节叫“万马奔腾”,所有参赛的选手,大概有上千个,穿着他们的县服或者村服,身上插着彩旗、国旗或者代表他们区域的、家族性的旗,诸如此类。反正每个人都会身上插杆旗。几千个人从你面前奔过去,地都在震动,我的心也在震动,那刻就真的会很感动。  赛马节上盛装的理塘少女 我们这些在城市里面生长和生活的人都太精致了,精致到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力都已经在皮囊包裹之下减弱,大概每天都在龟息养生。那一刻就发现他们那些生命力这么野蛮地呈现在你面前,让你一下看到人是可以这样活着的,人类的远祖或许就是这样征服世界,或许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能够繁衍到今天,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后面有分组比赛,什么小跑马、小走马。当地人对赛马真的是很狂热的,他们可以跟你聊上好多天。像丁真这样的小伙子参赛的比较多,因为一旦年龄大了以后,他体重变大了,跑马就跑不快了,参赛的都是十几岁的所谓少年。 我看到最年轻的,十一二岁的都去参加比赛,他们比较轻,骑起来比较快。如果你跟他们聊起赛马,他会告诉你哪一种骑马姿态是漂亮的,哪种弯腰捡哈达的姿态是美的,哪样是比较难看的、不雅的,它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还有什么样的马是好看的。大家都说丁真的马不好看,太丑了。理塘当地的马就是那种小马。比较高大的那些马,当地人叫它三河马,是从青海那边配的种,理塘当地的马都比较矮小,高大的马不多。 理塘的人认为骑马有两种姿态最好看,一种姿态是身体往前趴在马身上,一种姿态是完全后仰,相当于躺在马上,他们觉得这两个姿势是最帅的。正襟危坐像骑自行车一样的这种,当地人就很看不起,大家一看就会笑。赛马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概念词汇和讨论的语言系统,如果将来能有机会,做一个关于当地赛马的研究也是很有趣的。   八一赛马节上骑手的英姿
 此间:从您的视角来看,有哪些力量一步一步促成丁真成为了一个火爆的现象? 张帆:我觉得丁真的火是一个非常偶然性的事情。在这种资本流量的时代,几乎不可能操纵一个人让他变火。但是丁真火了之后,地方上很快就把他接盘接过来了,没有让他被过度消费,也就是没有让他过度参加各种娱乐节目,去过多地抛头露脸。丁真现在在各种社交媒体上,是非常克制的,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在做。这样一种比较克制的、政府的介入,可能是让他后续持续红起来的一个原因。 另外的一个原因是这件事情和地方的精准扶贫联系在一起了。他就不再是一个流行文化的资本选择的结果,他成了一个主流文化的国家选择的结果了,所以他就必然要红了。 此间:我们在相关的报道中注意到,丁真走红之后成为了一名国企员工,还在仓央嘉措博物馆之类的文化景点担任讲解员。他走红后的每一步是怎样安排的?为什么他的工作除了理塘的代言人之外,还可以延伸到这么多文旅事业的细部? 张帆:理塘有好几个小型博物馆,比如有关于地方陶器的、地方纺织的,还有关于仓央嘉措诗歌的、关于318记忆的博物馆。博物馆也是这一两年刚盖起来的。所以说他们基层政府的文化触觉非常敏感。 理塘要说旅游资源,优势也不是那么明显。318线不经过它的古城,所以很多人经过318线就走了。好多人对于西藏的想象大概是牦牛、草原,所以过去看一下毛垭草原,跟牦牛合拍几张照片,就走了。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游客,就把古镇重新打造,建一些博物馆。他们的出发点也是希望能够和地方居民有一些互动,所以博物馆都做得很小,而且在民居里面。  2020年7月中旬开幕的理塘“318旅行记忆微博物馆”/ 图源网络 因此,丁真在成了“旅游大使”之后,同时做博物馆的讲解员,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安排。他可以推广一下古镇本身的文化底蕴。仓央嘉措就是理塘一个很明显的符号嘛。研究西藏文化的有一批人最初是被仓央嘉措的情诗给带进去的,他太过浪漫化了。他在诗里面很明确地指出来,说他将来是要转世到理塘的。所以理塘在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就一下成了整个西藏世界的圣地之一了,所以(理塘)也是跟仓央嘉措这个符号是分不开的。 我觉得扶贫不光只是要让地方人吃饱——理塘人对物质的要求没多高,你真给他弄一桌什么海鲜,他们也是不吃的,因为西藏人是不吃海鲜的。所以他每天吃点糌粑,吃点肉包子,他就觉得生活很好了。他的追求不在这方面,他不是只要吃饱了,他就过好了。所以现在的扶贫工作也在关注,怎么让地方的文化世界或者地方的精神世界更丰富、更富有,怎么能够把地方的文化给挖掘出来,让这些大家原本觉得不重要,但非常重要的事情变得重要起来。现在当地人都会觉得很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我们有那个。丁真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对扶贫而言,对他的要求又提高了一个层面,就不只是饱肚子的问题了,是要饱脑袋的问题了。 此间:在您看来,丁真的走红对于藏文化的宣传有一个正面的推动,还是说您会有一定的担忧? 张帆:我现在还在静观其变。这个事情一直在酝酿、在发酵,有大量的关于这个事情的讨论,不管是正面还是反面的,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觉得有辩论倒是一件好事。 比如网上会有人说丁真为什么不上学,这打开了某一种讨论的可能性。我们大量在内地成长的孩子们,很难去想象竟然还有人能够不去上学。但你一旦到了西部,或者甚至是内地的很多贫困的地方,是很好理解的。 像是在理塘,有一个概念叫“完小”。你知道“完小”是什么吗?你不能理解对吧?“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为什么在理塘会有一个小学叫完全小学?因为在理塘很多的乡、村子里没有完全的小学,一到三年级就叫小学了。到理塘县了,才终于有一个完全小学,就是一到六年级都有的。那你想想从乡里、村子里要到县里面来上所谓的“完小”,路上代价是非常大的。 你要想理塘的地理环境。比如说丁真所在的毛垭草原,从毛垭草原开车到理塘县城都要一两个小时。虽然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尤其是在这种少数民族区域,上学的费用是国家全包的,甚至有些地方还给补贴,比如你吃饭都不用自己给钱,但是会有一些现实的情况导致很多理塘的孩子不上学。 理塘虫草资源非常丰厚,挖虫草一个月,挣的钱就足够过一年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上什么学呀,虫草季节来了,咱们挖虫草去。以至于很多学校后来就会强迫这些小孩子必须要上学,学校要去动员这些家长,可是问题是如果家长真的把小孩带到山上去挖虫草,老师根本找不到这些小孩。 这里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说丁真是个九年制义务教育漏网之鱼这么简单、扁平的一个话。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如果能够持续地被讨论,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们理解,扶贫是一个很具体的过程,它不是一句话或者是一笔钱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希望大家能有体认,而不只是停留在语言上或者键盘上。 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又在讨论说,理塘号称是刚脱贫的贫困县,丁真竟然用了一个那么贵的手机,还穿着什么名牌的衣服。 这就扯到万玛才旦的电影《气球》,你会看到那里面很多藏民都穿得上各种名牌的衣服。那些都是假的。各种什么阿迪、耐克,logo越大的衣服越可能是假的。你看丁真他手上会带着各种各样的金戒指、珊瑚,一方面很有可能它是假的,另一方面,即使它是真的(也可能是村落或者家族共有的,是有仪式功能的)……我在理塘参加过一个婚礼,那真的是隆重。理塘女孩子头上戴的珊瑚珠这么大一颗,她能戴几十颗,身上金的银的都有。理塘姑娘在结婚的时候,人都被变成一个博物馆了!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全挂在她身上了——金银珠宝、松石、珊瑚石……后来我就问结婚的女孩,我说你们家的传家宝吧,这么贵重,她就跟我说不是,这都是借的。  电影《气球》剧照/图源网络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想象。汉族人倾向于认为财富要攒起来,银行数字越高,就说明我这个人越有钱。这是一种非常积累性的世界观。但是很多其他的民族,包括像西藏,他们的财富观念是这个钱得花出去,才能代表我有钱。我钱都在银行里,谁看得见?没人知道。所以我就把它挂起来,穿起来,花起来,烧起来。 所以你看,理塘它是个贫困县,但它过节日的时候,像我这两年夏天的时候去,他们都要去耍坝子。耍坝子,和野炊、野餐、露营的概念很像。因为那儿到处都是草原,海拔又很高,所以一年可能就两三个天气好的月份适宜在户外活动,剩下漫长的九个月十个月都太冷,不太适合户外活动。所以在两个月期间,大家就会在草原上扎帐篷,什么活儿都不干,一切活儿都停下来(生活像被按了暂停键,连医院都只有急诊开着),甚至一个家族在外面吃喝玩乐。他一年挣的钱,可以在两个月就把它吃喝玩乐全烧掉,这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概念去评判他人这么穷,为什么还不攒钱,是不是道德上有问题,这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我们太习惯于认同我们自身的价值观、财富观,对于另外的可能性,有的时候是视而不见,有的时候根本连看都不去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可悲的事情。所以丁真的这个事儿如果能让我们有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好事。 也许有人会说,国家的扶贫款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凭什么流向西部被这样“挥霍”?一方面,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含义就是杜绝“输血”,所以大部分的扶贫款并没有流向个人,而是被用于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大家才看到理塘这几年逐渐通了电、通了水、通了路、通了网,虽然水管冬天还可能会被冻裂,电网在用电高峰会短路,网络在草原或者山区常常是没信号的,但是,总体情况在好转,很多理塘人的汉语不好,大家就把快手抖音作为“社交媒介”,尝试向现代生活“plug-in”。另一方面,其实,藏民们对于生活的物质的要求并不高,他们会把钱财用于信仰和仪式的支出,耍坝子最初也有着仪式功能,类似于我们的庙会,大家一起喝茶吃肉、跳舞唱歌、赛马祭山。所以所谓“挥霍”,和我们内地很多对于奢侈品的挥霍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的。
 此间:我看到有一些评论文章说,丁真所代表的想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香格里拉”——人们想象中纯净、远离世俗污染的异域。您会赞同这种观点吗? 张帆:我特别赞同。对任何异文化或者是这种所谓exotic的符号的追求,一定都是你自身的某一种欲望的投射,我觉得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不会像萨义德这么悲观。我觉得一切人在面对跟自己有差异的文化和人群的时候,必然都会产生这种非常东方主义式的——西方主义式的也好、南方主义式北方主义式,你管它叫什么主义——你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中既有美好的成分,也有丑恶的成分,我觉得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我不可能假装对你没有好奇,我也不可能假装说我对你不做想象,而是要承认我在好奇和想象的过程中会对你有歪曲,我会在跟你贴近的过程中慢慢让歪曲,变得不那么歪曲。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 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图源网络 他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是没有真实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 尽管我认为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无差异的对于异文化的认识,但至少在文化跟文化的惺惺相惜中,是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欣赏的。所以萨义德可能太过极端和悲观了,我没有那么悲观。 此间:您觉得丁真的宣传带来的大家对理塘的向往,会帮助人们修正歪曲的想象,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异文化景观吗? 张帆:我并不期待一个全民性的田野工作。最后能够身体力行到了那里,去体认当地世界的人毕竟是少数。但我觉得即使是少数,有也比没有好。在这之前,或许连理塘在哪儿都没有人知道,甘孜是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康巴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没有人知道。现在大家至少知道了它的一个面向。这面向或许是扭曲的,或许是扁平的,或许是窄化的,但是它也会激发一小部分人真正去了解它的愿望,最后付诸行动。我还比较乐观,这未尝不是件好事。 此间:我看到有一种概念叫“自我东方化”,比如说一些中国拍摄的影视作品中会固化一些文化符号,去迎合西方认知中的“东方”。您觉得在“汉人-藏人”的这种“中心-边缘”结构中,理塘把丁真、赛马固化成文化符号,以吸引大众,这是一种“自我东方化”吗? 张帆:“自我东方化”的批评最早大概指的就是张艺谋的电影。像李子柒这样的角色,最早出来的时候,大家也有很多这样的批评。但是她一直火到了国外,就有一些反转,大家会觉得不管怎么样,她把东方的文化推广出去了,不管这是不是以自我东方化的形式。这至少让我们文化的不同侧面被展现出去了。 所以那些认为丁真自我东方化了的人,似乎认为藏文化只可能有一种面孔。当它有另外一种面孔出现的时候,他或许就是在迎合谁。我觉得这个是有点过于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分析了,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面向,有一些面向被人认识了,有一些面向我自己隐藏了,或者没有被人认识到。 我觉得你要给一个人充分展现它的空间和可能性。丁真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并不直接认识他,但我认识很多当地跟他很像的小男生——20岁,像我学生这么大。他们确实有很多是这样,真的是乖乖的,长到20岁都没有走出过家乡,甚至都没有去过理塘县城。他对于很多地方是不会有想象的。比如说你问他要不要去成都,不想去,你想不想去北京,想想说有点害怕。我们一方面会认为康巴汉子充满野性,是一个敢闯天下、什么都不怕的角色。但是也同样存在着这样一些,相对来说很乖很奶,哪儿都不想去,他就想在家里面按照一定的节点娶妻生子,放牛,他就很快活。所以我觉得丁真展现了藏文化的多元性,没有那么截然的是一个自我东方化的过程。 此间:如果说丁真是一个被动进入大众视野的人,那么您前面提到的万玛才旦导演,则以藏族艺术家的身份去主动地展现一些藏区的风物。这种“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的人的出现,会是一种更好的传递当地故事的途径吗? 张帆:我觉得必然是。我会期待更多的所谓藏族的艺术家能够发出声音。 万玛才旦在我的眼里,不只是个艺术家了,他是一个非常复合型的知识分子。他有非常复杂的对于世界的思考,虽然他呈现的媒介可能是小说或者电影。但是我所认识的一大批安多的艺术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是这样的复合型学者。 在他们身上这种复合性体现得很好,不像我们——我们恰恰是比较狭隘的,只有对自己学科的了解,对学科以外,其他东西要么不了解,要么就根本没兴趣。他们对于世界的体察是全面而细致的。所以有更多这样的人发声讲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此间:万玛才旦导演的很多作品中都探讨了现代化对当地民俗文化的冲击。您在当地的经历中有相同的体会吗? 张帆:万玛才旦导演会有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这决定了他所要反映、表达的主题。我觉得他对这种冲击的感受会更深刻。毕竟以少数民族这样的身份,后来到很多地方求学,包括现在成名了在全世界游走,这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不断感受冲击的过程,他会非常直观地把这种冲击转化成他的创作主题。  2020年12月3日,北京大学MFA艺术放映系列活动中,张帆与万玛才旦的对谈现场 /图源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对于我来说,我也会有冲击,但那种冲击跟你作为一个少数群体感受到的那个冲击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我当然会认为它(其他文化)保存得跟我越不同越好,就好像我们很多人去拍照,一边拍照一边诅咒说“这里有个电线杆子太难看了”。可问题是,你在享受通电的便利的同时,不能剥夺别人享受通电的便利的权利。我当然会希望他们能过好,我希望我在理塘的朋友们都能有水有电,不再生病,没有寄生虫,会希望他们享受到洁净的生活和现代的便利。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能保存一些差异,希望这些差异不要因为这样的生活而最终消失,当然这可能出于我自己比较自私的想法。 但后来我也乐观地发现,好像也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现代性的冲击能够完全抹平差异。我觉得不管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好,还是现代性的扩张也好,它真的像水一样在流动,会在某一些区域渗透,但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水泥的地面,它连渗透都渗透不了。我相信我那些理塘的朋友会有选择地吸收这些东西。比如他认为有电是好的,有手机是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会有选择地排斥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依然还是喜欢用手来揉糌粑,尽管很不卫生;还是喜欢在草原上扎个棚子,尽管棚子很不保暖;还是在8、9月份跟全家人到坝子上去吃喝玩乐,也不去挣那些打工可能带来的钱。他还是会有一些对于这些方面的天然抵抗,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焦虑。
此间:您之前提到了丁真所在的康巴藏区和万玛才旦来自的安多藏区的区别,也提及了“藏彝走廊”的相关概念,似乎藏文化不像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样集中于西藏拉萨,而是不断流动的。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藏文化现在的分布情况吗? 张帆:藏文化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了。如果只看中国,藏地跟内地的互动开始得非常早。理塘就有一个文成公主塔,尽管我觉得历史上文成公主进藏一定走的不是那条路——因为那条路太不好走了,一般都是走青海——可是当地人会用这种方式去去铭记一段历史。那也就说明,汉藏文化交流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来讲都是好事。前年我为了研究藏戏去理塘,当地人因为我去了,特意把他们本来要排的一个很经典的叫《卓娃桑姆》的藏戏换成了《文成公主》。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汉族人,要表示友好,我就要跳一出跟你有关的戏。我只是想用这个小例子说明,文化交流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它有非常积极的面向。  理塘当地的藏戏 具体到我自己的研究,我的博士研究关注18世纪乾隆年间,我们能想象的最直接的东西——雍和宫变成了一个藏传佛教寺庙。我曾经在清代的一个御制全图,应该是一个18世纪或者19世纪初做的关于北京城的一个图,把上面的藏传佛教寺庙全部给重新定位了一下,发现在乾隆年间,北京内城的藏传佛教寺庙有几十所,在北京的藏传佛教的僧人——当然不一定都是藏族人,也有蒙古族、土家族、满族、汉族的,但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就有几千人。 现在大家看到的护国寺小吃,最早为什么会有?是因为当时护国寺是一个藏传佛教的寺,有很多信众需要在那里求请一些塑像,还有一些仪式用品,所以他们会在固定的时期开市、做买卖。那里后来就变成我们所谓护国寺的一个集市了。而今天,它的藏传佛教背景已经完全被淡化、被淡忘了,但在历史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藏传佛教在北京的痕迹。 包括像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清朝在很多地方都会存在这样的所谓文化杂糅的区域。不光是藏传佛教了,像中亚、蒙古、萨满文化的因素都有。至少在18世纪,在我们所认为的中国政权的核心,都遍布着各种文化形态,它都不是单一的、我们所认为的儒家主导的汉文化。 这个是我的研究想要展现、并且我自己特别想要强调的,就是要充分意识到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它本身内部是非常复合且多元的。我们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这么欣欣向荣的局面,恰恰在于我们的滋养是非常多样的,所以我们才更健康。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这些不一样的成分。 如果让我说藏文化,它真的就不是一个以拉萨为中心的这么简单的区域性分布。任何文化都是这样的,不光只是说是藏文化,任何文化都具有世界性。
 此间:我们刚才提到了丁真、万玛才旦,以及您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从媒体宣传、艺术创作和人类学研究三个不同的维度去接近藏区的一种真实。您认为这三者的机制有什么区别吗? 张帆:艺术创作的话,我是不懂,因为自己也没有切切实实去创作个什么东西。但我觉得艺术创作是要保持一种想象,所以不能对艺术家在真实性上过于苛求。恰恰是这样一种他自身的想象力和对于那个世界的某种远离式的体验,才可能真正激发他的创作力。 像我做人类学,当然不是说展现的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会期待尽可能贴近真实,但这个贴近真实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那个世界的那一群人慢慢变成了我的世界,慢慢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他们对我开始失去吸引力,他们不再神秘了。这些人开始从一种审美的存在变成了一种生活的存在。如果我是个艺术家,我可能就会丧失创作的欲望和冲动。 媒体宣传,在我的理解里——这可能要得罪新传的同仁了——我总觉得他们会尽快地抓取或者提炼某一些关键词或者关键意象,把这种关键意象做重新的组合,找一些渠道扩散。可能媒体更重要的是更快地提取和扩散。所以如果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更大的视野去关照一个地方或者一些人,他们就会变得犹豫。假设你要问我康巴是什么样的,我会说,让我想想吧,我大概可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告诉你。但这对于一个媒体来说,就成了问题。它只是需要一些关键词,它不要犹豫,它不要反思我这样是不是东方化它了,而恰恰是就要彻底把它东方化,把它推广。 这是我自己认为的这三个不同方式的差异,或者也可能是我自以为是的差异。像人类学,我觉得我们这个学科更像是手工作坊,你得用上几年的时间,泡在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接触,真正地把这个地方和这群人变成你的世界。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去理解他,呈现一个你所能理解的真实,或者只能说是在某一种理解上更全面。我们需要的时间更长,周期更长,最后出来的成果也是更无聊的。你读了我的东西,你会觉得,这不就跟我的生活一样吗?有啥可读的?我照照镜子,想想我自己的人生历程,似乎跟他们差不多。我觉得这就是人类学的一个工作吧,就是告诉你在看似差异很大的现象之下,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性。毕竟都是人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人性,这是我们学科的一些追求。 此间:您会觉得在文化交流中,或者说任何与他者的交流中,接近真实是必要的,还是说大家有各取所需的真实?比如说人类学研究和媒体所需求的真实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张帆:我不太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绝对的真实,任何的真实都是相对的。生活本身更像是一场交往吧,不论是生活中的交往也好,学科中的交往也好,本质上都很像一个中医看病的过程。并不是我要把这个人当成一个死人,来看他各个器官、脏腑、血管、神经。这个人是个活的人,这个群体是活的群体,我要像中医一样,我要用我的脉搏来看他的脉搏,所以我要时时刻刻地看他也看自己,这个是交往的一个出发点。 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保持这样的态度和真诚,这就是很真实的一种交往以及一种很真实的知识,而不在于说我要寻找绝对的真理。常常有人打着绝对真理的名义进行各种各样的讨伐,就像是十字军东征,我认为我的上帝是真的,你的上帝是假的,我跟你打一仗。但如果大家都更真诚一点,把彼此当人来对待的话,那也就不再存在到底我的神是真的还是你的神是真的这样一种争论。大家会更加包容地认为我们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做到互相理解,一定程度上互相尊重,我觉得这就很真实了。 此间:现在作为一名人类学学者,您会建议大家怎样在各种文化中更好地进行交流和相互理解? 张帆:我觉得最好就是以心度心,把他当成你的朋友而不要先认为他是一个喇嘛或者一个藏民,跟他产生某一种距离。就好像我的学生去做田野,跟一些老人做访谈,完了就认为这些老人好像也提供不了什么有效信息,甚至有一些人比较狡猾,故意规避他们想要得到的信息。我觉得,你不要太过功利,就认为这些人只是在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这样这些人就不是人了,成了一个一个长了肉的数据了,这种态度本身是你的问题。你要先把他当成人——如果你跟你奶奶这样聊天,你会聊些什么?再跟他去聊。当你以心度心把他变成你的朋友、你的亲人,这个时候可能真的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智慧。  张帆在毛垭草原,图中黑色帐篷为传统的藏式帐篷“黑牦牛帐篷” 不光只是对西藏了,我觉得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有一种更开放的心态都是有益无害的。很多人可能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经历过很多。但这个世界是很多样的。过早下定论,或者过早划界限、过早设立场,这本身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还是应该时时刻刻对自己有一些反省。比如说,我一旦有了这样一种见解和定论,这个见解跟定论在多大意义上、在什么范围内是适用的?而不要把它普适化到所有人。 假设人类学这个学科它还能有一点点用的话,最好就是说,人类学是一门“以他者为上”的学科,是以尊重差异为前提的学科。必然是因为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才去研究它,或者我才去思考这种差异,而不是要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把所有的差异都视为不道德的,要把差异灭掉。我看到有人在网上持这种态度,我都觉得很难过。
文中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受访者。  新媒体编辑|王朗宁 陈子衿 责任编辑|戴汀屿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