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话古尔纳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莫言的家乡是 › 莫言对话古尔纳 |
莫言对话古尔纳
|
2024年3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先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与同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莫言,进行了题为“文学的故乡与他乡”的文学对话,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神盛宴,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马骏教授出席并代表学校致辞。 对话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与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举办,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中文创意写作研究所承办,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教授担任现场主持。  马骏校长代表北师大向古尔纳先生赠送礼物 莫言先生在开场致辞中幽默地表达了对古尔纳先生及夫人到访的热情欢迎。他提及,尽管科技日益发展,“给文学敲警钟”的言论层出不穷,但事实证明,文学永远不会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消亡,自己与古尔纳并不会因为AI的出现而“失业”,因为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这种思维的获取,需要从本民族传统里面寻找不可代替的资源,并且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广泛接触人类共同的情感体验与现实追求,让文学可以真正走向世界,而这正契合了古尔纳先生的文学追求,也是今天这场对谈得以展开的基础。  莫言致辞 古尔纳在开场致辞中感谢马骏校长和莫言先生的热情欢迎,他十分赞同莫言对文学事业与文学力量的判断及阐发,也非常期待今天的对话,期待看到中国读者对自己作品的阅读反应。  古尔纳致辞 在文学对话环节,两位作家从“故乡与他乡”谈起,非洲对于古尔纳先生来说是“故乡”,而对于莫言先生来说则是“他乡”。莫言先生认为过去从作品中了解到“文学的非洲”与真正看到“现实的非洲”有很大不同。他曾在玛拉河边等待着看成群结队的动物“英勇”过河的壮观场景,但始终没有等到;那些有耐性的、美丽的金色鳄鱼,的确会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任凭飞鸟落在它们身上,任凭阳光曝晒、劲风吹拂;而当眺望“乞力马扎罗的雪”时,他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小说中那只高山上冻僵的豹子——“它是为了追寻光明和理想爬到高山,它的牺牲有一点壮美的境界。” 对于古尔纳而言,非洲则承载着不同的记忆:他的故乡是非洲的一座小岛,那里有大片的海滩——“我们的海滩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和世界进行着连接,与世界的其他文化进行着跨大洋的交流。”正如当年郑和船队的到来,让非洲了解了中国,家和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莫言进一步提出,随着作家创作经历的延长和活动半径的扩展,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纳入作家“故乡”的范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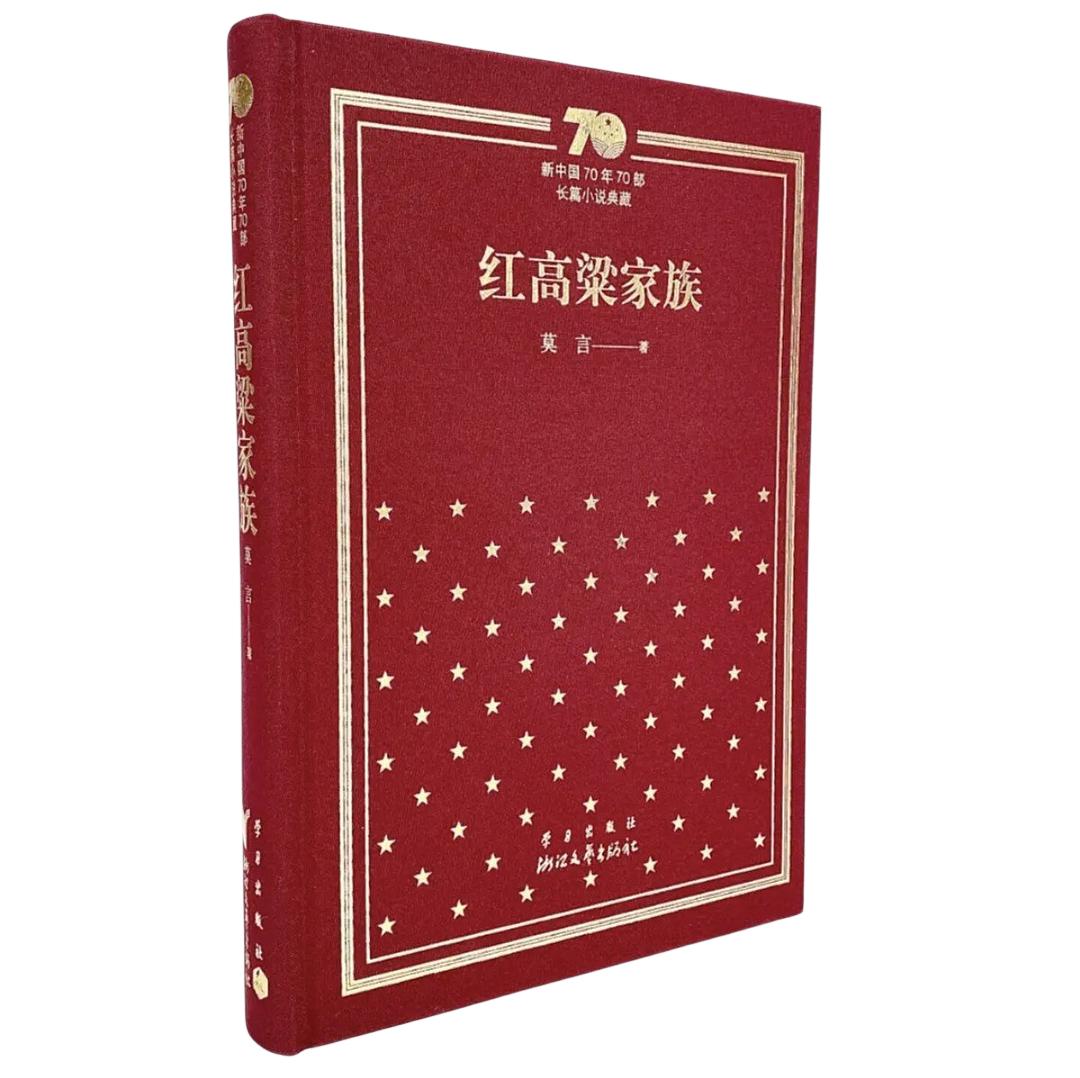 《红高粱家族》(左)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红高粱家族》(右) 莫言 著 从故乡与家乡的话题延伸,古尔纳谈到对莫言《红高粱家族》的阅读感受,他非常喜欢这部作品的语言描写、叙事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气息”,他称赞莫言的小说特别擅长书写一个普通人在宏大历史中具体经历了什么,这对于读者而言是具体可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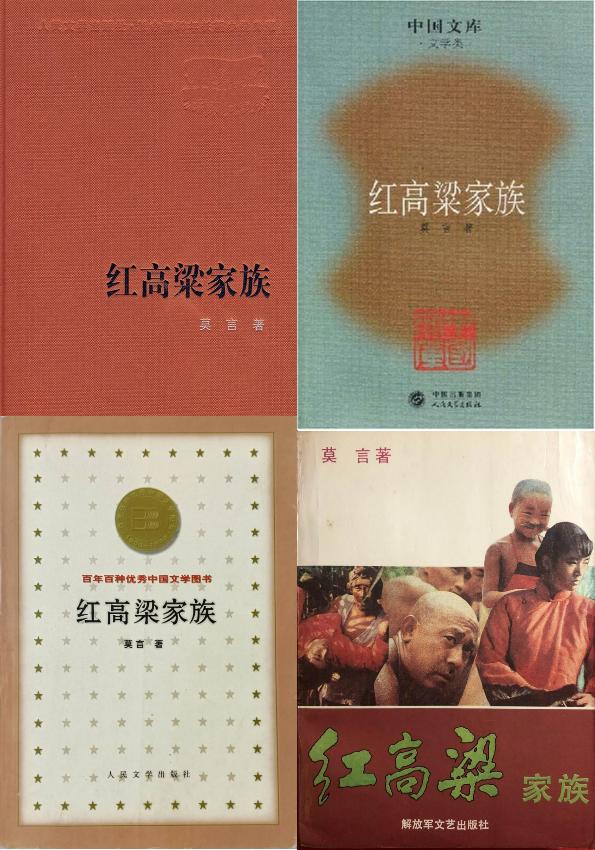 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版《红高粱家族》 中国文库版《红高粱家族》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系列《红高粱家族》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红高粱家族》 莫言则从“讲故事”的角度强调,作家的写作一定脱离不了自己的故乡。一个小说家的自传往往就体现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小说家的自传或许包含着小说的成分,但小说家的小说却恰好表现很多自传的内容,这不是诚实的问题,而仅仅是艺术的问题。他以古尔纳的《遗弃》为例进一步说明,小说家不会像历史学家一样全方位、立体地描写一场巨大的变革,小说家更擅长的是“由小见大”,从一扇窄门进到宽广的世界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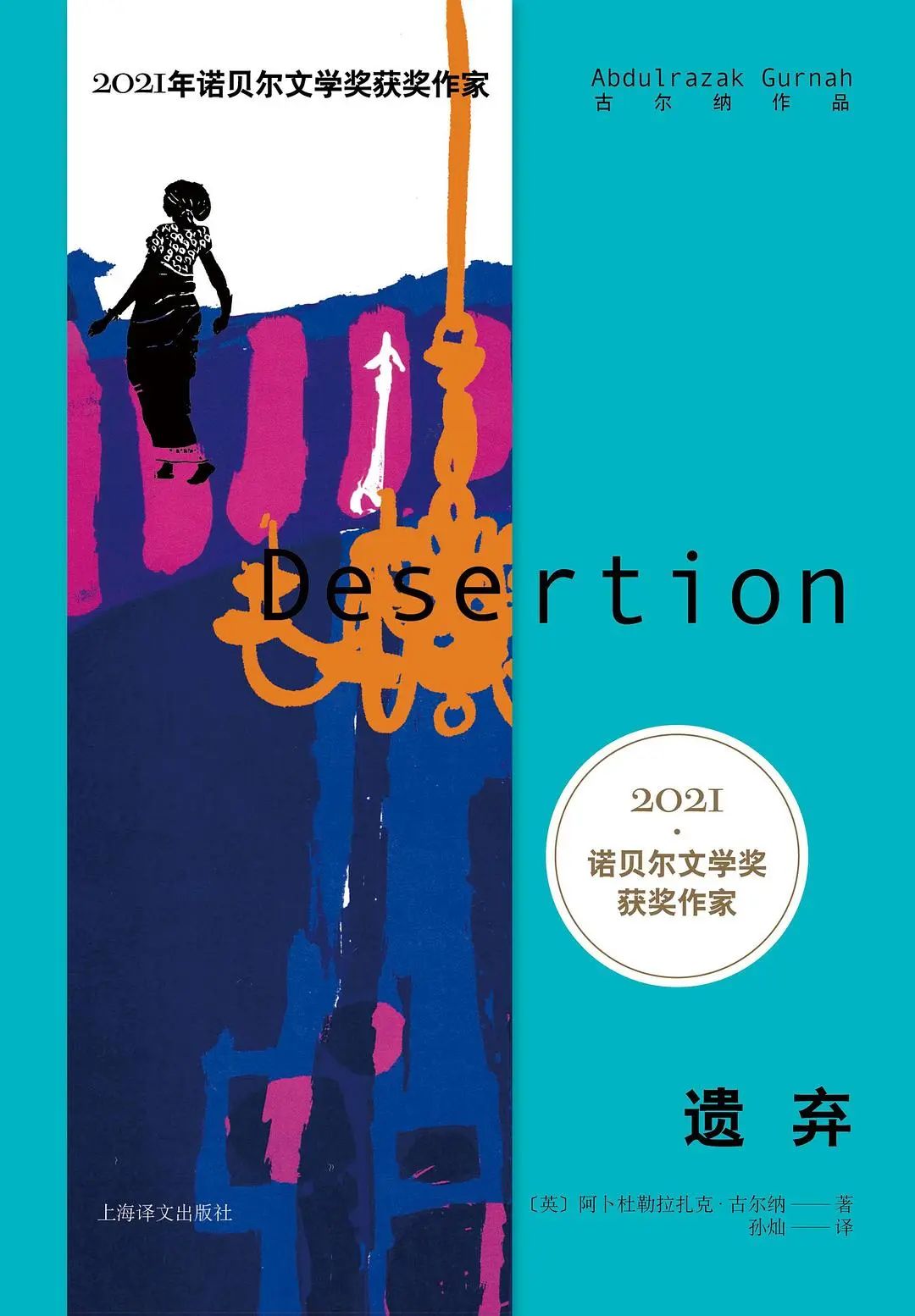 《遗弃》,[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著 在“小说家”之外,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还有另一重身份。古尔纳先生是非洲文学、殖民文学和后殖民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莫言先生同时是一位剧作家。如何在两种不同的身份之间切换?古尔纳认为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是他的志向所在,两者间不会难以平衡。在写作学术专著和论文时,他会采用学术化的语言、丰富的支撑材料以及权威的口吻,尽可能做到全面覆盖;而在写小说时他是完全自由的。 莫言也介绍了自己创作戏剧的初衷与心得,他曾三次去往莎翁故居,走遍了那里的大街小巷,还在斯特拉夫堡的街心公园发现了一座牡丹亭。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是同时代东西方的伟大戏剧家,《牡丹亭》突破了生与死的界限,情到至深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爱情高于生死,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是如此,可见伟大作家捕捉到了人类情感深处的相通。  对谈临近尾声,张莉教授将话题引向创意写作教学。莫言表示,多年来在北师大的写作教学积累了宝贵经验,学生们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上发表优秀作品。国际写作中心成立了创意写作工作坊,定期组织改稿会,邀请批评家、作家和编辑,共同研讨学生的作品,通过这个形式可以为文学队伍源源不断地培养作家,相信假以时日他们就会成为文坛的主力军,“北师大作家群”也将从梦想变为现实。 古尔纳虽然没有直接教授过创意写作课程,但他提到英国很多学校都开设了这一课程,选课人数大大超过了可选人数,也超过了文学类课程的选课人数,足见学生的喜爱程度。古尔纳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建议,初学写作时需要自己学习摸索,写完后要尽可能请别人阅读,了解读者的意见。他认为创意写作课相当有价值,应该鼓励学生,帮他们指出正确的写作方向,教他们如何能够被读者熟知、理解与欣赏。  这是一场文学史上星光闪耀、熠熠生辉的对谈,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文学的故乡与他乡谈起,触及小说的历史与真实、写作的经验与技巧、文学的地方与世界等诸多话题,思想的碰撞、情感的共鸣,让我们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共识与深思。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供稿,李昊 吴烨。有所删减) 2021年,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因“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而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也曾在一次演讲中谈论过离散和文学的关系。 离散与文学 莫言 | 文 (2007年11月9日) 我的学习英美文学的女儿告诉我,diaspora的本意是指离散在外的犹太人,后又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人。因此,仅仅用“离散”这个词,并不能完全代表diaspora的原意。 diaspora的确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与文学的关系,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今年的9月,我与访问中国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进行过一次谈话,我们谈了阅读彼此作品的感受。 他说他从我的作品里读到了中国乡村生活的画面,感受到了中国下层百姓的痛苦和欢乐。我说我从他的作品里读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当今世界上的艰难处境和犹太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读到了像柳絮一样飞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悲剧命运。  莫言与阿摩司·奥兹 当然我也读到了他在小说里表现出的那种理智和宽容。我觉得像阿摩司·奥兹这样的作家,就是几千年来始终处在离散中的犹太民族的文学代言人之一,而他的文学,就是典型的离散文学。 离散是一种千百年来就存在着的人类处境。这种处境可能是一个民族的处境,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处境。 造成这种处境的原因可能是战争、灾荒、瘟疫等不可抵抗的外力,也可能是一个家庭或者个人的主动选择。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离散,都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一个培育文学感情的温床,一种观察世界的文学眼光。 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有一批身处离散境遇的作家像灿烂的星斗在闪烁。如祖籍印度、现居英国的萨尔曼·拉什迪,祖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现居英国的V.S.奈保尔,祖籍日本、现居英国的石黑一雄,原籍俄罗斯、现居法国的安德烈·马金尼,原籍尼日利亚、现居美国的奇诺瓦·阿切比,原籍南非、现居澳大利亚的库切,原籍阿富汗、现居美国的卡勒德·胡塞尼,等等。这些作家,都在世界文坛上获得了巨大的名声。  石黑一雄 他们都因为其离散的处境,而获得了澎湃的创作动力和丰富的创作资源,写出了名扬世界的文学作品。 他们虽然人在异国他乡,描写的却都是他们母国的往事,利用的也大都是他们母国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因此他们的作品,就具有了与西方作家迥然不同的个性特征和民族特色,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和批评界的关注。 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创作,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 从人类的一般情感来讲,离散的处境最容易产生的情感就是思念。在世界文学的浩瀚海洋里,怀乡、思亲、伤别离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的古典作品中,都洋溢着浓浓的乡愁。人们在离散的处境中,总是愿意把故乡理想化,总是会忘掉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甚至伤害过自己的丑陋,总是愿意用理想的花环,来装扮自己的乡思。 随着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变迁,人们,尤其是那些身处离散之境的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用含着热泪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母国与家园,已经不满足于把对母国与家园的描述停留在肤浅的歌颂上。  这些身处离散之境的作家,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开阔了视野,拓展了精神的疆域。 这些作家的父母之邦基本上都处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发达国家,有的甚至还处在愚昧落后的状态中。 但他们都在西方发达国家接受了现代教育,都能熟练地使用西方语言讲话与写作,对西方社会有不亚于当地人,甚至比当地人还要深刻的了解。 但他们的根不在这里,相对于西方人,他们永远是精神上的外来者。他们的血液里流动着的文化基因来自他们在亚洲或者非洲的母国,他们的深层心理结构和文化记忆来自他们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和心理矛盾,就促使他们时时刻刻进行着比较。 他们其实是永远地处在两种文化的挤压与冲突之中,由此他们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目光。这目光已经不是被单纯的乡愁浸润着的目光,而是一种冷静的、批判的目光。 由此,他们的创作便呈现出崭新的气象。这样的文学已经不是简单地可以归属为东方或西方的文学;这是越界的文学,也是跨界的文学;这是边缘的文学,也是中心的文学;这是一种新形态的世界文学。 在这样的文学中,对于母国或家园的描写,已经超越了歌颂与怀念的层面,而是一种在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下的清醒审视。这里面尽管没有太多的对于西方社会的描述,但西方文化的影响却渗透在字里行间。 这里的批判也不仅仅是针对着母国的,也是针对着西方的。其实,这些离散的作家,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上,相对客观地描述着两种文化、两种价值体系的对抗和冲突,渗透和融合。  正在世界文坛上大放异彩的离散文学中所表现的母国与家园,其实大多数都是作者对母国与家园的想象。 新的离散文学中的母国与家园,应该是作者的艺术创造,与作者真实的父母之邦有着巨大的差别。这是一次真正的超越,是一场文学的革命。 通过这样的文学,离散作家们不仅仅向西方的读者,而是向全人类,奉献了一片片崭新的大陆。这些大陆在现实的地球上无处安置,只有在文学的世界里,方可存在。 在科技日益发达、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今天,母国与家园的意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离散之民,恒定不变的家园已经不存在了;所谓永恒的家园,只是一个幻影。 回家,已经是我们无法实现的梦想。我们的家园在想象中,也在我们追寻的道路上。因此,我们都可以算作离散作家,我们所写的作品,都可以划到离散文学的大范畴里。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想象和热情,在虚构着我们的家园;我们也都在借用着母国与家园的母题,来表达我们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 我们亚洲和非洲的作家,生活在物质相对落后的国度,但我们同时也占有着独特而丰厚的文化资源。 尽管我们不可能像那些生活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离散作家那样“身在西方,心怀祖国”,但信息化时代,已经可以使我们“身居祖国,心怀全球”。 我们不仅可以从本国和本民族的生活中获取创作资源,我们也可以从世界文化中汲取营养,来丰富我们的头脑。作家是有国籍的,但文学是无国界的。 我们可以从离散这一母题中,获得理解、尊重和宽容,创作出属于全人类的文学。 本文收录于莫言演讲集《我们都是被偷换的孩子》   原标题:《莫言对话古尔纳 | 世上的一切都可以是故乡》 阅读原文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