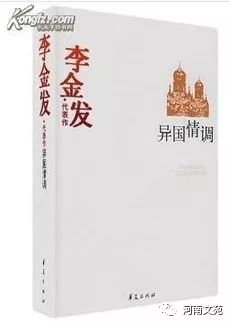诗经驿站(九)失乐园的哀歌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自我之歌的主要象征 › 诗经驿站(九)失乐园的哀歌 |
诗经驿站(九)失乐园的哀歌
|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李金发”是一个被淡忘的名字。然而正是这个李金发,在20 世纪20 年代,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才能和表现手法开创了中国象征派诗歌先河,他的诗以神秘、怪异、晦涩、颓废引人注目并因此受到批评,被评论界称为“诗怪”。 对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评论总是毁多誉少,他的诗成为食洋不化的例证,人们从功利角度看待李金发其人其诗,进而连他对诗歌艺术的独创精神、审美价值乃至他对新诗走向繁荣所作的有益尝试和探索都一并抹杀,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诗歌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是有其独立性的,它和其他任何一种文学样式一样,可以为政治服务,但又不属于政治,不能当作代言工具而丧失“自我”。诗歌是心灵的产物,其本质是艺术的,因此,只要符合文学自身的规律,具有审美价值,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和审美的愉悦,也可称之为“好诗”。我们认为,评价诗歌作品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客观的态度对诗歌本体进行从释义到审美的评论,主要标准之一应该是其审美意义及是否符合艺术自身规律,这也是对文学艺术的 一种尊重。我们试图从审美是“自由的精神释放与超越”[1]这一角度,对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作一客观的评价。
一、失乐的歌者 李金发(1900—1976)早年留学法国学习雕塑和诗歌,在学习艺术之余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法国文坛浓郁的象征主义氛围中,对象征主义诗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受波德莱尔、魏尔兰等诗人的影响,喜爱象征派诗歌并开始了创作。1925 年,李金发出版了诗集《微雨》,这部作品宣告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的诞生,此后相继出版的两部诗集《为幸福而歌》和《食客与凶年》,则奠定了他在中国象征诗派的“开山祖”地位。有人把1920-1927 年称为李金发的诗人时期,因其象征主义诗歌的主要作品大都于此时完成。此后,由于政治的、历史的、个人的原因,李金发几乎没有进行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 任何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象征派诗歌也是如此。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科技迅猛发展,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格局必然导致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孤独感和疏离感成了当时的社会特征。这时候的西方文学因之带有了浓厚的世纪末情绪和非理性色彩,人们的精神教堂轰毁了,心灵倾斜、心理失衡,传统信仰和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动摇,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时,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学说及非理性主义、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以及弗洛伊德关于精神分析和梦的解析,还有马克思主义都一起登上了理论的殿堂。悲观、怀疑、失望使得一些诗人们选择了以“唯意志论”及“超人”为基础的象征主义作为自己反抗的武器。象征主义作家不主张再现客观现实而强调表现主观世界,强调想像自由,追求内心的真实感受,反对说教和虚伪的感情,凭借直觉创造某种不可捉摸的意境,并以此来寄托他们的理想。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被五四惊雷唤醒的青年一代在短期的呐喊和兴奋后,随着五四退潮,革命低落、社会生活动乱,他们感到信仰和希望被摧毁了,那种前途渺茫、无路可走的痛苦和悲哀,使青年一代普遍患上苦闷、失落、彷徨的“时代病”。一些人为了摆脱内心的痛苦,把目光投注到大自然或农村乡间,也有一些人飘洋过海,去寻求真理或理想。而此时的李金发远离祖国,孤身飘零于异域,没有亲人和朋友,又遭受失恋的打击,精神的孤苦、爱情的挫折,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观和哀愁,加之忧郁的性格气质和与留学生们的隔阂,更加剧了他凄苦、愤懑的心境,因而,他只有把一腔的愁闷和悲哀寄之于为之狂热、为之倾倒的艺术了。发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崇尚神秘、象征、暗示,提倡臆造抽象的意愿,认为艺术的任务之一就是发现美和创造美,这一切正与李金发纯艺术而非功利性的文艺观及心灵颤动的频率合拍,加上反对传统、反对理性、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理论似乎给这个孤苦无依的漂泊歌者的心灵提供了一方宁静的停泊地,于是,李金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象征主义诗歌。
二、短歌当哭 李金发曾宣称:“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惟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惟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这正是他唯美主义文艺观和象征主义诗歌的自白。象征主义文学强调用象征的方法暗示作品的思想、事物的发展和抽象的哲理。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要让艺术把人们引向精神世界,去探索所谓内心的最高真实,表现不可知的宗教性的“彼岸世界”的奥秘。李金发曾说:“诗人因为意欲而做诗,结果意欲就是诗。”[2]因此,李金发的诗中表现了对人生的厌恶和失望,对命运的无奈和失望,死亡、颓废、寂寞等主题和坟墓、骸骨、荒野等词语处处可见。这与当时中国的现实主义诗歌揭露社会及浪漫主义诗歌讴歌理想都是格格不入的。难怪有人说他的诗“取消了为社会呐喊和对光明灿烂的、人道主义理想的讴歌,丢弃了诗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使命感。”[3]应该说,这是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看法,也是他的诗遭到责难的主要原因。李金发的诗虽然存在许多消极的东西,但事实上,李金发并没有完全回避现实和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他用特殊的方法隐晦、曲折地反映了社会,同时抒写了自己痛苦的灵魂。对此,我们从他的诗作中可以找到佐证。
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家国之歌 远离政治而醉心于艺术象牙塔的李金发毕竟还是一个善良正直的热血青年,他不可能脱离现实世界,更未忘情于故乡、故土及养育他的祖国和人民。他的诗集中不乏反映人民困苦与国家灾难、揭露丑恶现实的作品。《故乡》第二首中:“有时锣鼓鸣了,/ ⋯⋯ / 自然报点急警。/ 如兽群的人,悉披着上帝的使命,/ 出了刀与矛,奔赴前敌;/三十的跟了四十的,如海潮之汹涌,/( 热血更何须说!)/ 此后人稀了,钟儿更无人敲了! / 但铁链的光,仍是闪着。/ 树虽未秃,但鸟儿早已去了,/ 留下小雏的死骨!”表层意义是在刻画故乡强悍的民风,野蛮血腥的械斗以及械斗后的惨像。更深层的含义则是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现状愤怒的苦号!“树虽未秃,但鸟儿早已去了,/ 留下小雏的死骨!”让人想起曹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诗句,悲惨的诗歌意象给人以阴森凄凉的强烈感受,这种感受能够溶进人的思想和灵魂,使人产生不尽的联想。 《街头之青年工人》更是将阶级对立及其不同生活以鲜明的反差展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将因劳作,/ 而曲其膝骨,/得来之饮食,/全为人之余剩;/他们踞坐远处,/嗤笑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与剥削者的丑恶嘴脸一目了然。作者直面社会和人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生活,其诗歌容量和意蕴绝不亚于当时的《相隔一层纸》、《人力车夫》等现实主义诗歌。《恸哭》中,作者以带有神秘和哲理色彩的语言写道:“所有生物之手足,/全为攫取与征服而生的。/上帝,互相倾轧了!/ ⋯⋯ /群狼与野鸟永栖息于荒凉乎? /或能以人骨建宫室,/报复世纪上之颓败。”在物欲面前,人性泯灭,人与人互相榨轧与征服⋯⋯这里既是对人的“兽性”的揭露,又是对人类生存家园混乱动荡、弱肉强食的强烈不满与深切悲哀,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全诗反映了现代人的道德堕落和精神崩溃,对于否定社会的黑暗,是有积极意义的。 《春城》写游子怀念故国的痛苦和感伤:“心房如行浆般跳荡,/笔儿流尽一部分的泪。//当我死了,你虽能读他,/但终不能明白那意义。”流泪的思绪、跳荡的心房所表达的“眷恋祖国的情绪”,几乎与“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一样,甚至死了,别人也无法明白自己心底深藏的爱国情意。 这类感时伤民、怀乡恋土并透出现实主义微光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仍能看出一个青年诗人的心灵轨迹。至少可以说李金发并未完全游离于社会现实之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不可能大声呐喊、强烈反抗,只能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审视这个不平等的世界。他用自己的痛苦低吟、用自己的凄冷泪水来恸哭祖国的不幸和社会的残酷,用“另一种声音”以艺术的倔强来抗争,尽管是那样的无力和不被理解,但他抗争了。后来在白色恐怖的“四•一二”之后,他曾经多次营救进步学生,这些行为,显然是对当局的反感和抗议[4],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识和爱国之心。 (二)爱情之歌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诗神缪斯尤钟情于她。在李金发的诗中,歌唱女性几乎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他说:“愿永久做爱情诗,因为女性美,是可永久歌咏而不倦的”。他还认为,“能够崇拜女性美的人,是有生命统一之快感的人,能够崇拜女性美的社会,就是较进化的社会。”[5]他把自己的爱情诗称之为“公开的谈心”,“这种公开的谈心或能补救中国人两性间的冷漠”[6]。这种理论使他的一些爱情诗热烈而大胆,给新诗创作带来别开生面的景象,同时也颇具反封建的积极意义。如《温柔(四)》里的诗句:“我以冒昧的指尖,/感到你肌肤里的暖气,/⋯⋯ /你低微的声息/叫喊在我荒凉的心里,/我,一切之征服者,/折毁了盾和矛。”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爱情的怀抱,温柔深情,全无粗俗浅薄之感。爱情是如此美丽幸福,但这幸福又是那么短暂,留给人的是刻骨铭心的痛楚。爱让人欢乐又让人痛苦,因此,李金发的爱情诗很多是写失恋的。最具神秘与颓废气息的当数《夜之歌》:“我们散步在死草上,/悲愤纠缠在膝下。//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任我在世纪之一角,/你必把我的影儿倒映在无味之沙石上。//但这不变之反照,衬出屋后之深黑,/亦太机械而可笑了。//彼人已失其心,/混杂在行商之背而远走。//大家辜负,/留下静寂之仇视。//任‘海誓山盟’,/‘桥溪人语’,//你总把灵魂儿,/遮住可怖之岩穴,//或一起老死于沟壑,/如落魄之豪士。”这首爱情诗没有阳光、欢笑和甜美,正如他许多爱情诗篇多的是梦幻、伤感与叹息一样,诗中出现的“死”、“臭”、“朽兽”、“仇视”、“无味”、“可怖”、“深黑”这些词语似乎应与爱情无缘。古今中外诗人歌咏爱情总是将最美好的词语赋予她,李金发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因为失恋使他受到深深的伤害和打击,“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的抑郁情怀无处诉说,只有苦吟独唱,歌唱爱情失落后的伤感。这种爱情诗新巧的立意和出格的描写,可以说弥补了“中国缺少情诗”[7]的部分缺憾,同时,作者以审评内心迷蒙的情绪暗示了人生、爱情的无奈与悲怆。 还有《少年的情爱》、《钟情你了》、《心》、《美人》、《日光》、《她》、《在淡死的灰里⋯⋯》、《Elegie》(法文,“哀歌”之意)等都可称之为佳作,爱情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美”,更使他的诗平添了几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 (三)艺术与命运之歌 作为艺术的信徒,李金发对艺术与命运是始终保持一种思考与观照的。从个人主义立场出发,他是崇尚人性论的,对艺术、对个人乃至“人”的命运是有独特认识的,这种认识、思考和观照(还有反思与自省),构成了他象征派诗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题自写像》:“即月岷江底,/还能与紫色之林微笑。/耶稣教徒之灵,/吁,太多情了。//感谢这手与足,/虽然尚少,/但既觉够了。/昔日武士披着甲,/力能搏虎!/我么,害点羞。//热如皎日,/灰白如新月在云里。/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生羽么?太多事了啊!”与其说这首诗是满足于自己的漂泊生活,不如说是诗人面对可悲的社会现实与失落的精神家园的尴尬和无奈。再如《诗人的凝视》:“中伤的野鹤,/从未计算自己的命运,/折羽死于道途,/还念着:多么可惜的翱翔。”这个野鹤凄美的形象,实际上是在艺术美的追求和无限眷恋中不断挣扎的诗人自身的形象,也可看出黑暗社会环境对艺术的戕害和摧残,在以金钱与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中,艺术像被折羽的鸟儿在作临死前的挣扎与反抗。《有感》不足百字,却在首尾两次出现“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 的笑”,让人不寒而栗,不由得思考:生命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又是什么?著名的《弃妇》中,诗人用象征手法暗示人生如一个披着散乱长发、“徜徉在秋墓之侧”的衰老的弃妇,似乎表达的是对一个被生活遗弃的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悲诉,实则用象征手法谈论人生问题,进而深入到人性问题的理性思考:当正常的人类美好天性被社会所扭曲,被外物所异化、消弭,人的精神就被抛到了死亡的边缘。这个“弃妇”的意象发掘于人类灵魂的最深处,诗人在自省中发现了自我的渺小,这给人的就不仅是启示,更是震撼。读李金发这类诗是能够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大伤感的。这是灵歌,是哀歌,让人感到的是伤痛、空茫和虚无,却不能给人以拯救的希望。这正是它被视为颓废诗歌的主要原因。这些诗带给人的是感伤的美、凄绝的美,一种近乎病态的、耐人寻味的美。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 (四)自然之歌 李金发还有不少艺术上颇有生气的吟咏自然之作。它以新颖的比喻和象征将心灵与自然的交融、契合以及个人对自然的热爱、追求诉诸诗歌,引起了读者心灵的感发和共鸣。如《园中》抒写了无拘无束、平等自由的生存空间及理想状态,自然的乐园象征诗人内心向往的“理想国”,内在的诗情与外在的景物达到完美的统一和谐,给生存疲惫的人以精神的慰藉。此外,《盛夏》、《风》、《秋》、《律》、《无名的山谷》等都是各具特色的佳作。
三、哀歌之“哀”与不“哀” 说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为哀歌,是基于如下三点: 其一,主题之哀。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主题多为死亡、梦境、幻觉及破灭的爱情与凄惨的命运等,基调大都为冷色调,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色彩。其意象是黑夜、鲜血、灰烬,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死亡”、“血痕”、“眼泪”、“黑夜”、“梦幻”等与哀伤相关的词汇,从而改变了传统诗歌惯用的主题,为世俗所不齿。 其二,内容之哀。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歌咏家国、社会,歌咏爱情,歌咏艺术、人生、命运,歌咏自然,但大抵歌其悲哀的一面。在内容上,偏重个人内在的感受和情绪。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这当然是消极的、落后的,这为当时的时代所不容。这也是李金发作为诗人的悲哀。 其三,形式之哀。如果说李金发的诗在内容上是消极的,那么在形式上却是激进的。由于深受西欧文学的影响,李金发的诗在形式上带有明显的欧化痕迹,象征主义观念联络的奇特性和意象组合的非逻辑性造成的解读困难,使他的创作脱离了民族审美心理和欣赏习惯,这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用兼容并蓄的眼光去审视艺术发展的历史,就能真正发现李金发和象征派诗人在新诗的探索实践中对诗歌艺术的独特贡献,以及创造诗美的经验与教益,从中为我国诗歌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艺术的个性与独创性 李金发诗歌创作是以个人唯心主义和象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他的象征主义诗歌有其鲜明的个性,他所努力追求的是一种东西方诗意的融合,即西方诗歌的活泼自由与东方诗歌含蓄蕴藉的结合。尽管这种尝试和探索不很成功,但影响却相当深远。象征派诗歌追求深层表现,追求含蓄蕴藉的审美效应,试图从意象的创造和联结来完成诗歌的使命,恢复诗歌的“本我”形象。因而,这种诗完全不同于当时“明白如话”的白话诗,也不同于稍后标语口号式的“政治宣传诗”和“说理诗”。 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个性与独创性,首先体现在诗歌意象的象征性上。例如《上帝》一诗中:“上帝在胸膛里,/如四周之黑影,/不声响的指示,/遂屈我们两膝”,通过象征的手法,暗示了精神世界的神奇力量,这种神奇力量可以有多种解释。李金发认为,象征之于诗“犹人身之需要血液”[8]。诗歌评论家认为,象征派诗歌“内涵表现了无限伸张的弹性”( 参见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孙玉石先生在《中国现代诗导读》中多次谈到象征诗的“弹性”,如“审美的弹性”(66) 页)、“表达感情的弹性”(70页)、“抒情的弹性”(124页)、“陈述的弹性”(131页)、“富于弹性的感情内涵”等),也就是说象征的含义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来认识象征派诗的朦胧晦涩及多元释义应该是可行的。 其次,其艺术个性与独创性表现在诗歌情调的暗示性上。诗歌情调的暗示性是象征派的独特艺术追求。暗示性是造成诗义多层性与含蓄性的一种重要因素,它往往借助于梦幻来表现,在技术上通常运用比喻来完成,正如朱自清所说:“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9]象征派代表人物马拉美认为,只有梦幻能达到不属于人世的美,只有梦是未被玷污的地方,梦境是诗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李金发在《少女的情爱》中写少女梦的纯洁与安宁:“病倒的女孩,/梦见天使吻伊的额;/穷追的野兔,/深藏在稻草窝里”。梦境的描写,扩大了诗歌意境的表现领域。李金发大胆而特异的比喻跳出了俗套与框架,用看上去并不相关的事物构成陌生新鲜的意象,如“我的灵魂是荒野的钟声”,“我的哀戚惟游蜂能深印着”,“呵,多情之黑夜,! 你始终掩着面蹑步而来,! 为拍兔之野狮”等,词语违背了规定用法,令人在这陌生的字码关联中竭力去感悟并破译意象暗含的意味,从而赋予诗歌更大的想像空间,由此产生审美的愉悦。 再次,语言的怪异、新颖、陌生化。大量外语词汇入诗或作题目,语言有明显的异国情调,这是李金发诗歌的又一特点。如大量运用通感,语意常常故意省略,使意象产生跳跃,读之如解题猜谜,这对传统的审美习惯是一种破坏和反叛,在诗歌语言形式的多样化方面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如:“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车轮的闹声,/撕碎一切沉寂”等,活泼奇特,使人眼界开阔,领悟了诗歌的精深与微妙,丰富了审美体验。我们认为,李金发对白话诗语言积极探索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的诗对当时白话新诗几成流弊的浅露直白也是一种反动。他厌倦诗歌的原有形式,又无力改变白话新诗浅入浅出、缺乏想像力、缺乏韵味和内涵的现实,只有独树一帜,标新立异。
(二)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在新诗艺术上的影响 可以说,李金发在新诗探索的实践上是具有超前意义的。尽管他的诗在艺术上略显粗糙,调子也过于低沉,有时未免流于神秘,然而对新诗向着艺术和审美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创作技巧与手法及诗的音乐性的完成、诗情的深层次挖掘方面,都具有较深远的影响,而且也透露出了现代诗歌发展的动向。 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中自由的创作精神和个人色彩,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独力追求,一些年轻诗人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侯汝华、胡也频、林英强、蓬子等,受李金发影响,都曾投身象征主义诗歌的创作。正是李金发的倡导和一些年轻人的实践,才使戴望舒在此基础上把象征诗推向蓬勃与发展,进而形成“现代派”并拥有一个诗人群,还有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人对西方现代诗歌融汇后的创作等,他们的创作基本上完成了东西方象征诗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使新诗具有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象征派诗歌像流星雨,在中国新诗坛留下了暂短而耀眼的光辉。 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还对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七八十年代中国朦胧派诗歌异军突起,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和中国早期象征派诗歌有着血脉相连的密切关系的。它们无论是外在形式上还是技巧手法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只是朦胧诗走得更远。两者在20世纪的两端遥相呼应,决非偶然,从文化意义和审美取向来看,有着历史的必然。 一个诗人,站在时代的经纬点上,可以为时代吹响战斗的号角,也可以为自己吟唱心灵的哀歌,这是不同的文化选择,这种选择应该是自由的。号角也罢,哀歌也罢,凡具艺术审美价值的,都应承认是“好诗”,并且“好诗”所创造的美感应该是超越时空的,其艺术生命力也是长久的。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在当时既没有“载道”,又没有“言志”,只是抒发了个人的情感,但七八十年后,我们读来并没有时代隔阂感,它所具有的审美情感依然浓郁。所以,时代选择诗人和诗,诗人和诗未必选择时代。 诗是源自灵魂的自由歌唱,是感情与艺术的载体,在重负着艺术与审美价值的同时,不可能过多地背负其他的一些不属于它自身的东西,诗歌与政治的疏离,可以使读者对诗歌的认识和评论的目光从社会功利转向诗歌本身。我认为,文学应该有宽松的发展环境,而我们也不应该只听到一种歌唱。文学的真正繁荣,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在文学殿堂里,象征主义诗歌应该有她自己的一席地位。 [参考文献] [1]刘心古,等.文学原理教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96. [2]李金发.艺术之本原与其命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105. [3]魏洪丘,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概观[M].四川:成都出版社,1990.191. [4]陈厚诚.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139-140. [5]李金发.女性美[A].孙玉石.象征派诗选[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1. [6]李金发.为幸福而歌•弁言[A].李金发.李金发诗集[Z].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439. [7]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A].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四卷)[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0.369 [8]李金发.序林英强《凄凉的街》[A].吴中杰.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11. [9]朱自清.新诗的进步[A].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二卷)[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320. 作者简介: 杨桦,河南淮阳人,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曾入伍,从事军事新闻报道。现供职于焦作某机关。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星星诗刊》《中国诗歌》《中国诗人》《绿风诗刊》《青年文摘》《河南作家》《河南诗人》等数十家报刊。
683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