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百书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聊斋口技的创作特点是什么 › 经典百书 |
经典百书
|
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清代,产生了两部带总结性的作品——一部是《红楼梦》,一部就是《聊斋志异》。《红楼梦》是长篇小说的总结,《聊斋志异》则是短篇小说的总结。这两部作品在思想艺术上都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红楼梦》的总结地位是毫无疑义地确立了,《聊斋志异》的总结地位虽也有人论及,但至今认识仍不充分。 唐宋以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发展分为文言与白话两途。但两条路并不是互不相干、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文言短篇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两个发展系统,共同构成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艺术传统。历经明清时期的发展,两个系统、两条道路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向愈加显著。除了语言工具一通俗一典奥的明显差异,在思想旨趣、艺术手法、艺术风格等方面,虽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这一点,在像《聊斋志异》这样优秀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志怪与传奇
图:撒旦君 《聊斋志异》作为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首先是继承和总结了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经验。 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由于受古代相当驳杂的小说观念的影响,无论从内容或形式看,范围都是十分广泛的。我们通常所称的笔记小说,内容广博,篇幅短小,形式活泼,手法自由,是其基本特色。但在文言短篇小说中作为主体和正宗的,则是志怪和传奇。志怪和传奇,既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同时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体制。它们之间的差别,表现在题材和形式上,但又不仅仅表现在题材和形式上。志怪以写神鬼妖异之事为主要内容,传奇虽也传写奇事,甚至在某些作品中(尤其是唐代的早期传奇)也有涉及神鬼精怪的,但却以反映社会人事为主。志怪一般篇幅比较短小,常见的多是一二百字、二三百字,有人物(神鬼乃是幻化的人物),但多数缺少性格, 形象也缺乏社会内涵;情节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艺术空间来容纳丰富的场面和细节描写。传奇则一般敷演为上千字或几千字的规模,情节完整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而且有较丰富的社会内涵。更重要的差别还在于:由于作者创作指导思想的不同而产生的作品性质的不同。 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与产生于同一时期的志人小说一样,都没有脱离史的性质。尽管作品所记的神鬼怪异之事本属子虚乌有,但作者却把它们当作跟社会人事一样真实存在的事情来记录,谈不上艺术加工和艺术概括。早期志怪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干宝,在他的《搜神记序》中,就特别强调志怪小说的史的性质,并明确申言《搜神记》的写作目的在“发明神道之不诬”。“不诬”就是真实存在的。这样的认识,不单单反映出作者有神鬼迷信的思想,更重要的还说明了,指导作家写作的是史家的意识,而不是小说家的意识。他所追求的不是通过艺术的想象和虚构来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而是力求“使事禾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搜神记序》)。他把志怪小说当作“信史”来写,虽然明知做不到,却还是要那样去追求。尽管当今的小说史研究家们都把《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当作中国早期小说的代表作家来论述,但他本人在写作的当时却是把自己当做史家来看待和要求的。在他的心目中,写作《搜神记》和撰史,同是忠实的记录,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到唐代,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传奇作者的小说家意识绝对地压倒了史家的意识,这样唐人传奇就与史分手而成为真正成熟的小说。这一点明代的胡应麟看得很清楚,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卷三十七《二酉缓遗》下)虽然他并不肯定“幻设语”,但却十分敏锐并且正确地指出了这是唐人传奇不同于以前志怪小说的显著特征。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聊斋志异》既继承和总结了志怪小说的传统和经验,又继承和总结了传奇小说的传统和经验,并且加以融合、提高、发展,在题材、体制、手法、风格诸方面,都使文言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聊斋志异》的创作特色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十分精辟地概括了《聊斋志异》对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继承和总结。当然,这句话还不能仅仅简单地理解为蒲松龄是运用了唐人传奇的体制和手法(一种成熟的小说艺术形式和手法)来写志怪小说。更重要的,是指他用小说家的创作精神来改变了传统志怪小说的面貌。他一方面广泛搜集民间传说,而所关注的又不仅是奇诡怪异的故事本身,还有故事中所凝聚的人民的思想感情;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又不是简单的记录和整理,而是通过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和虚构,将自己的生活体验、爱憎感情和对生活的评价,都熔铸到花妖狐魅的艺术形象中去。清代评论家冯镇峦正确地指出:蒲松龄是“有意作文,非徒纪事”(《读聊斋杂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蒲松龄有着非常自觉的小说家的创作意识。这一点,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讲得非常清楚:“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卜”在他的心目中,《聊斋志异》的写作跟屈原创作忧愤深广的《离骚》和李贺创作牛鬼蛇神似的诗歌没有什么不同。他追求的不再是写出“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的“信史”,而是寄托他得自生活并与人民的爱憎息息相通的满腔的孤愤。因此,《聊斋志异》虽然多数描写的是花妖狐魅,充满奇思异想,却有着非常深切的现实内容;它所提出的多是现实生活中重大的社会问题,触及到多方面复杂的社会矛盾。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位热切地关注现实的作家,以幻想的形式写出的一部社会问题小说。《聊斋志异》在奇幻的艺术想象中处处透出强烈的现实感和浓郁的人间气息。不仅那些篇幅较长典型的短篇小说如《促织》、《席方平》、《红玉》、《青凤》、《嬰宁》、《叶生》等是如此,即使一些篇幅短小形式上类似六朝志怪的作品,其旨意和精神气韵也跟传统的志怪小说迥不相同。奇异世界映照出现实人生,花妖狐魅散发出人间气息,这才是“传奇法”的精神实质所在。这就是《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一二百字的短篇,读起来却极富于隽永的思想意趣的根本原因。 不妨这样说,《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之作,不论篇幅长短,都同时兼具志怪和传奇两种特色,既不完全同于六朝的志怪,又不完全同于唐人的传奇,是两种体制和创作传统的融合和总结。《聊斋志异》在总体艺术风格上,既有六朝志怪的简括精炼,又兼具唐人传奇的委曲丰妍。
提笔作伏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一直受到史学传统和史传文学的影响。《聊斋志异》对史传文学的继承和总结,远绍“史”“汉”而中承唐人传奇。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聊斋志异》主要取法于历史散文中的纪传体,一般以写一个人物为主,为主人公立传,围绕着主要人物来展开情节,结构全篇。且多数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如《青凤》、《红玉》、《小翠》、《席方平》、《连城》等。小说创作而取法乎史传,唐人传奇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的许多名篇采用的就是纪传体,而且在题目上还明确地标出“传”字,如《任氏传》、《柳氏传》、《莺莺传》、《柳毅传》、《霍小玉传》等。《聊斋志异》吸收了唐人传奇的艺术经验而又有所发展和提高。 在《聊斋志异》中,史传乃其形,而神气却完全是小说的。例如,按纪传体的写法,开头一般介绍主要人物,诸如姓名、出身、里籍、性格特点等。如果变成一种僵死的程式,则千篇一律,殊无意趣。《聊斋志异》开头介绍人物却大有讲究,介绍什么,不介绍什么,如何介绍,总是立足于全篇的总体艺术构思,或跟人物性格的刻画,或跟情节的发展,或跟主题思想的揭示,都密切相关。如《王桂庵》篇这样介绍主人公:“王樨,字桂庵,大名世家子。” 这是典型的人物传记的写法,粗看似无出奇之处;但“大名世家子”五字,却非贸然落笔,而是在精心提炼主题、精心谋篇布局的基础上写出的,成了全篇艺术描写的纲领。后文写王桂庵的性格,写由这种性格引起的与芸娘的富于戏剧性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构成的波澜起伏、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都跟开头这五个字有关。这种立足于整体艺术构思的开头,体现了与写历史有别的小说创作的神髓,是得之于史传文而又高出于史传文的。这样的开头,清代的聊斋评论家冯镇峦给了一个精当的概括叫:“提笔作伏”。
不可不读“异史氏曰”
《聊斋志异》在许多故事的后面都附有“异史氏曰”,这也是取法于史传文学而又有独特创造的。《史记》在人物传记之后常缀以 “太史公曰”,对所写人物或事件发表评论。这种形式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汉书》、《后汉书》称“赞”,《三国志》称“评”,刘知几在 《史通》中加以总结,称为“论赞”。唐人传奇中的一些作品,于结束处每有议论,但并未形成定例,像《霍小玉传》、《长恨歌传》这样的名篇就都没有;有的,内容也比较简单,位置不固定,形式也不统一。唐传奇中的“论赞”并不重要,还没有跟正文故事形成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更少画龙点睛或锦上添花之笔。 明代《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写过一部志怪小说集叫《禹鼎志》,原书已佚,序文却留了下来。“序云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何其让焉。作《禹鼎志》。”(《吴承恩诗文集》卷二)《禹鼎志》中的作品是否有“论赞”不得而知,但他自称“野史氏”却是自觉地以小说家的面貌出现,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所谓“野史氏”,表明了吴承恩在《禹鼎志》中是以完全不同于正史史家的立场和眼光去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无论蒲松龄是否读过吴承恩的《禹鼎志》,“异史氏”和“野史氏”一样,其取意都富于小说家的内涵则是毫无疑义的。而这一点,正好昭示了蒲松龄是以小说家的精神改造了传统的史家之笔的。 蒲松龄将传统史传文学中的“论赞”形式提高发展为一种既完备且隽永的古小说体例,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成为与正文故事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成为《聊斋志异》髙妙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异史氏曰”的写法多种多样,形式自由灵活,不拘一格,往往议论纵横,妙语成趣。短的寥寥数语,长的则可以多出正文文字一倍以上;有散体,也有骈体;内容或阐发题旨,或借題发挥,常常针对现实,抨击时弊,泼辣犀利,有如现代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要正确理解《聊斋志异》的思想和欣赏《聊斋志异》高妙的艺术,不可不读“异史氏曰”。
一书三四体
图:亮年 《聊斋志异》还融进了传统散文的手法和笔意,如结构的严谨, 布局的精妙,叙事的简净,语言的精炼,意境的优美等等,处处都透出中国古典散文的情韵风致。关于《聊斋志异》继承传统散文这一点,前人已曾指出,如邹強在《三借庐笔谈》中说:“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盖脱胎于诸子,非仅抗手于左史龙门也。”(转引自《小说旧闻钞》)赵起杲在《青柯亭刻聊斋志异例言》中也说:“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乌、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蒲松龄借鉴吸收古典散文,不是生硬的模仿,而是化为小说,得其精神气韵,而不露痕迹,使人易读易晓。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部分作品,本身就是散文。多数为纪实, 写作者的亲历亲见亲闻,一般篇幅不长,像是对实生活的素描和速写,但下笔时也作过精心的提炼和构想。如写民间杂技的《偷桃》,写山中奇景的《山市》,记自然灾异的《地籐》,述人物异行的《农妇》等。 明代的胡应麟曾将古代的文言小说分为六类,即志怪、传奇、 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几乎囊括了传统所谓笔记小说的全部内容。《聊斋志异》以志怪传奇两类为主,除了纯议论的“丛谈”、“辨订”外,其余都包括在内了。《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昀批评《聊斋志异》中又有“小说类”(他实际指的是志怪)又有“传记类”(他实际指的是传奇),“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纪昀其实还说少了,《聊斋志异》是一书而兼三体、四体。文备众体,兼收并蓄,正表现了蒲松龄打破陈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带总结性的艺术创造。纪昀所不解处,正是他不及蒲松龄处。冯镇峦就委婉地向他提出 了批评,说:“《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还说纪昀的《阅微草掌》四种虽无此弊,比之《聊斋志异》却是“生趣不逮”。话虽含蓄,却真是说到点子上了。
师承白话
除此之外,《聊斋志异》还继承和总结了宋元以来白话小说的艺术经验。比之叙事委曲生动的唐人传奇,《聊斋志异》更加着意于对情节的提炼和组织,故事情节更丰富、更曲折,更富于波澜起伏的艺术特色。优秀之作处处有伏笔,有悬念,令人疑窦丛生,却又猜想不透,常常大起大落,出人意外,而掩卷回想,却又无不在人意中。这显然是从源于说书艺术的话本小说中吸取了营养。一般的文言小说是难于讲说的,除语言的因素外,故事性不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聊斋志异》却很容易还原为口头文学,以评书、子弟书、鼓词等说唱文学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与此当不无关系。 用文言写小说,写人物对话是比较难的。《聊斋志异》中对话得到广泛运用,吸收口语成分,不仅富于个性特色,且声口语气,逼真传神,成为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此外,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得更加丰富、细腻,也是继承和总结白话短篇小说艺术经验的重要成果。
图:蓝雯轩 总上所论,《聊斋志异》不仅继承和总结了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经验,还继承和总结了史传文学、古典散文和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经验,并加以融合、发展、提高,创造出了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最适宜于表现花妖狐魅幻想题材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使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艺术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聊斋志异》名副其实是一部集大成的带总绪性的作品,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 来你好源 |广州大学图书馆 微信编辑 | 徐晓盈
|
【本文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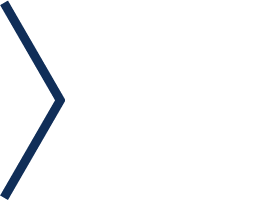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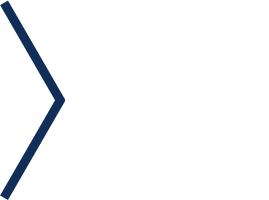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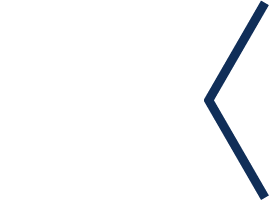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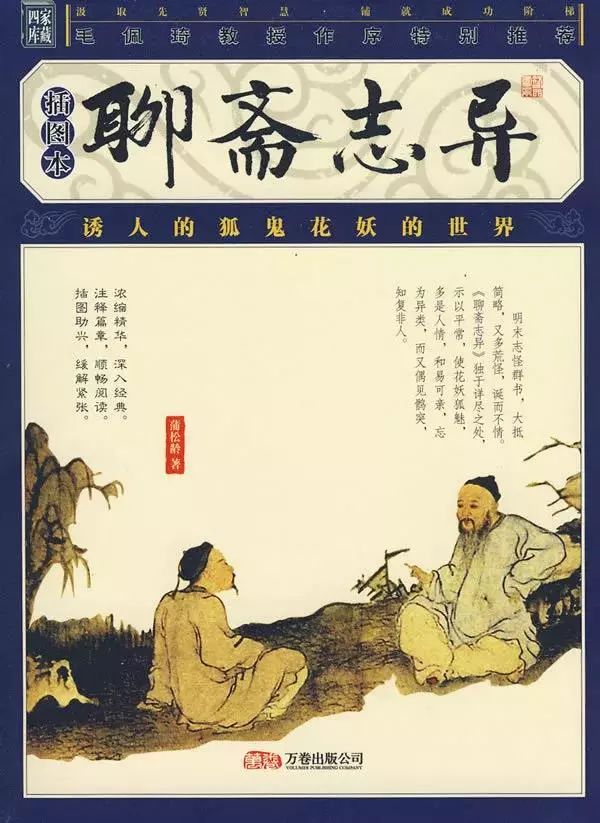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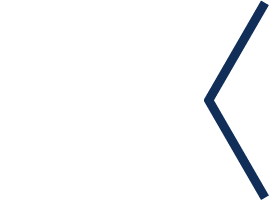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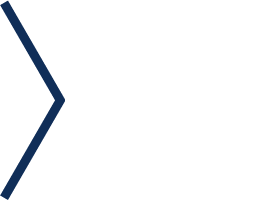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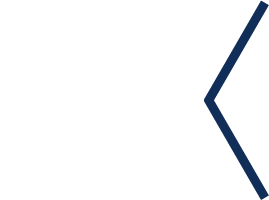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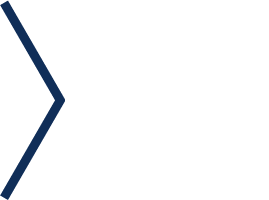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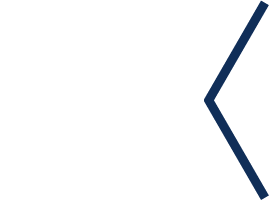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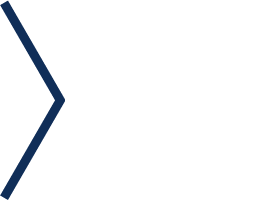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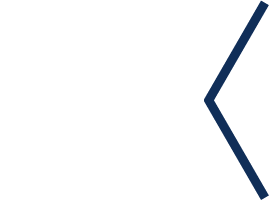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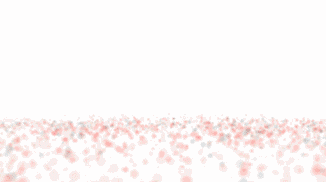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