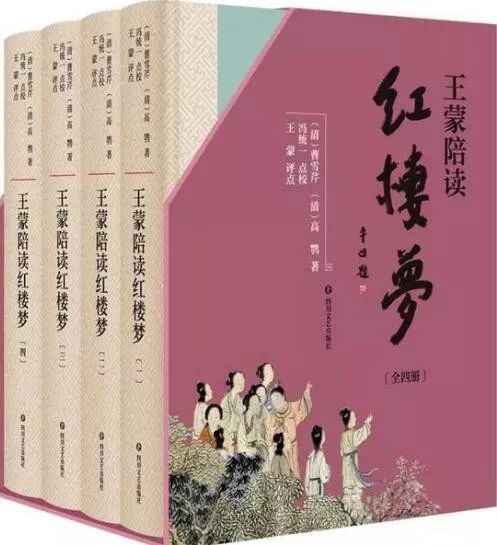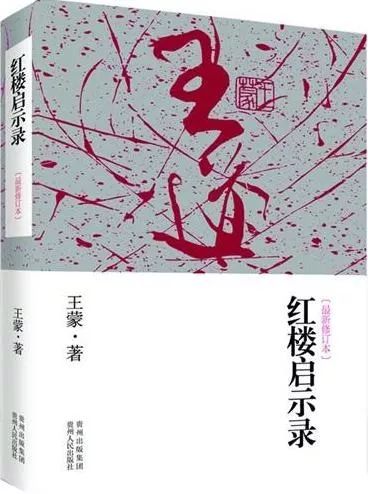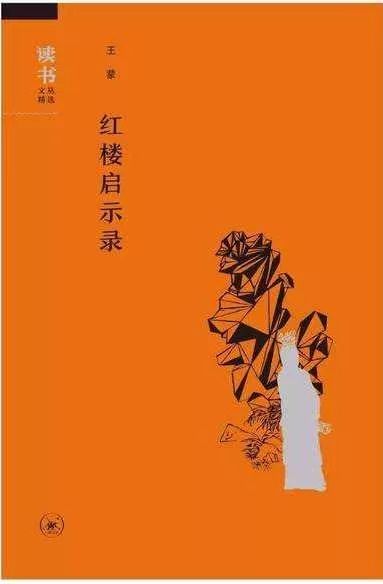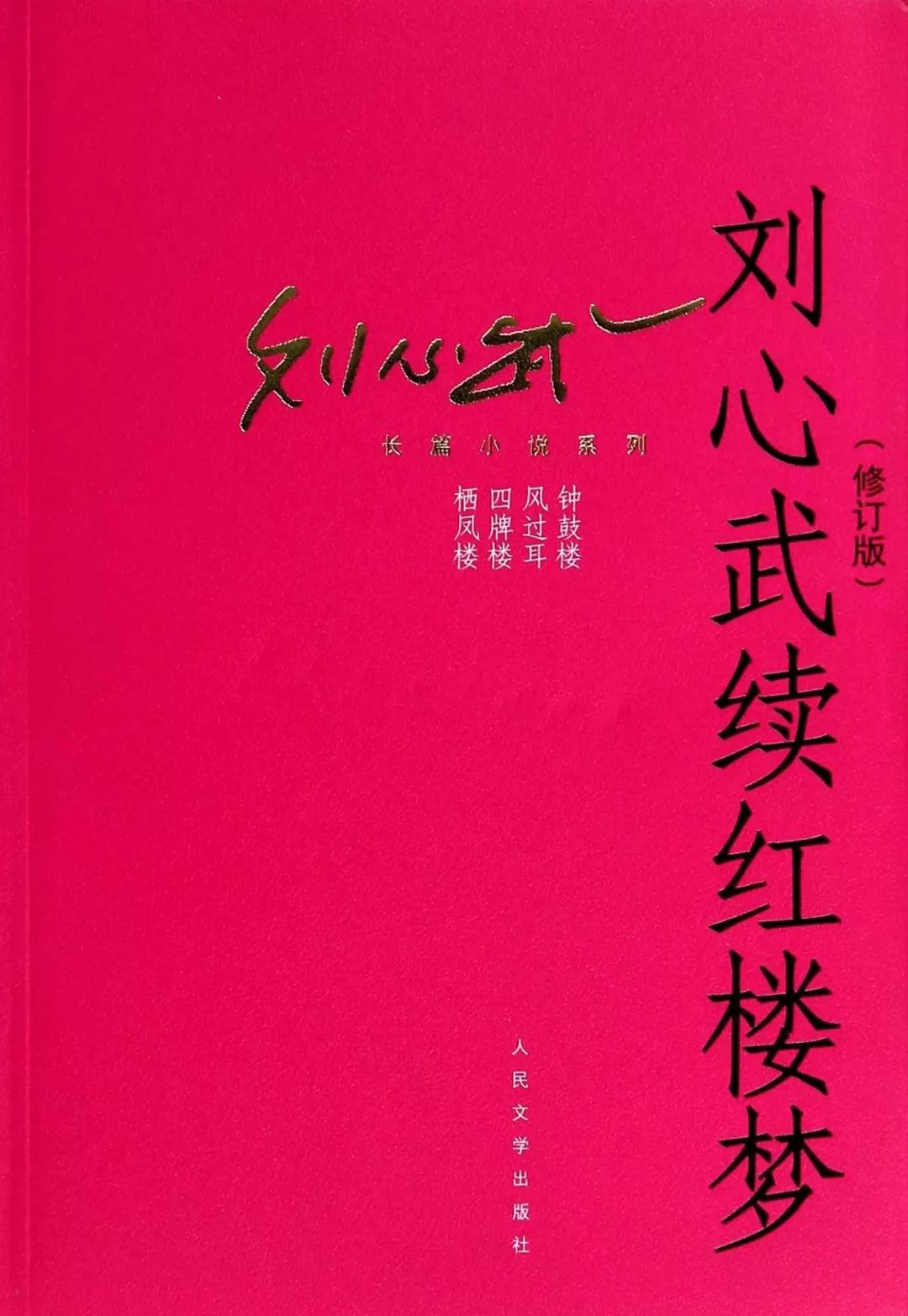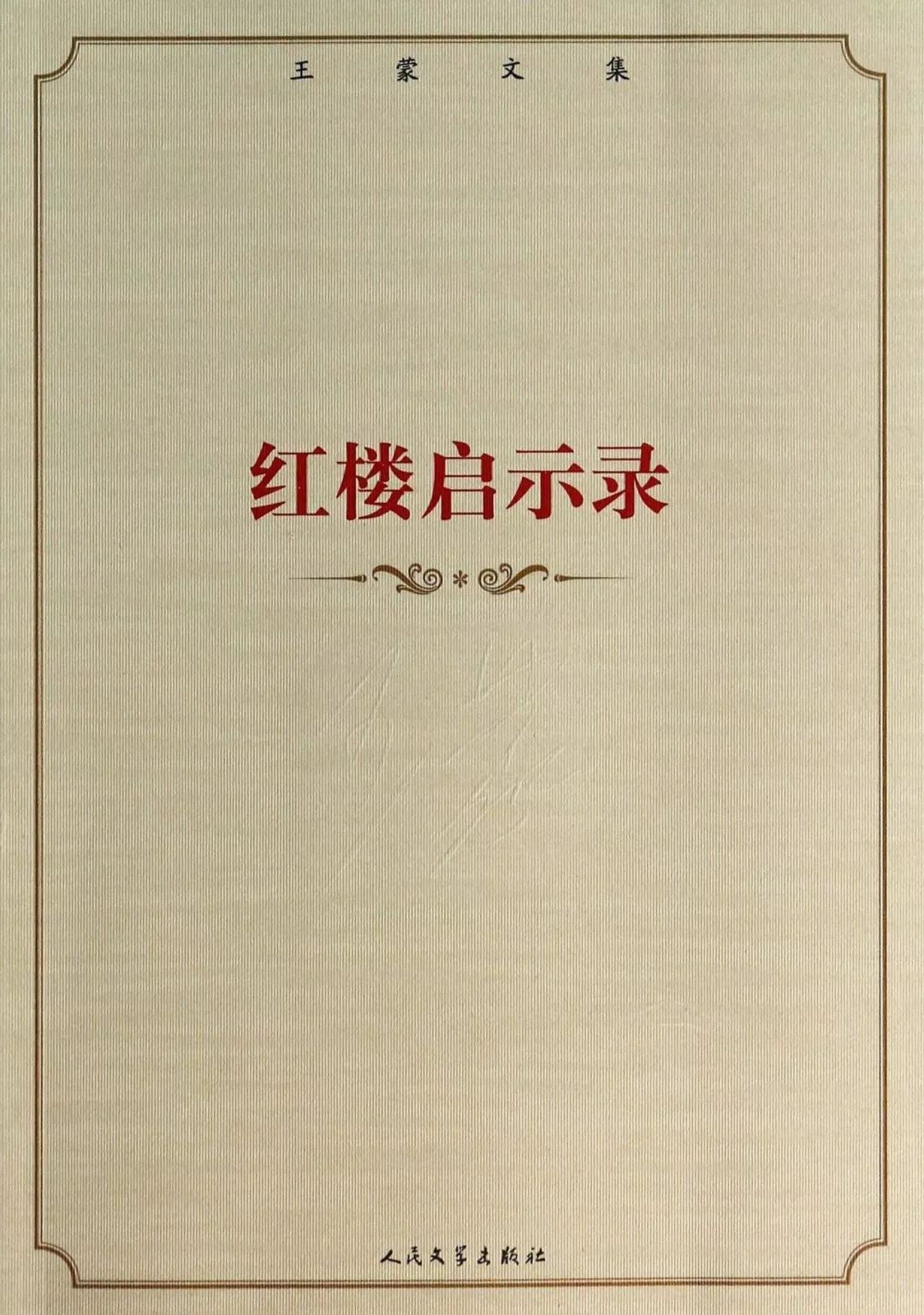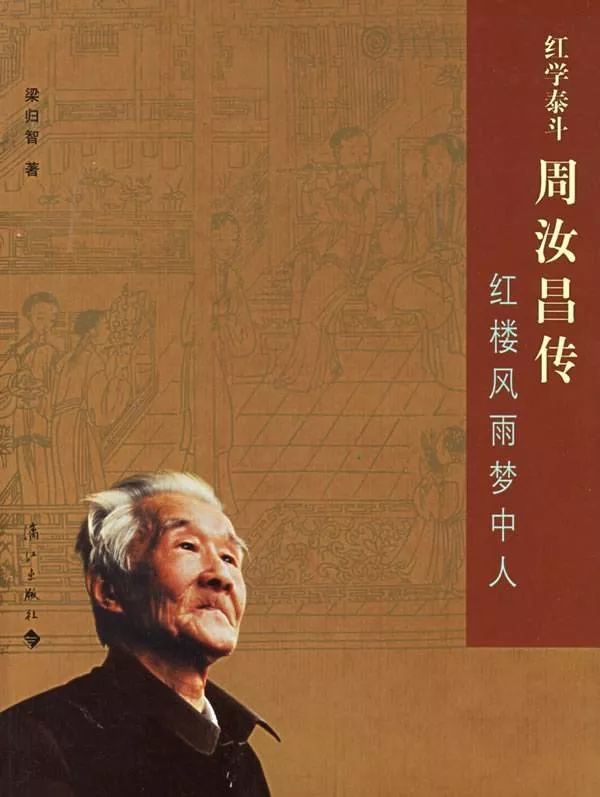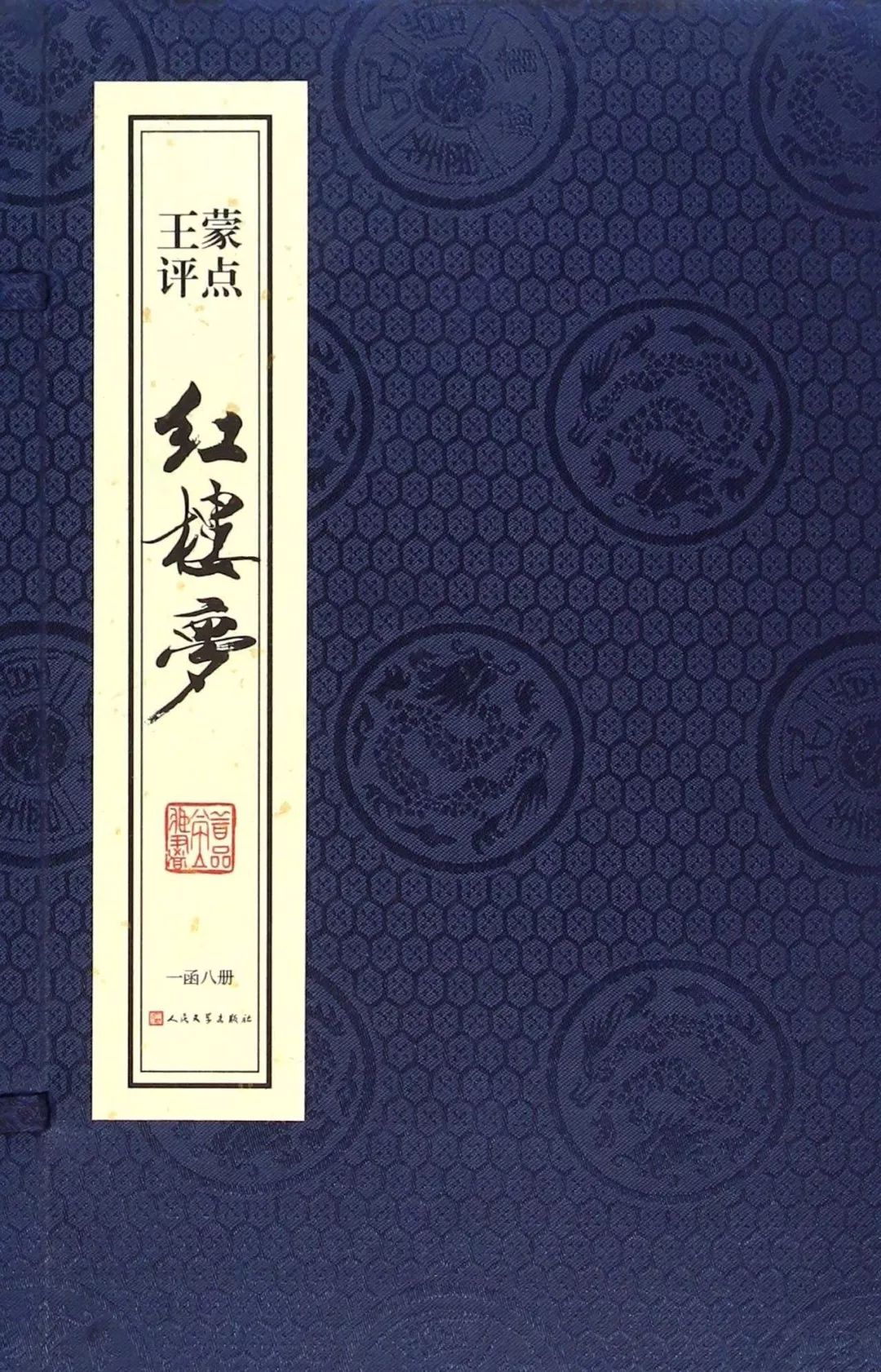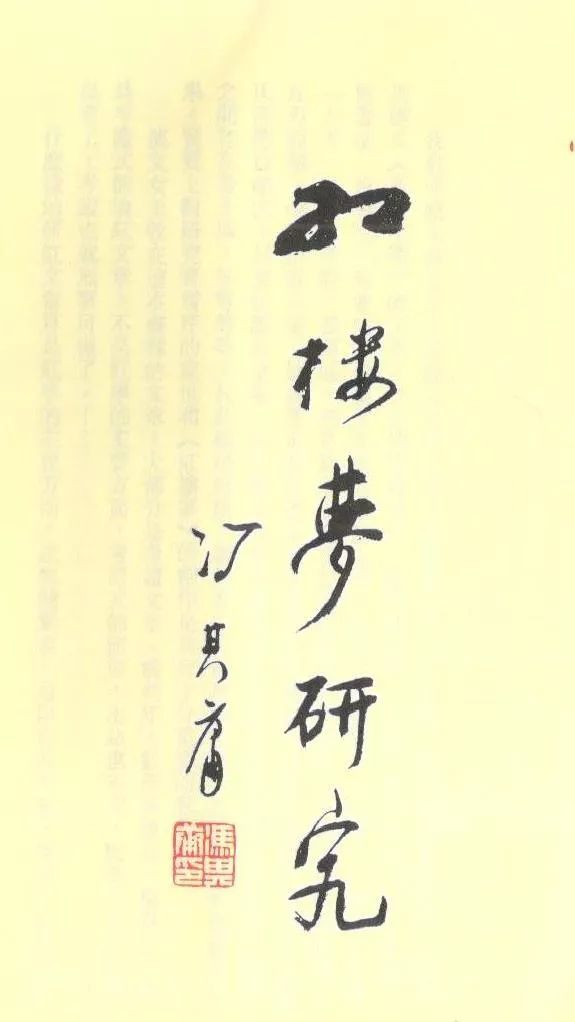高淮生:王蒙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十二)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红楼梦的线索是 › 高淮生:王蒙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十二) |
高淮生:王蒙先生与《红楼梦》研究(名家与红学系列之十二)
|
《红楼启示录》 平心而论,《红楼梦启示录》之所以耐读,主要因为尚未大量出现像多年后出版的《王蒙的红楼梦》(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的夸饰和炫耀。平心而论,如果称《红楼梦启示录》一书乃当代红学经典,应不为过誉。 2012年12月11日晚,收到中文系同事转交来的学术论文获奖证书,即《王蒙红学研究综论》一文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六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因授课任务较多,且忙于撰述“综论”稿,未能赴南京东南大学会议现场领奖。 当笔者将这个消息电话告知胡文彬先生时,胡先生向笔者道出该文之所以获奖的主要理由:王蒙是知名作家,自然最容易被关注!笔者竟恍然大悟起来。 记得2012年5月10日上午与胡文彬先生通话时,胡先生曾阐述过这样的道理:人成名了就有公信力,说同一个问题,人们看得兴趣不一样,没有公信力的人自然没人理会。王蒙的文章不论好坏,都低着头看。而公信力是大家认可的,有一定的成就,著作就被肯定。 胡先生接着告诫笔者:不要轻易乱写,要为自己建立公信力!如此说来,“综论”系列文章的写作最应谨慎,否则,何以建立自己的“学术公信力”呢?的确如胡先生所告诫的那样,笔者彼时写作过程始终葆有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绪。
《王蒙陪读红楼梦》 2011年9月7日至8日,笔者主动与胡文彬先生讨论应补进“综论”写作的人选事宜,王蒙成为应补进的人选,此前已经刊发了《蔡义江综论》《胡文彬综论》《张锦池综论》《吕启祥综论》《李希凡综论》等“综论”稿,彼时,《郭豫适综论》正待刊《河南教育学报学报》2011年第4期。值得一提的是,提供“综论”人选的师友愈来愈多,笔者亦愈来愈谨慎起来。 2013年4月17日上午9时,“《百年红学》创栏十周年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会议室开幕。李希凡先生、蔡义江先生、胡文彬先生、吕启祥先生、孙伟科教授、曹立波教授分别对《红学学案》做了客观中肯的评价。
《红学学案》 因涉及有关王蒙评论的细节,现将孙伟科教授对《红学学案》的评价节录如下: 刚才专家也说到了,从《百年红学》到《红学学案》,学术进步的历程是很艰难的,是一次飞跃。迈出这一步,应当是充分肯定的。…… 高淮生的《红学学案》引起了反响,他的书出来后,有很多人都看到了,有很多反馈声音,这些反馈声音也让我有一些思考。我想谈这样三点。第一点就是当代学人评价难写,这是大家公认的。淮生有不畏难的精神,我很向往。…… 第二点,切人点在哪里?淮生的写法,往往是从别人的分析找切人点。这好像是一种手法、写法吧,叫“借力打力”,这当然是一种选择。我感觉淮生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想通过争论中的分歧点找到一种引线,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他引到了哪里?引到了曲终奏雅。…… 第三点,淮生这样一种做法还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就是他坚持学术立场的写法。为什么这一点我要说一说呢?今天,红学当代人物,我们不写,别人都在写。别人用戏曲化的手法写,用漫画法的方法写,从揣摩人格的角度写,写的有些东西很不堪。当我们这边没有、拿不出一个有分量的东西的时候,其他的论调就要占领市场了。所以,在这时候,淮生从学术的角度来写,这样的写作应当支持,否则就被别的声音淹没了。
《百年红学》 以上发言节录自《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学报》编辑部编《创栏州十周年暨出版座谈会实录》一文,该文刊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3期。 4月18日下午14时53分,笔者乘坐G39次车返回徐州,15时40左右抵达徐州东站。上午曾发给孙伟科教授一个感谢的短信,即感谢他在座谈会上的很有道理、也很有想法的发言,尤其关于《红学学案》写法的评议(譬如“借力打力”“曲终奏雅”之类),笔者至今仍津津乐道。 彼时孙伟科教授正在授课,课后已是中午时分,即发给笔者短信道:“你为当代学人正形象,大家都得感谢你才对。一上午在上课,迟复抱歉。”(12:20:36)当G39次车抵达徐州东站时,又收到孙伟科教授发来的短信,他认为《红学学案》将王蒙列入足见“你的判断力”。
王蒙先生 遗憾的是,红学界不少的人将王蒙论红看得不是学术,可以说根本不懂文学。所以,“赞你一个!”由此显见,《学案》是否入选王蒙先生,从根本上说,至少关涉到是否真正懂文学的问题。且不说这种意见是否周延,彼时的笔者竟欣然自得起来! 其实,笔者的欣然自得早已显露于《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王蒙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一》(2万6千字)一文结稿之际,不仅主标题“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拟得很得意,“内容摘要”同样拟得很得意。现将该文“内容摘要”抄录如下: 王蒙的《红楼梦》呈现出个性鲜明的特征: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生活经验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思想观念与笔调文情汪洋恣肆。他敢于立说,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他的《红楼梦》研究能够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理予以“概念化”表述,并在体悟、阐释、批评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红学研究的“系统”。 2万6千字的文章,概括于141字的“内容摘要”之中,实收执简御繁之效。 再如《红学学案》出版之前,“前言”第一稿达9千余字,出版时则9百余字,真可谓“要言不烦”了,这也是笔者很得意之处。
《红楼启示录》 于是,“前言”第一稿以《换一种眼光看红学——“学案体”红学史撰述述略》为题刊发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1期。 且说不懂王蒙论红的价值是否意味着不懂文学这一问题,笔者以为,仁智之见而已。记得2011年9月25日蔡义江先生致笔者的信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些会讲、会写的名人,谈红楼,好说假话、大话、势利话,其实与真正的研究、科学的真理并无多大关系。”以上这段话真可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王蒙既属于“会讲、会写的名人”,又喜好“谈红楼”,至于是否“好说假话、大话、势利话”则不易遽然定论。试问:《红楼梦启示录》《王蒙活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王蒙评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王蒙的红楼梦》等著述中果真毫无蔡义江先生所指斥的情形吗?
《王蒙活说红楼梦》 笔者以为,这种情形显然是存在的,甚至是愈演愈烈的。“自嗨式”评红已然“娱乐化”(“自娱”或“娱人”)了,显然不能归属于“批评派红学”了。 当然,如果你并不认同归属于“批评派红学”的《红楼梦》批评应该是“学问化”的而不是“娱乐化”的这一看法,那么,你也就全然不会理睬《红楼梦》批评的“边界”或“门槛”之说。王蒙曾提出风靡一时的“作家学者化”之说,他的《红楼梦》批评显然是有“学问化”倾向的,尤其《红楼梦启示录》体现得很明显。 王蒙曾在《把文学评论的文体解放一下》一文中说:“不要一写评论文章就摆出那么一副规范化的架式。评而论之,大而化之,褒之贬之,真实之倾向之固然可以是评论,思而念之,悲而叹之,谐而谑之,联而想之,或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或别出心裁,别有高见,又何尝不是评论?”(《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不奴隶,毋宁死?——王蒙谈红说事》 王蒙有一种热望,即把《红楼梦》批评看作如他的小说创作一样——“激情的燃烧”。有一位评论者发表过一篇题为《批评是一种燃烧:王蒙的文学批评论纲》(王文初《批评是一种燃烧:王蒙的文学批评论纲》,《孝感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的文章,直接将“批评就是燃烧”作为王蒙文艺批评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格调来认识(这当然包括王蒙论红)。 的确,王蒙毫无顾忌地踏着“燃烧”的飞火轮恣意地飞翔在《红楼梦》批评的天空中,引来相当可观的观赏者、追随者。 当然,王蒙的“燃烧式”《红楼梦》批评的确以其特有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们阅读和评论《红楼梦》的兴趣。他的《王蒙评点》出版后曾引起冯其庸的大声呼吁:“快读《红楼梦》王蒙评!”(笔者按:冯其庸专门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推介文章《快读王蒙评》,刊于《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四辑。) 遗憾的是,物极必反,燃烧自我者也最容易走向“自焚”——“学问化”《红楼梦》批评公信力的自损!笔者以为,就红学学科建构而已,其负面影响不容低估。严格意义上说,王蒙的“燃烧式”论红与刘心武的“揭秘式”论红最终在“消解红学”(“解构红学”一词是否更准确呢?)意义上殊途同归了。真可谓:成于“燃烧”!败于“燃烧”!
《红楼启示录》 2015年12月5日下午5时,笔者乘车来到徐州南郊郡岭庄园酒店,拜访南京大学赵宪章教授,他应邀参加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文艺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会议《“全媒体时代下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高端论坛》。 笔者与赵宪章教授交流期间,谈及南京大学文学院以文献学取胜的学术特色,赵教授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文献学是学术评论的基础工作,是工匠可为的工作,他对文学研究中的考证很不以为然。 笔者则谈了自己的看法:考证是不可或缺的!譬如《红楼梦》的版本差别很大,黛玉还泪,是说她要报恩,后四十回却是焚稿,是以怨报德,意思完全变了。 接着,赵宪章教授很有兴趣地问及刘心武谈《红楼梦》该如何看?笔者则将王蒙谈《红楼梦》与刘心武比较着谈了一些看法。赵教授说自己并不熟悉《红楼梦》研究,但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红楼梦》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红楼梦》的“情”,另一点是《红楼梦》微妙的人际关系描写。
《红楼启示录》 显然,赵宪章教授并不真正了解刘心武“揭秘式”论红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并不真正清楚王蒙论红与刘心武“揭秘”的异同得失。彼时,笔者略有些怅然之意。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每每与人谈及正在做的课题(“红学学案”)或者受邀做《红楼梦》讲座之时,往往会被问及这样的问题:“你对刘心武谈《红楼梦》该如何看?” 笔者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往往因人而异,如果提问者是学界中人,便每每将王蒙谈《红楼梦》与刘心武比较着谈一些看法,希望给提问者一个明晰的认识。 笔者曾不无感慨道:刘心武“揭秘秦可卿”这一话题可以休矣! 2011年2月18日,笔者撰写了一篇题为《红学家们为什么对“红学家”称号避之如瘟神》的短文,其中写道:
《讲说红楼梦》 那么,为什么明明在“红学”这一学术领域已经学有专长而成一家之言,甚至红学著作等身,却又避称“红学家”如避瘟神,竟要一味地撇清呢? 这一撇清自己的奇观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似乎首先就与古时文士进退得所的自保心理的遗传很有关系。 因为,“红学”虽然不过一学术领域(既然大家已经认可),它也是个是非场、争斗场。如周汝昌在《红楼夺目红》中所言:“‘红学’是个挨‘批’的对象,欲发一言,愿献一愚,皆须瞻前顾后,生怕哪句话就犯了‘错误’。” 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红学领域的争议或论争最多,而且,也似永远说不完、争不清,它始终影响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思想、历史、文化、学术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譬如刘心武《揭秘秦可卿》闹出多大的动静来,几乎掀起了全国范围所谓的“民间红学”与“主流红学”的世纪大战,难道还不热闹吗? 姑且不说刘心武于“百家讲坛”讲论的内容是真学术还是伪学术,他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力真就有一股子“殉道”精神哩。你瞧!《刘心武续红楼梦》又闪亮出版,赚取版税姑且不论,其敢为天下先的这一做法自然不能不令某些国人神经为之大振。 刘心武这般勇力哪里来?首先来自红学“泰斗”周汝昌的提携,周汝昌对刘心武的百般厚爱常常使得这位“伤痕作家”百感交集:“我的研究,得到‘红学’前辈大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点。我们完全是君子之交……周先生看到我一些文章,会主动给我写信……每当展读,我都感动莫名。”(《红楼解梦》) 他口口声声称“我的‘秦学’研究”怎样怎样,“我创建了秦学分支”又如何如何,不过是要标榜自己是一位横空出世的、继周汝昌大师之后的“红学大家”。 他卯足了劲头要赚取一顶“红学家”的顶戴不说,而且还要以大众热门话题明星的身份力图为喜爱《红楼梦》的“小人物”们谋求“红学”这一公共共享文化空间的话语权。仿佛他就是“小人物”们的大救星似的,他的领袖群众的魅力尽显,不免激起了“小人物”们即刻行动起来口诛笔伐“大人物”们的热情,似有“革命家”风范。 另一个激励来自当代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作者王蒙同志。 王蒙同志因作家做得很有成就以后,一不留神写了一本小书《红楼启示录》,一个撑杆跳就摘下了“红学大家”的顶戴,这能不令新时期文学的开场人物、著名的“伤痕作家”艳羡不已嘛。 刘心武不仅艳羡,同时也还怀抱着莫名的亢奋,因为“红学大家”王蒙同志说了——“作家要学者化!”这无疑是金针度人,这位“伤痕作家”于是马上行动起来,搞起了多种经营:撰写研红论文、发表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三部曲)、“百家讲坛”揭秘秦可卿、续写《红楼梦》等等,精力过人,不亦乐乎! 功夫不负有心人,老天有眼,他不久便成为继王蒙同志之后的又一位作家型“红学大家”了。不同的只是,王蒙同志说了——“我不是‘红学家’,我不懂专门的‘红学’,如‘曹学’,‘版本学’等。然而我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红楼启示录》“前言”) 他只是把自己的《红楼梦》阅读心得记下来,再与他的“李商隐的诗歌”阅读心得合起来,作为自己“作家学者化”的“双飞翼”,即翅膀。这样,王蒙同志就可以自由地“任我往来”于写作和学术的广阔天地了。文学与学问兼通,即便很不情愿做一名当代之“通人”,也难矣!
《红楼启示录》 既然王蒙同样“撇清”自己不是“红学家”,那么,有人不把王蒙论红看作学术,也就大可不必为之义愤填膺了。 王蒙在《红楼启示录》“前言”只把他的论红文字称之为“札记式的感想”(《红楼梦》读后感)而已,这类情形在作家评红活动中很是普遍。 当然,这类情形并非作家专属,譬如周汝昌甚至认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实质也是较长的“读后感”,有别于真正的学术性研究著述。王国维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只是读了《红楼》的一些思绪感发,因而也就还不是“红学”的真谛。王国维只属“评”家,而不是“学”(“红学”)家。(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由此而言,王蒙不过是一位“评红家”,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红学家”。由此说来,他的“撇清”也不算出于进退得所的自保心理,自然谈不上“矫情”了。
《王蒙的红楼梦》 其实在这方面,李希凡先生倒是一直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自觉:“我不觉得成为‘红学’的一家,有什么光荣。我一向不承认自己是‘红学家’,因为我只把《红楼梦》看成伟大的文学杰作,对考证没兴趣。我是文艺评论的。”(李希凡先生2011年12月15日致笔者的信,这一年是他的本命年,已年届84岁高龄。)因为,“做个‘文学评论家’,又是很久以来的理想”(李希凡《李希凡自述:往事回眸》,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255页)。 笔者由此联想到1982年由周汝昌首先提出、应必诚最先回应的“什么是红学”的论争(刘梦溪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列为红学“第十四次论争”)是否真的有必要!如果那些“评红家”都葆有李希凡先生的一种清醒的自觉的话,红学“第十四次论争”也许只是周汝昌先生一个人的独角戏。
《红楼梦悟》 再譬如刘再复以“悟法”读《红楼梦》,几年内竟然写了“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他“只想感悟其中的一些真道理、真感情。”(《红楼梦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 “红楼四书”的确引起不少读者的阅读兴趣,不过,这“四书”一直未能在红学界被认真重视起来,记得孙伟科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红学与红楼美学——评刘再复“红楼四书”中的美学思想》(《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5辑)。 并且,又有作者称“刘再复开启了红学研究的新阶段”(王世德《刘再复开启了红学研究的新阶段——对《红楼四书》的审美感悟》《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该文同题再刊发于《东吴学术》2012年第2期),作者的这种提法并未得到红学界的积极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梦阳先生与刘再复先生是故交,他就曾建议笔者一定要好好写一写刘再复先生的《红楼四书》,并将刘再复先生的地址、电话告诉笔者,希望能够及时与他联系。
《共悟红楼》 张梦阳先生的热情令笔者感佩,当是也曾萌生过为刘再复先生立案的想法,不过一直没有联系刘再复先生。笔者2012年12月16日短信回复张梦阳先生:“说实话,我很感佩梦阳老先生这样支持刘再复先生,他若闻知,一定很是欣慰。因为,我在写作中也有耳闻,似乎刘先生被学界不少的先生们无意误读或有意误读,我不知何意?先生可以教我,以明晰我的思路。” 今天看来,“误读”虽有,“正读”亦在,问题是如果是将刘再复论红同样归之于“会讲、会写的名人”且喜好“谈红楼”之属,声誉自然会受到影响。彼时,尽管笔者《红学学案》原拟方案中列了刘再复先生,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法。 笔者于2011年9月7日至8日的日记中补记道:刘再复先生争议大,学界中大家多半不认同他近年来出版的几部“悟红”随笔,认为那不过是他身居海外的发泄之作,不是严格的红学著作。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尤其他曾为梁归智所写《红学泰斗周汝昌传》写过序文,而序文恭维失志,令人不屑。(笔者按:今天看来,刘再复先生的“悟”的确与周汝昌先生的“悟”有所不同:一个讲人生的体验;一个做索隐的学术。周汝昌先生的新索隐,以“悟”作为主要特征。胡文彬先生曾在2016年9月20日上午与笔者的通话中旗帜鲜明地说:我不赞同红学研究讲究“悟”,它直接继承的该是传统学术,譬如“朴学”。笔者对胡先生这一态度的赞同在于:“红学”之“学”并不基于“悟”字上!)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6月25日至6月27日召开的北京曹雪芹学会第一次年会即江西庐山会议期间,笔者与张梦阳先生同居一室,彼此相谈甚恰。数月后即2013年5月29日,张先生寄来他所精心创作的叙事抒情长诗《谒无名英雄家墓》题签本,该书由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2012年4月19日上午8时30分至10时30分,笔者为已退休的吉林省通化市政府副秘书长齐焕成先生的古体诗稿集《月下吟》撰写了一则序言,此乃受笔者任职的文法学院汤道路老师的请托勉力而为。
《王蒙评点红楼梦》 这篇短序大段文字谈及王蒙,彼时,《鉴赏与批评并举,体悟与活说贯通:王蒙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十一》一文尚在构思之中,现将这段文字节录如下: 当代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部长、《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作者王蒙同志曾将自己阅读《红楼梦》和李商隐诗歌的心得合起来出版了一本小书《双飞翼》,“翼”,即翅膀,即把《红楼梦》和李商隐诗歌作为自己“作家学者化”的两扇翅膀。 有了这样两扇翅膀,王蒙同志就可以自由地“任我往来”于写作和学术的广阔天地了。文学与学问兼通,即便很不情愿做一名当代之“通人”,也难矣! 他的“双飞翼小语”是一篇上佳的“王蒙式小品”,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心可以有。一翼是小说,一翼是诗歌。一翼是明清小说,一翼唐诗。一翼是《红楼梦》,一翼是李商隐的诗。我对这双飞翼情有独钟。 在出版了《红楼梦启示录》以后,谨把新写的谈‘红’与说‘李’的文章汇集为这本小册子。心有灵犀一点通。有吗?灵吗?通吗?请读者批评。一九九五年七月酷暑中”。“有吗?”“灵吗?”“通吗?” 依我看来,王蒙同志的话题本旨关键是在这一个“通”字上。他不无炫耀的“通”其实更侧重于“通人”之“通”,并不就是我所理解的生命之灵从容不迫地自由飞翔的本旨。 王蒙同志的“通”是有目的性的,而我则赋予“通”以自在性或本体性,即“通”是人之生命灵魂的自在或本体,无所谓目的。正如女娲炼石补天遗落的这块“通灵石头”一般,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地都是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下,无论你把它置于何处,它都是一块“通”了心性的“通灵石头”。不知齐先生以为如何? ………… “书山有路灵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这是我前些年读书阅世的心得,是的,我改造了人们最熟悉的这两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我最爱这“灵”字,有了“灵”,才会有“诗兴”、“诗意”、“诗情”,有了“灵”,抛开这“诗才”的自矜也罢!我不喜欢这“苦”字,也自然不喜欢所谓“苦中作乐”的自矜,因为,有了“灵”在场,心性即“通”——通畅、通变、通明、通达、通神,“苦”将何以自处?可谓:苦处休言苦,乐时只须乐!(《月下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12月) 王蒙在当今中国的文化大众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以王蒙为例说理更易于《月下吟》作者的接受吧!
《王蒙谈红说事》 2013年1月13日晚8时20分,笔者与新华出版社张琳琅编辑通话谈《红学学案》书稿的封面设计。张琳琅编辑毫不迟疑地说:封底所选印的文字部分应该首选王蒙的文字,再选周汝昌、李希凡的文字,因为他们在读者中的影响更大些。 笔者欣然同意了这种设计,《红学学案》书稿的封面设计文字出版时又增选了冯其庸的文字,均选录《红学学案》中的大标题文字。 值得一记的是,新华出版社张琳琅编辑是由笔者兼任本科生班主任的2000年级1班学生蔡燕同学帮助联系的。彼时,她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任《意林》编辑部编辑。此前,曾拜托张燕萍主编帮助联系河南郑州的出版社,曾拜托曹学会李明新秘书长帮助联系北京的出版社,曾拜托尉天骄教授帮助联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均未获得成功。 其中,《红学学案》书稿相关资料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审处呆了近三个月,仍无疾而终。一位朋友告诉笔者,可以电话询问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一家影响很大的出版社,出版过大量畅销的人文社科书籍。
冯其庸先生题写红楼梦研究 于是,笔者尝试联系了该出版社社长,社长表示为难,他告诉笔者:我们是出版过不少这类书籍,但并不挣钱啊! 2012年10月13日上午12时,学生蔡燕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已经联系的两家,都说学术著作出版不盈利,表示为难。 她的同学中又联系了新华出版社,需要收一万五的版面费,她咨询笔者要不要答应?笔者说可以答应!于是,她说把联系信息给了笔者。 2012年11月14日,笔者与张琳琅责编的通信,当时的恳切之情溢于言表: 张琳琅老师: 首先感谢你能抽出宝贵时间审看我发去资料! 我的这一红学学术史课题比较庞大,按照北京语言大学周思源教授的说法:可以做一辈子! 因为,百年红学发展史涌现了比较多的可以专人立案的学人,他们的学术精神、学术成就、学术个性、学术方法、学术典范等均有很广泛地学术启示意义,并非只限于红学领域。这一组学案,已经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百年红学”(全国社科优秀栏目)全部刊发,形成书稿则又做了详细修订。这一组文章已经在红学领域引起广泛关注,我期望在我有生之年,把这一学术史课题做出成绩,成为我个人学术生涯中标志性成果! 由于我忙于写作而不善于与出版社老师们交流,所以,我希望如果这一次我们的合作能够成功,可以长期合作。 我知道现在的出版社讲效益,我也会努力在书稿出版之后,拿出精力促进这部书的订购之事,这也是对我有益的事情。我的书有人看,我自己更有写作信心啊! 再次感谢张老师的辛勤劳动! 高淮生拜呈 2012年11月14日
作者在《红学学案》出版座谈会 2013年1月3日上午,《红学学案》书稿校对完成,快递寄给张琳琅责编。 《红学学案》的封面题签则由笔者的弟子、蔡燕的同班同学顾峥嵘(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毕业后回宜兴丁蜀镇从事紫砂陶艺创作)拜请著名书法家谢少丞先生所题,笔者十分地欣赏这一幅封面题签,遗憾的是没有存留原件。 2019年8月10日晚于槐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