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的核心不是科学,是人文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科幻片是怎样的 › 科幻的核心不是科学,是人文 |
科幻的核心不是科学,是人文
|
沃克:中国老牌科幻作家王晋康先生说,科幻的价值在于第101种关于未来的可能。我非常同意。此外我认为,科幻小说提供了一种讨论现实生活中关于政治和种族等敏感问题的安全方式。在科幻小说里,未来不同种族人之间通婚生子,不会引起任何恐慌,相较于传统文学,科幻小说具有一种天然的“安全优势”——我们可以在异域空间里讨论现实。 比如我最爱的《星际迷航》是20世纪60年代末越战之后推出的科幻作品。越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公民的精神状况非常糟糕。这时出现了《星际迷航》,用科幻的方式把人类的生存环境转移到外太空来讨论美国的社会现实,吸引了一大批对现实失望的人。连我保守的老父亲都对《星际迷航》目不转睛。面对现实,科幻小说有种更讨巧的进入方式。
《穿梭时间的女孩》 作者:瑞萨·沃克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年8月 16岁女孩凯特生活的时间线被一场谋杀改变,她必须穿越时空去修正时间线,才能拯救未来。
理查德·摩根 英国科幻小说家 保罗·J·麦考利 英国科幻小说家 新京报:1817年英国人玛丽·雪莱创作《弗兰肯斯坦》,这以后英国作为现代西方科幻小说的发源地,诞生了不少优秀作家,比如H.G.威尔斯和阿瑟·克拉克,然而一战后西方科幻创作重心转向了美国也是不争事实,直至今日美国都是西方科幻小说的中心。你们两位都来自英国,如何看待科幻小说在英美两国的迥异发展状况? 摩根:一战后,美国呈现出年轻的文化气象,相比之下英国文化显得落伍。1926年是美国现代科幻小说的起始年,因为出现了第一本科幻小说杂志《惊奇故事》。当时美国社会有种乐观的倾向,认为科技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科幻小说在美国很自然地迎来了黄金时代,那时的科幻小说用了很多科技成分包装故事主人公的冒险精神。英国科幻不是没有过反击——20世纪70年代发端英国的“新浪潮”运动提出要关注人的“内部空间”(Inner Space),然而美国科幻市场的魔力在于,它们可以迅速内化这种冲击,由此诞生了80年代的“赛博朋克”运动。事实上如今美国一直是中心,英国一直处在一个夹层中——一面受到传统英国文学的影响,一面受到美国科幻的冲击,有点疲惫。 麦考利:我认为英国和美国科幻的最大区别在于,英国科幻在科学层面更“弱”,会偏向更多政治性议题。美国在文化上很自由,科幻土壤更乐观,更有冲劲,更多去关注读者喜好,所以科幻小说更多的是色调明亮、结局美好的作品。但是英国人生活态度上更悲观,我们在写作上有更极端、更有冲突感的表达欲,会去直面社会的现有架构。英国科幻作家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不只是科技的元素。美国作家听读者的,读者想看什么就写什么。英国人更“拧巴”——我知道读者想看什么,但我就是不写,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好。 新京报:对于资深的科幻迷来说,也有两个人群——喜欢硬科幻或软科幻,你们如何看待西方科幻创作中这二者的分别? 摩根:“硬科幻”关注的是科幻的实体,但其实业界不太说“软科幻”,因为“软”对于科幻不是一个好词——这表示科幻小说里写科学的成分不够专业。其实我认为不应该简单两分。任何一本好的科幻小说都需要人文层面的论述。如果科幻小说里没有人性,读起来会很冷漠。如果你想写未来的科技世界,你是不可能不写人的,否则作品中就只有机器了。 麦考利:关于“软科幻”,我想说有些科幻作家其实是“反科学”的,他们把科学当做一种给人类的警示。比如《弗兰肯斯坦》中实际上说的是责任——你对你自己的创造物必须负责。怪物被创造出来后,他读了很多哲学书,然后去问科学家,我是谁?你让我的生活很痛苦,我也不会让你好过。很多软科幻作品中试图讲述,很多人怕科学又不懂科学,这造成一种灾难。人类现在的生活是稳定幸福的,但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异化,埋下了人类自我毁灭的种子。 科幻需要直面人类最难以启齿的问题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韩松,科幻作家,代表作《宇宙墓碑》《红色海洋》等。 新京报:你的新书《驱魔》描摹了一个被人工智能全面统治的世界。你如何看待当前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关注? 韩松:驱魔描写的是超级人工智能通过一个很具体的节点即医院,可以取代医生并进而接管整个人类世界。这里的基础是社会以人为本或者以生命为中心。当前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的未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在看到它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警告防备它的危险性。它有可能是人类在过去短短几十年里面掌握的能毁灭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些工具或者武器的一种,其他的还有核技术、纳米技术、基因技术等。科幻也被称作预警文学,功能之一就是提醒人们阻止世界末日的到来。 新京报:科幻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没有过的文学类型。西方科幻二百年的发展史,对中国科幻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韩松:现代科幻被认为是1818年出现在英国的,是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产物。中国长期是农业大国,真正持续的科幻热兴起比较晚。西方科幻给我们的借鉴启示是,创作类型要更加包容,想象力还要更解放一些,要紧跟科技前沿发展,要直面人类最难以启齿的问题,要用大无畏的精神去挑战前任制定的规则,它们不一定都是对的。另外科幻的核心是人文而不是科学,它寄寓着文艺复兴的灵魂。
《驱魔》 作者:韩松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年5月
王晋康,科幻作家,代表作《十字》《与吾同在》等。 新京报:对于如何在科幻这一“舶来品”的外壳之下创造属于自身时代和民族的作品,你有怎样的心得? 王晋康:我的作品在当下的中国科幻作品中,应该是中国味儿最浓的作品之一,我自嘲为“中国红薯味儿”。这与我的年纪和经历有关。作为一位工程师,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仅出于爱好。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我开始科幻写作时,就只是为了写我“个人之所欲言”,心中没有科幻与主流文学的籓篱之见,没有“科幻必须如何写”的定规,也没有经过对国外科幻作品的模仿阶段。再加上我写作科幻时已45岁,与其他年轻作者相差至少一代,是站在过去看未来,所以笔尖下流淌的自然是“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感情、血与汗水。 新京报:在当下这个急速变迁的时代,通过科幻作品,实现对未来的精准预测是否还有可能? 王晋康:对“远未来”不可能精准预测的。科幻文学能做到的是描写101种“可能的未来”,如果真正的未来能包括在这101种描绘中,我们就要开香槟了。但也有可能,真正的未来超出了科幻作家的预测范围。尽管我们以为,随着科学技术的极度昌盛,人类终究能够进入自由王国,能够精确预言乃至操控自己的未来,那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高高兴兴地迎接每一天的朝霞。 相较于“远未来”,科幻对“近未来”做预测的准确性要大一点。比如,对于近两年突然爆发式发展的人工智能,我早在2003年第5期《科幻世界》就发表过《人工智能能超过我们吗?》一文,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直到2005年,美国著名发明家雷·库兹韦尔出版了《奇点》,这个问题才得到广泛关注。
陈致宇,美国华裔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特工袋鼠》。 新京报:总体上,中国科幻作家重点关注“后人类时代”和人工智能两大主题。根据你的观察,现阶段北美科幻关注哪些主题? 陈致宇:当下美国的科幻小说类型非常庞杂,星际旅行的主题近期有回潮的趋势,比如安·乐克(Ann Leckie)的“仆士的正义”系列就是以已有的科幻题材为外衣,注入新的内核。我希望看到更多作家从过去自己喜爱的阅读中汲取营养,然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重新诠释这些理念。 电影和电视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科幻小说。我个人就是因为青少年时期看了《星际迷航》开始对科幻小说感兴趣的。上世纪90年代,因为《终结者2》,我记忆中似乎美国涌现出更多运用科幻元素的动作片。但这些动作片运用未来科技的概念,仅仅是为了合理化那些大场面。 新京报:你如何理解科幻小说之于文学、社会的意义? 陈致宇:有人说,科幻小说其实并不是讲述未来,而是讲述当下。但科幻小说尤其能帮助我们思考未来,以及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学会运用这些或让人警醒或充满启示的想法。 本文整理自新京报书评周刊B03-04版。作者:柏琳、张畅;编辑:张畅、柏琳、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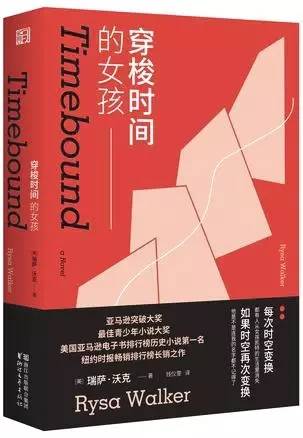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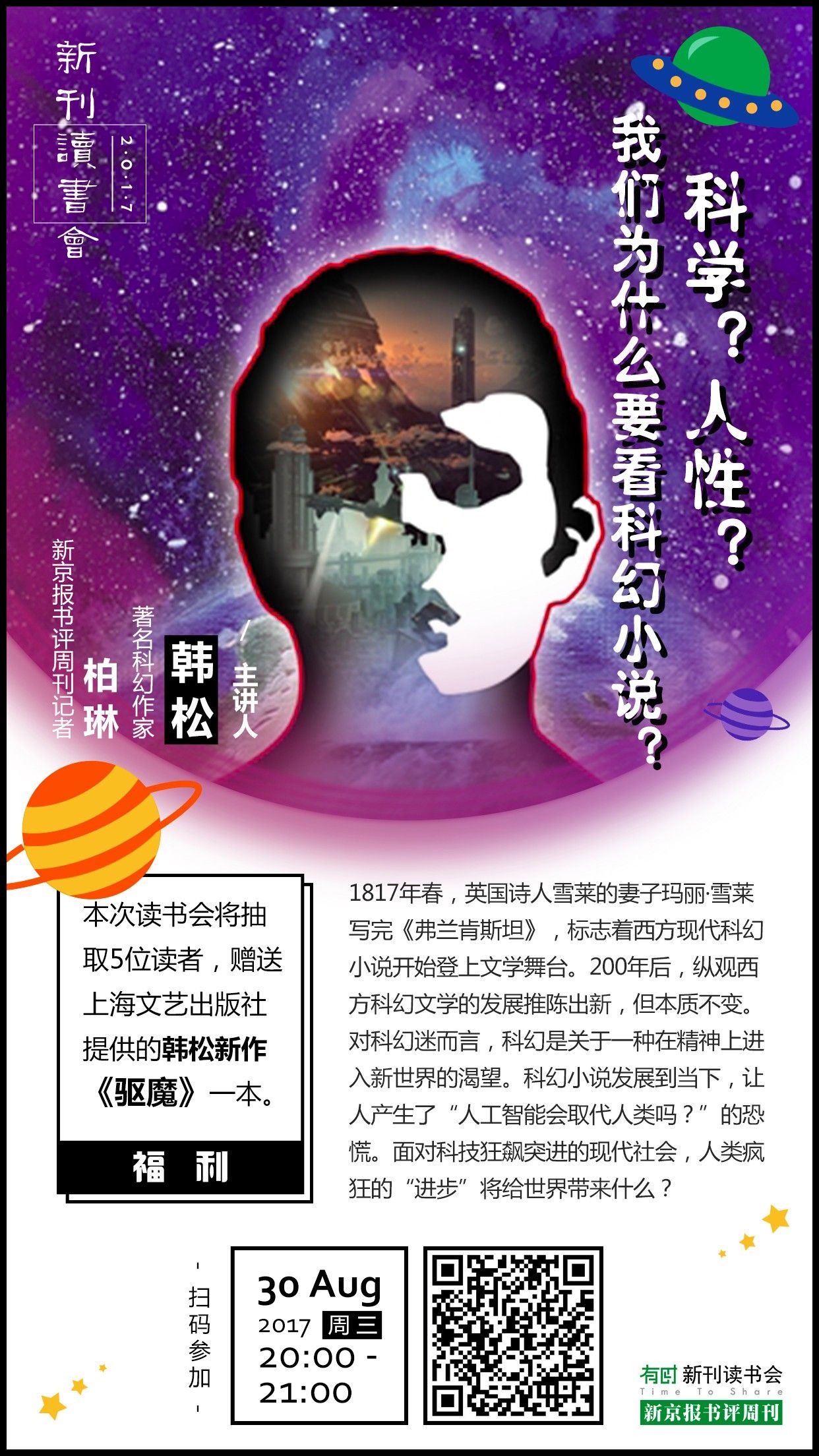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