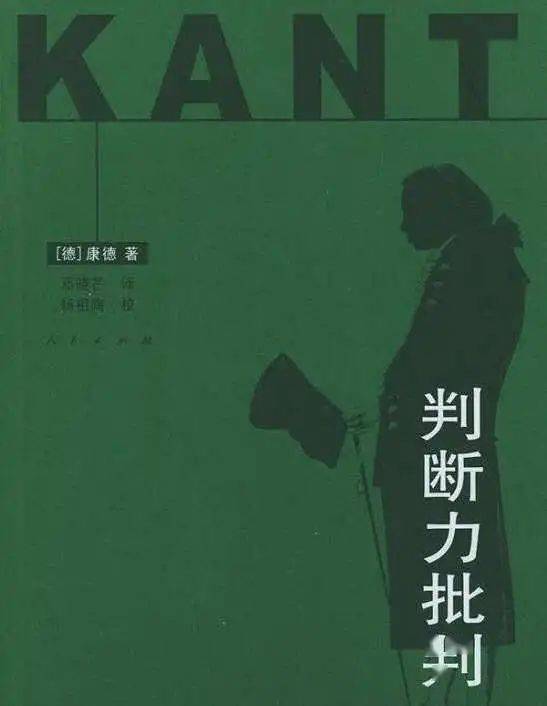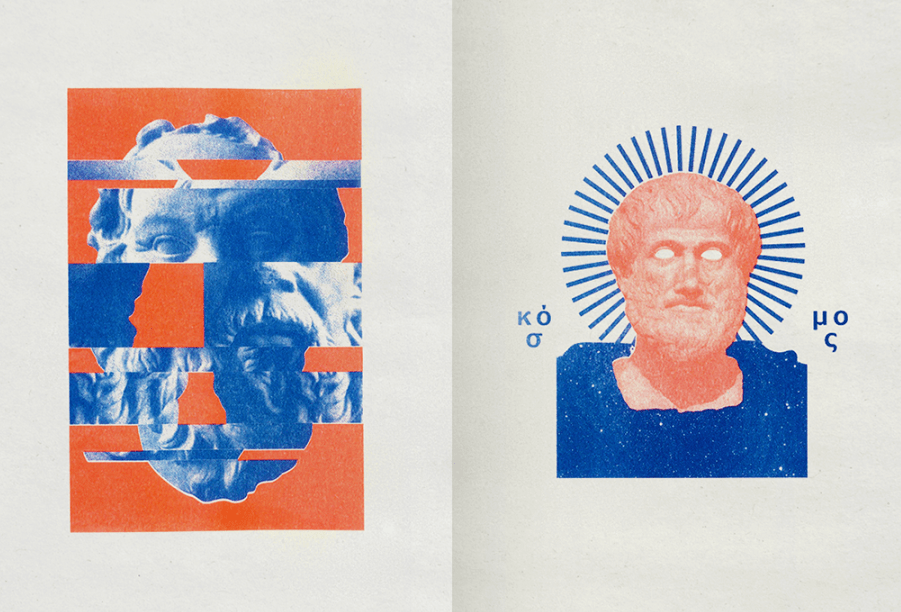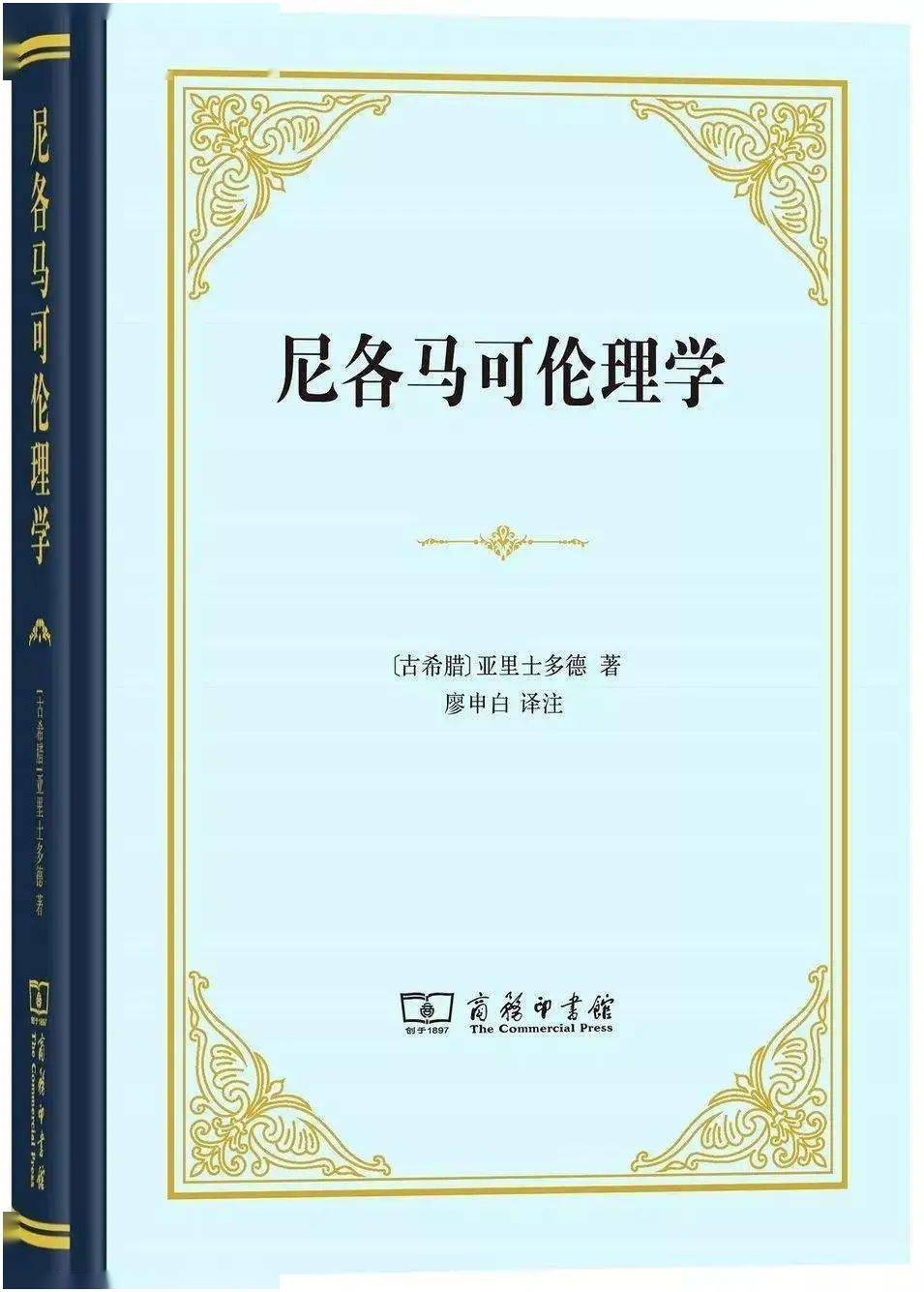伦理德性、明智与共通感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电脑核显和独显哪个好用 › 伦理德性、明智与共通感 |
伦理德性、明智与共通感
|
这种不同,他后来又作了进一步区分:“比起健全知性来,鉴赏有更多的权利可以被称之为共通感;而审美[感性]判断力比智性的判断力更能冠以共同感觉之名。”对此,康德自注: “我们也许可以用审美的共通感来表示鉴赏,用逻辑的共通感来表示普通人类知性。”表征人类在审美活动中共通感觉的共通感,在此就和认识活动中的普通知性也即逻辑共通感区分了开来。当然,康德认为只有前者才能真正被称为共通感。在他那里,审美共通感不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普通知性中倒是有一些,只不过还很模糊——也因此要向更高的纯粹理性的实践法则提升,只有纯粹实践理性确立的道德律才能作为道德的原则。
尽管如此,康德还是认为审美共通感蕴含了 一种应然的要求。这是因为,鉴赏判断建立在我们的情感之上,而情感又具有共通性、普遍的可传达性,且“情感的单纯普遍可传达性本身对我们已经带有某种兴趣”,因此,鉴赏中的情感“被仿佛作为一种义务一样向这个人要求着”。具体来说,“在我们由以宣称某物为美的一切判断中,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有别的意见”, “所以我们不是把这种情感作为私人情感,而是作为共同的情感而置于基础的位置上。于是,这种共通感为此目的就不能建立于经验之上,因为它要授权我们作出那些包含有一个应当在内的判断:它不是说,每个人将会与我们的判断协和一致,而是说,每个人应当与此协调一致”。换言之,审美判断中的规范效力不是来源于所有人具有相同的判断能力,即每个人的判断将会在事实上和我们相同,而是说每个人都应该和我们的判断相协调一致。因为个体的审美判断具有示范性意义,它可以正当地要求别人与此判断协调一致。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作出好的鉴赏判断,这本身就说明了审美共通感的前提性存在。 为了完成判断力批判,康德曾区分了 规定判断力和反思判断力。他认为,把个别事物纳入一般原则的判断力是规定性的,基于个别事物修正、补充着一般规则的判断力则是反思性的。于他而言,规定判断力无疑表现在逻辑、认识领域,而在自然、艺术的美学领域,对事物的鉴赏都是个别趣味性的,因此是反思判断力在起作用。但在伽达默尔看来,反思判断力不能像康德那样局限于审美领域,它还表现在法学上,因为法律知识也是在个别情况对一般性原则修正﹑补充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即便在美学领域,反思判断力的创造性也不来源于单纯的审美。伽达默尔指出:“认为判断力只有在自然和艺术领域内作出对美和崇高东西的判断才是创造性的,绝不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甚至不能像康德那样说,‘主要’在这里我们才能承认判断力的创造性。自然和艺术中的美应当被那弥漫于人的道德现实中的美的整个广阔海洋所充实。” 换言之,判断力不是只有在对美和崇高的判断上才是创造性的,在对善恶是非的道德判断上也是如此,并且,后者才是反思判断力创造性的主要领地。这实际意味着,美的审美意义首要表现在道德之美而非自然和艺术之美上。 伽达默尔进而指出,将判断概念应用于美学,这在康德那里才根本确立,但康德关于规定判断力和反思的审美判断力的区分,根本就有问题。 因为在把个别事物纳入一般原则的规定性判断中,“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审美的判断。这是康德所间接承认的,因为他承认事例对增强判断力的作用”。康德通过审美判断力批判所证明的,不过是不再具有任何关于审美趣味的客观知识的主观普遍性。问题就在于,被归给判断能力的普遍性根本不像康德所说的,是某种抽象的、共同的东西。“判断力与其说是一种能力,毋宁说是一种对一切人提出的要求。所有人都有足够的‘共同感觉’,即判断能力,以致我们能指望他们表现‘共同的意向’,即真正的公民道德的团结一致,但这意味着对于正当和不正当的判断,以及对于‘共同利益’的关心。” 换句话说,审美判断根本不是在目的概念中作为整体被给出的,而毋宁是在所有人的共同感觉、共同意向也就是在共通感中形成的。也因此,共通感中必然蕴含了应然的规范力量。康德对于判断力的运用,正是忽略了它对一切人的要求向度,也即道德的、社会的向度。
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批评康德窄化了共通感的意义。康德为了反对英国的道德情感学说,取缔了共通感的道德含义。如此,原本具有道德、社会意义的共通感,就只被他限定在了审美领域。为了说明共通感的道德意蕴,伽达默尔进一步把它追溯到以维柯、沙夫茨伯里等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中。 在维柯的时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们认为,真理是客观的、必然的,且必定具有普遍的形式与规定。维柯反对这种科学观,照伽达默尔的梳理,他对共通感的援引,正是为了维护个别事物存在权利的或然性真理,说明“新科学”的原理。自然,新科学首先表现在对个别事物持鉴赏态度的美学中,但共通感在维柯那里并非只具有审美意义。 维柯的共通感是指对公共福利和合理事物的共通感觉,且它通过生活的共同性而获得。由此,对一个民族、国家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就不是自然科学所倡导的抽象、绝对普遍性了,而是具体的普遍。维系这一具体普遍性的,正是共通感。也因此,维柯非常重视共通感的培养。对于他, 教化的作用就在于造就共通感。 在沙夫茨伯里那里,共通感除了维柯所强调的意义外,“也是一种对共同体或社会、自然情感、人性、友善品质的爱”。沙夫茨伯里将人文主义对共通感的一般定义——对共同福利的感觉——进行了扩大,在他那里, 共通感与其说是天赋的素质,毋宁说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心灵品性。在他之后,哈奇森﹑休谟进一步将其发展为道德感学说,强势地挑战着传统的形而上学。康德正是由批评英国道德情感说,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哲学大厦,但他的问题也由此开始。作为康德判断力批判之基础的鉴赏或趣味,最早并非审美概念,而是道德概念,因为它描述的是真正的人性理想。伽达默尔由此推论,“一切道德上的决定都需要趣味”,“趣味虽然确实不是道德判断的基础,但它却是道德判断的最高实现”。他也在这样的意义上说,希腊的伦理学,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都是关于好的趣味的伦理学。 二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共通感与伦理德性的内在关联 (一)共通感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思想渊源 伽达默尔在交代共通感的概念史时,明确断言:“共通感概念根本不是起源于希腊哲学家,而是一种听起来像泛音一样的斯多葛概念的回声。”在评述维柯时,他也说:“确切地说,维柯是返回到古罗马的共通感概念,尤其是罗马古典作家所理解的这一概念。” 照此说法,共通感最早是古罗马哲学而非古希腊哲学的概念。现在有学者把共通感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 “共同力”概念,认为它是罗马时期翻译共同力时形成的拉丁文概念。事实并非如此,共同力和共通感根本就是两个概念,共同力是将对同一事物的视觉、听觉等感觉会通为一的灵魂能力,而共通感则鲜明地表现在人文、道德等精神科学的领域。伽达默尔即指出:“这种思想就像斯多葛派的Koinai ennoiai(共同观念)一样,具有某种天赋人权的特色。但是,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共通感也不是希腊人的观念,它完全不表示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里所讲的Koine dynamis(共同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主义所强调的共通感和亚里士多德没有关联。我们仍然可以说,亚氏哲学中有着丰富的共通感意蕴。伽达默尔就仍然将共通感的思想渊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 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共通感概念所蕴含的对个体事物存在权利的辩护、对精神科学领域或然性真理的主张, 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明智和理论智慧的区分中。在他看来:“维柯在这里所强调的,正像我们所指出的,乃是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之间的对立,这是一种不可以归结为真实知识和理论知识之间的对立。实践知识,即phronesis,是另外一类知识,它首先表示;它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因此它必须把握‘情况’的无限多的变化。” 换言之,人的实践所面临的境况都是具体的、当下的,不存在一个普遍规则运用于其上。实践上的原则、真理必定是或然性的,而非严格必然的。因此,明智不同于理论智慧,它必须包含把握道德境况无限变化的能力和智慧。伽达默尔进而说,亚氏关于明智和理论智慧的区分,“其中还有一种积极的伦理的考虑在起作用,这种考虑以后就包含在罗马斯多葛派关于共通感的学说里”。这无疑表明,在罗马时代起始的共通感概念可以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智慧和明智的区分中找到渊源。这一点,我们将留待下一部分具体讨论。在此,先要讨论的是共通感与伦理德性的本质关联。
实际上,人在个别情况中所谋求的正确实践不仅需要掌握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还需要适应既定的社会习俗。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明智之德性是一种精神品性,“他在这种品性里看到的不只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社会习俗存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如果没有整个‘道德品性’就不能存在,就像相反地‘道德品性’如果没有这种规定性也不能存在一样”。换句话说, 明智代表的不唯是主观的道德品性,其中还渗透着社会习俗的客观规定性。而这种化客观的社会习俗为主观精神品性的东西,就是共通感。在将共通感思想追溯到古罗马斯多葛派乃至古希腊伦理学之后,伽达默尔就断言,“基于共相的推论和根据公理的证明都不能是充分的,因为凡事都依赖于具体情况”, “人的道德的和历史的存在,正如它们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所表现的,本身就是被共通感所根本规定的”。伦理、社会意义上的共通感——共通感的原始意义——在此就对人的生活和历史具有了奠基性意义。 因之,当伽达默尔认识到历史的真理源泉不同于理论理性, 当伽达默尔认识到历史的存在权利就在于人的激情不能完全为普遍必然的理性规定所支配,他还是要回到亚里士多德。“在所有这些说法里,亚里士多德所认识的那种伦理习俗知识的存在方式都在起作用。记住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认识,对于精神科学的正当的自我理解来说将会是重要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通感对于历史的作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通过伦理习俗知识的存在方式而建立。 换句话说,共通感就是关于伦理习俗的知识。只不过,这样的知识并非建立在理性科学的范围内,而是关乎个别、具体事务的直观审美活动。而这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心之所同然”之理义。
(二)共通感与伦理德性的本质关联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道德、伦理的根源被追溯到它的历史基础,也即伦理教化和习惯风俗之中,而不像康德那样,归为纯粹实践理性为自身实践确立的道德律。这是因为,在亚氏看来, “正如其他技术一样,我们必须先进行现实活动,才能得到这些德性”,我们只有在建筑活动中才能成为建筑师,在演奏活动中才能成为演奏家,“同样,我们做公正的事情才能成为公正的,进行节制才能成为节制的,表现勇敢才能成为勇敢的”。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在有德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养成伦理的诸德性。 “品质是来自相同的现实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像柏拉图一样,非常强调自孩童时期起就必须有的伦理教化,他认为“从小就养成这样或那样的习惯不是件小事情,相反,非常重要,比一切都重要”。如此,伦理教化和社会风俗就对人的德性之形成有着基础的作用。 但要注意,一个人做公正的、勇敢的、审慎的有德之行,并不意味着他就能达到中庸的德行境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中庸才是伦理德性的真正形态。亚里士多德一再讲,“不论就实体而论,还是就是其所是的原理而论,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伦理德性就是中间性”。如是, 从伦理教化到中庸之至德,这中间是如何过渡的,在解释上就是一个问题。 严格说起来,社会习俗和伦理教化塑造的只是共通感,而非就是伦理德性本身。因为教化和习俗培养的首先是我们自小起就对哪些事物是好的、善的,哪些事物是坏的、恶的直观感受或感觉,而 这种关于伦理习俗的知识,这种善恶感就是共通感。 亚里士多德一再讲,伦理教化在于自小就培养人们对应做之事的正确情感,因为“伴随着活动成果的快乐和痛苦,形成人们品质的表征”。我们对回避肉体快乐感到快乐,就是节制,相反则是放纵;对危险能坚定不移,就是勇敢,相反则是怯懦。既然一切行为和感受都伴随着快乐和痛苦,伦理德性也自然与快乐、痛苦有关。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伦理德性就是关于快乐和痛苦的德性”,“伦理德性是一种关于快乐和痛苦的较好的行为,相反的行为就是坏的”。也就是说,伦理德性与行为及其伴随着的苦乐感内在相关。当然,此所谓苦与乐不是感性欲望之满足与否造成的苦、乐,而是精神层面上的道德之苦乐。而这种苦乐感就是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等的好恶感,也即我们所说的共通感。 由于它是在共同的城邦生活中被教化所塑造的,所以具有共通性、可传达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与共通感的关联是本质性的。他总结性地讲道:“德性以关于快乐和痛苦而存在,由快乐和痛苦而生成和增长,相反则毁灭。同时现实活动也由它们而生成,是关于它们的现实活动。”这实际意味着, 共通感是伦理德性的根源和前提,而伦理德性也是在共通感中得到的自我实现。 进而言之,伦理德性何以必须在共通的苦乐感,也即共通感的范围内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原因正在于,是共通感使得中庸之德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所论之中庸,最基本的面向指向感受。他认为,在关于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一个人恐惧、勇敢﹑欲望﹑愤怒和怜悯,总之,感到痛苦和快乐,这可以多,也可以少”,多就是过、少就是不及,而伦理德性就是“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 如是,中庸就表现为苦乐感受中的适度。 这一适度,实则来源于共通感的可传达性、可比较性。由于在生活实践中,人的苦乐、好恶的感觉是一种审美判断, 在伦理习俗,具体来说是共通感的前提下,它应当同别人的苦乐、好恶判断保持协调一致——不是事实上一定会相同、一样——所以它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规范力量,使得人们的行为不过也无不及。作为适度,适宜的中庸之德性正是由此实现。亚里士多德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说:“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 伦理德性与共通感的本质关联,也可以从 城邦政治的角度得到说明。毋庸置疑,伦理德性与城邦政治有着撇不清的关系。余纪元即指出,《政治学》中阐述的“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的理论是理解《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的必要部分。亚里士多德在论及伦理德性的时候,确乎讲到:“立法者通过习惯造成善良的公民,所有的立法者的意图都是如此,不过有一些做得不好,他们失败了。一个好政体和一个坏政体的区别就在这里。”《政治学》中也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 城邦具有好的政体,无疑有利于其公民趋于完善、有德。 换句话说,在很重要的意义上,城邦政治与共同体生活是伦理德性形成的前提。在伽达默尔对人文主义的追溯中,共通感和政治的密切关联亦是他强调的重点之一。这就无怪乎唐文明把共通感视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这个命题的一个注解。 从我们的立场看,人天生处在一定的城邦共同体之中,对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等自然会形成一定的、通行的、可传达的直观感受。这也就是共通感。人们正是在这一共通的、可传达的好恶感受中,达到彼此协调、协和地生活。尽管共通感依赖于城邦的伦理教化和风俗习惯,但就人天然地处在一定的城邦共同体中而言,它好比是人的“天赋人权”,如斯多噶派所强调的那样。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共通感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伦理德性由此而出、中庸即此而现。
三 共通感、伦理德性与明智三者间的诠释循环 亚里士多德把人的灵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禀有理性,一部分没有理性。在实践问题上,未禀有理性部分的灵魂其德性是伦理德性;辜有理性部分的灵魂其德性是理智德性。 在亚氏伦理学中,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绝对是两个核心的概念。作为伦理德性的中庸与作为理智德性的明智其关系为何,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曾明言,明智是伦理德性的一个部分,“没有明智也就没有正确的选择,正如没有了德性一样。因为德性提供了目的,明智则提供了达到目的的实践”。就是说,德性确定善的目的,而明智选择达到此目的的方式。换言之,明智要以伦理德性为前提、目标,而伦理德性的实现又依赖于明智的参与。 但正如余纪元指出的,“回顾一下《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第6章对德性的总定义。德性是一种能作出选择的品质,是一种中庸,是由理性决定的。 换句话说,伦理德性自身要求实践智慧去决定。而现在亚里士多德又说,伦理德性为实践智慧提供目的。这不是陷入‘循环论证’了吗?”但余纪元毕竟没有对这种“循环”具体给出解释。以下从共通感的角度,试作说明。 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共通感思想时,唐文明曾指出, 亚氏区分理论智慧和明智的关键在于,把共通感中的祈使力量与共同体生活也即社会习俗紧密联系了起来。社会习俗的存在是共通感的前提条件,“而实践之知作为与社会习俗的存在直接相关的一种知识,正是以共通感为基础产生出来的”,因此,“社会习俗的存在、共通感与实践之知就恰当地构成了诠释的循环”。由是,亚氏共通感思想的理解脉络就在于习俗、共通感、明智三者间的解释循环。但已如前述,唐氏所谓“与社会习俗的存在直接相关的一种知识”,也即伽达默尔评述亚里士多德时所说的论理习俗的知识,是关乎善恶、是非、美丑等的道德感或共通感,而非就是指明智。故而唐文明的总结还不确切, 正确的说法是,在共通感﹑伦理德性、明智三者间存在一种诠释上的循环。 毋庸置疑,伦理实践要以一定的社会风俗、城邦政治为前提。人们总是在这样那样天然的人文环境中成长,形成共通感,并进而在其中实现可能的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以中庸为伦理德性的本质特征,正是基于共通感这一隐秘的前提。但如余纪元所说,在对伦理德性的总界定中,亚氏确乎用到了明智:“德性作为对于我们的中庸之道,它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它受到理性的规定,像一个明智人那样提出要求。”德性是选择的品质,并且要如明智之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这说明只有明智的人才能达到中庸。换句话说,作为伦理德性的中庸的完全实现才是明智!在此,明智似乎就被拉到了伦理德性之中。 问题的关键是,作为理智德性的明智如何被带入到伦理德性之中? 毫无疑问,行为上的中庸直接地属于实践领域,是明智管辖的范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是在苦乐感受和行为两方面都命中中间、达到中庸。事实上,在实践中,明智之人正是以伦理德性为目的,以共通感为前提,来达到、命中中庸这一目标。只有在共通的、可传达的苦乐感受中。人们才于能做到发于情、止乎礼,与他人的行为保持协调一致,做到中庸。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伦理德性的中庸正是根源于共通的苦乐感,而在行为﹑实践中具体实现。
关于实践,亚里士多德并未给出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在他看来,人类的行为应该以合乎正确的理性为目标,但“关于行为的全部原理,只能是粗略的,而非精确不变的”,理性所提供的严格普遍的规则和原理并不能适用于实践领域,实践“只能是对症下药、顺水推舟,看情况怎样合适就怎样去做,正如医生和舵手那样”。换句话说,在行为实践上并不能达到严格的科学性,也没有什么普遍适用、固定不变的伦理原则。每一行为都要视具体情况定。 在具体情境中,我们依靠什么来下判断呢?亚氏认为,依靠的是感觉。他讲:“感觉的东西是难以规定的,它们总是在个别情况之下,而决定又是在感觉之中。”据此,决定行为的不是理性的思考和知识,而是直接的感觉,也即直观、直觉。这在本质上属于审美判断或判断力。在评述亚氏伦理学时,邓安庆也类似地指出,理智德性关乎在具体处境中如何行动最合适,主要体现为判断力和理解力。而这一点,亚氏主要就是从明智的角度来讲的。 在他那里,保证伦理实践之成功的是明智,而明智与否在于直觉、直观判断。直觉判断不是理性知识,而是对个别事物作鉴赏﹑审美判断,所以它能够和共通感联系起来。实则,之所以明智要以伦理德性提供目的,是因为 在共通感的要求下,明智之人的判断才会和别人的协调﹑和谐。 我们始终不要忘了,在实践活动中,明智之德性所依赖的判断是一种审美判断。如John Milliken所说;“有德之人不是计算出美(Kalon)的事物是什么;毋宁是,他看到了它。所有美的行为共有的形式不是被意识抓住的东西,而可以说是被心。有德之人出于美而行动。”伽达默尔也始终强调, 审美判断是对个别性事物的鉴赏判断。在此过程中,明智之德会加深、强化、提升善和美的趣味,也会修正、补充、发展着共通感,同时,也因此维系着城邦共同体和社会习俗的存在。对于明智及其运行原则,亚氏并未明确给出界定,而只是说“关于明智,只要我们考察那些明智的人,就可以明白了”,道理也在这里。 因此,明智以伦理德性为前提、目的,但在现实表现中,它又会深化、发展、修正着伦理德性赖以存在的共通感。而已如上述,共通感是伦理德性的根源,伦理德性要在共通感中才能得到实现。如是,共通感﹑伦理德性与明智三者之间始终存在一种诠释上的循环。 来源:叶云,《道德与文明》,2017年第6期,第155-160页。 另一种普遍主义:范例的力量 论阿伦特政治判断与审美判断的可通约性 我为何信任你
simple living,noble thinking 排版|张银浩 校对|汪 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