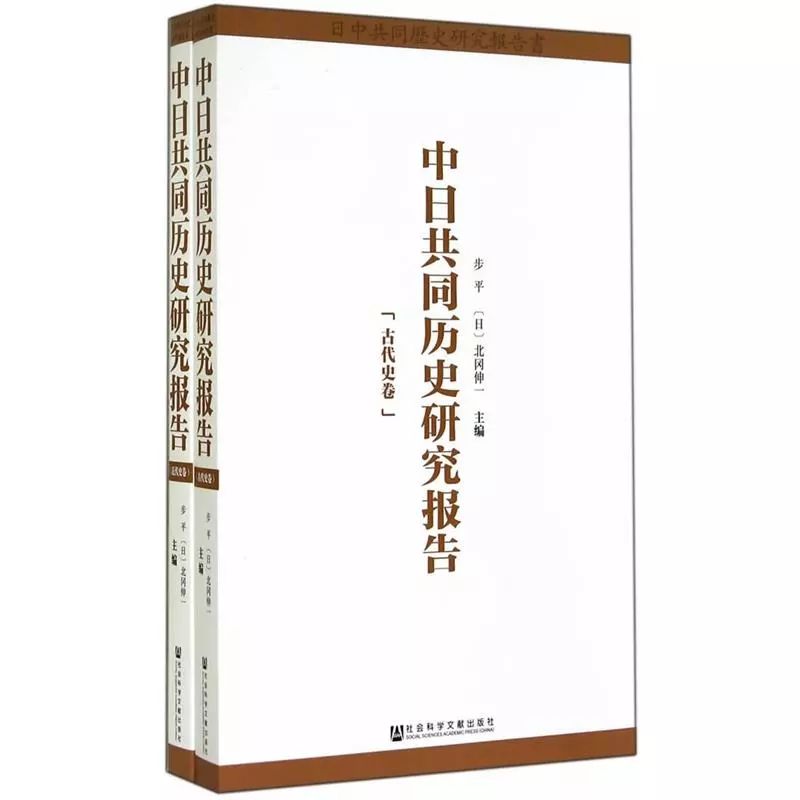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日本人眼中的丽泽大学 › 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
日本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
诚然,由于战时日本严厉的新闻封锁、归国日军官兵的“禁口令”等,日本国民当时确实不太了解南京大屠杀,但并非毫不知情。一是日本政府和军队上层早已获悉南京大屠杀的情况,尤其是随着日军返回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将日军暴行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暴行的“抗议”呈报外务省。1938年1月17日,外相广田弘毅致电日本驻美使馆,其中提到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逾30万”。笠原十九司指出,南京大屠杀期间,“日本政府、军方的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拥有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二是日本《东京日日新闻》《鹿儿岛每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鹿儿岛朝日新闻》等对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百人斩竞赛”的持续报道,日本人对此不可能毫无所知。三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通过从上海到南京的调查采访,以参与实施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官兵为原型创作了《活着的士兵》,发表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虽于发售次日被禁,且石川本人也被判拘役4个月、缓刑3年,但有些日本人还是从各种渠道获知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一些消息,日本“当时的多数国民,朦胧感觉发生过南京事件,但只是模棱两可的认识”。 战后日本历史教科书和大部分著作,往往称战时日本国民完全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似乎平添了不少日本国民的无辜感。甚至暗含倘若日本国民知道南京大屠杀,便会站出来反对的凛然大义感。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近代日本侵华史上制造了多次大屠杀事件,如甲午战争期间的旅顺大屠杀、1928年5月出兵山东的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后的平顶山惨案等。当年日本人或多或少知道这些暴行,但从未见他们反对和谴责,反而欣然接受日本侵华战果,形成了蔑视中国、“膺惩暴支”的侵华战争狂热,南京大屠杀不过是近代日本制造历次大屠杀事件的延续和扩大。日本进步学者津田道夫在《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指出:“滥杀无辜,掠夺以及令人酸楚的对女性的暴力——强奸、轮奸、杀戮,这一切都无疑暴露了日军官兵的人格崩溃。而且,后方日本大众的道德同样败坏,这可以说是前方败坏的基础。”因此,即使战时日本国民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全貌与真相,也不可能站出来批判。 日本国民在东京审判期间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介绍,反应比较平静,既没有“晴天霹雳”般的震惊,也没有公开反对和拒绝,而是冷漠地接受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佐证了津田的观点。战后初期日本经济衰败、物资匮乏、生活困苦,日本民众中普遍弥漫着一种战争受害意识,未能主动思考日本侵略战争带给受害国民众更大的灾难。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于1945年12月由河出书房出版单行本;堀田善卫从1953年开始,以“时间”为题,先后在《世界》《文学界》《改造》3家知名杂志上发表主要描述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且于1955年由新潮社出版单行本,但并未引起日本社会的强烈关注。东京审判前后,《朝日新闻》转载的战犯起诉书、发表的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章、对中国南京审判的报道等,虽记述了战时日军的南京暴行,但如同三岛由纪夫在短篇小说《牡丹》中描述原日军官兵在南京滥杀无辜一样,只含有“呈现真实和历史反省的成分”,缺少对中国人加害责任的思考。 无论东京审判,还是新闻媒体对日军暴行的报道,都是美国开展“日本人再教育计划”的一部分,这是南京大屠杀进入战后日本人视野的重要原因之一。1945年12月8日,盟军总司令部命日本各大媒体连载由美国战时情报局职员、盟军总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企划课课长布拉特·史密斯执笔的《太平洋战争史——军国主义日本崩溃的真相》,内含南京大屠杀一节。1946年2月17日,NHK开通广播栏目《真相盒》,其中也有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毕竟有限,且“并不客观,充斥了虚假宣传的色彩”,关键是缺少中国受害者出面作证,受到不少日本人的质疑,“没有成为大多数国民的记忆”,反而成为日后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所谓“证据”之一。美国的“日本人再教育计划”成效暂且不论,至少为战后日本出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著作和自由报道创造了氛围与条件。于是,田中隆吉、石射猪太郎等出版了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回忆,进步人士金子廉二呼吁日本民众认清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责任,1948年石川欣一翻译美国驻日大使约翰·格鲁的《在日十年》中也有南京大屠杀的记述,甚至南京大屠杀还进入了日本教科书。 二、教科书中的南京大屠杀 历史教科书既体现一个国家对待历史的态度,也反映其现实关怀和发展方向。美国主导下的日本民主化改革,大力铲除战前和战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避免日本再次成为美国的威胁,于1947年帮助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以培养建设和平国家和身心健康的日本国民为基本方针。因此,战后初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依据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在叙述日本侵略战争时,提到了南京大屠杀。但其内容比较简单、笼统,往往是一句话,即“日军占领南京时实施了残杀行为”“日军在南京的残杀行为”“南京暴行等事件”。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将日本建成东亚防共的“防波堤”和反共的“桥头堡”,逐渐放松对日本右翼的压制,所谓“民主化改革”以虎头蛇尾收场。日本历史教科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以“进出”代替“侵略”的“改恶”趋势,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家永三郎 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1963年被文部省审定“不合格”,后经修改于翌年提交审查,结果仍有293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引起了他的愤怒。家永三郎遂以文部省的审查违背教育自由的原则,于1965年6月12日、1967年6月23日、1984年1月9日分别以日本政府、文部省、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3次诉讼。其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争论点,是家永三郎在教科书的注释中指出日军占领南京后杀害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军民,即“南京大屠杀”。文部省认为据此注释可以理解为日军实施了“有组织的屠杀”,要求“改正”,说明那是在“混乱”之中发生的事情。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所提供的强大学术支持,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省关于“南京大屠杀”审定意见违法,责令政府赔偿家永三郎40万日元。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活动,借助中日复交后“和平友好”的两国关系,促使20世纪50年代后日渐弱化或消失的南京大屠杀重回教科书,到1984年几乎所有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这一历史事实。 日本右翼攻击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是“自虐”,组织以原文部省主任教科书调查官村尾次郎为代表的“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在1986年由原书房出版高中历史教科书《新编日本史》,是为此后扶桑社版、育鹏社版、自由社版、明成社版右翼历史教科书的原型,但受到多数高中历史教师的抵制。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最高采用数是1989年9357册,到2016年降至4110册,占高中历史教科书采用率的0.08%。笠原十九司以扶桑社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为例,分析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招数”:一是以括号注解的形式说明日军占领南京后,普通百姓死伤较多,因为是括号中的内容,所以往往不太被重视,以此降低南京大屠杀的影响。二是通过“不过”这一转折词,强调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因为资料上有疑点、众说纷纭,所以尚在争论之中,以此“虚化”南京大屠杀。但是,如此违背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判决的历史教科书,竟能通过文部科学省的审查,而那些越详细越正确记述南京大屠杀的教科书的采用率却有所下降。这个现象值得警惕。 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以来,中国人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记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侵华史实非常敏感,甚至不少民众误将日本历史教科书与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历史事实画等号,而中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越来越理性。孙智昌指出,日本政府因教科书事件而公布“近邻诸国条款”后,日本历史教科书记载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增多了一些,但主要描述中国军民因此增强了抗战意识;在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上,以东京审判的20万人为上限,几乎没有一本承认30万人,甚至不少还没有具体数字;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受害内容占据大量篇幅相比,南京大屠杀往往一两句,多则三四句,如此容易混淆加害与受害、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钟成发现,绝大多数日本历史教科书虽涉及南京大屠杀,但往往一笔带过,甚至其注解长于正文,即使介绍中国的“30万人”说,也会补充日本学者的不同观点。据报道,继现行教科书之后,日本各校2017年春季采用新的世界史和日本史教科书都将涉及南京大屠杀,但对于屠杀人数,文部科学省的审定意见仍是“存在多种说法”。其实,日本历史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大多采取“中性”立场,虽缺乏对侵略战争的深刻反省,但主流还是比较客观的,这与日本社会的南京大屠杀肯定派、虚构派和中间派的争论有所区别。 三、三派“斗法”与二元“争论” 南京大屠杀虽作为历史记忆在日本传承,但并未成为日本国民的历史“共识”。如战时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今井正刚、秦贤助等人,在战后初期就发表了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回忆性文章。平凡社于1961年出版的10卷本《亚洲历史事典》中,“南京事件”也占有7行的分量。1967年日本进步人士新岛良友访问南京后,连续发表几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章。洞富雄的《近代战史之谜》,以大量篇幅介绍南京大屠杀。《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也多次提到南京大屠杀。 然而,那些原本就对战争责任没有什么反省的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借助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力和美国深陷美苏争霸、越南战争而无暇顾及的国际环境,掀起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日本作家林房雄从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在《中央公论》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原日军第六师团随军记者五岛广作,在《熊本广播》1966年8、9、11月号上连载《六师团无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铃木明从1972年在《诸君》上连载《“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否认战时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暴行。由此,南京大屠杀肯定派(亦称“屠杀派”)与虚构派开始延续至今的“争论”,进一步撕裂了日本国民的南京大屠杀认识。 肯定派与虚构派的“争论”中衍生出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所谓“实证研究”的“过少评价派”,即“中间派”,形成了三派“斗法”的局面,但仍以肯定派与虚构派之间的二元“争论”为主。笠原十九司指出,到21世纪初,日本社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总体而言以虚构派的失败告终。但是,由于保守派政治家和右翼分子的反对,且试图从日本“国民的记忆”中抹除南京大屠杀,导致“争论”的双方至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给人一种‘半斤八两,都不咋样’‘泥潭中搏斗’的印象,使得大多数日本人逐渐退缩,最终成了旁观者。这也是南京事件的历史认识难以在日本社会形成固定共识的巨大障碍”。高兴祖、王希亮、程兆奇、笠原十九司等学者,已详细介绍肯定派、虚构派、中间派关于南京大屠杀“争论”的来龙去脉和基本情况,此处不再赘述。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虚构派将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成果”译成英文,试图向英语世界扩大影响。不过,西方大部分历史学家以专业化、客观化态度和严谨治学原则,抵制日本右翼对南京大屠杀的歪曲,逐渐主导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在西方的发展方向。 中国学界以史料为基础,坚持一切归真,批驳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错误言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原秘书田中正明,于1984年出版《南京大屠杀之虚构》、1985年出版《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中,妄称南京大屠杀时南京人口仅有20万,进入南京的日本记者“从未”见到屠杀。高兴祖以当时南京的人口资料、国共两党报刊的报道和战后日本记者的回忆,指出南京大屠杀“不容抹杀”。李松林指出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阵中日记”900多处,其中最严重的部分是占领南京前后的这一章。章开沅以耶鲁大学所藏“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指出当年日军控制下的新闻机构和今天的日本右翼是伪证制造者。张宪文以目前搜集的8国语言的4000多万字的南京大屠杀资料,揭批日本右翼的南京大屠杀“伪造论”。但是,日本右翼以伪证为“铁证”,以狡辩为学术,“检证”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没有一张是“真实”的,污蔑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中国学界清楚他们抹杀南京大屠杀的伎俩和目的,但不可能将之彻底击碎,因为“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中国学界联合清醒的日本进步人士,共同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一是向中国介绍日本进步学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成果。如洞富雄的“定本”《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之证明》等出版后,很快就被介绍到中国。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构造》,被称作“无惧地解剖日本人的精神世界”的著作。笠原十九司的不少论著直接在中国发表。二是宣传日本进步人士、友好团体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采访、忏悔反省活动。1985年以来长期带领“铭心会”到南京忏悔和访问的松冈环,多次在中日两国举办南京大屠杀纪念活动,以促使“更多的日本人反省侵略历史”。三是支持日本老兵的南京大屠杀证言活动。一些日本老兵在战后出版或展示自己的战场日记,透露亲历或目睹之“南京大屠杀”。他们的证言活动遭到右翼分子的干扰和破坏,引发了一场著名官司——东史郎诉讼案。中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支持东史郎,但东史郎最终败诉,反映了日本司法界的南京大屠杀认识不足与局限。 日本进步人士与中国学界在南京大屠杀基本事实、日军残暴行为方面具有“共识”,但在屠杀人数、原因方面并非完全一致。如日本进步人士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和东京审判,一般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是20万或10余万,但不排除今后根据新发掘资料增加遇难人数的可能性,而中国学界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30万。在对南京大屠杀的描述中,中国学界侧重介绍屠杀规模和残暴行为,强调日军官兵的战争罪行,而日本学界重在分析屠杀原因与人数争议。2010年初,《》公布前后,日本媒体大肆宣扬中日双方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上的“鸿沟”,试图抹杀双方共同认定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实这一重要成果。日本一些政治家常谓:“相信历史学家会对历史问题给予准确的叙述。”如今中日历史学家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得出了结论,而日本一些政治家、右翼分子却一仍其旧。如此,南京大屠杀研究之路任重道远。中日学者建议从多个视角出发,如实记述每位大屠杀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建立南京大屠杀资料库,加强国际学术对话与交流,引导南京大屠杀记忆的传承与形成更加广泛的“共识”。这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南京大屠杀研究颇有启发。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结 语 南京大屠杀至今80年,其间日本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深受东亚局势和中日关系影响。日本人战时隐约知晓南京大屠杀,在战后初期更加了解真相,但随着冷战开启和美国转变对日政策,对其关注度不断下降,直到中日复交前后一些日本人才再次关注南京大屠杀,而与之同时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也甚嚣尘上,终成影响中日关系和两国民众感情的障碍之一。二是日本社会围绕南京大屠杀,出现了肯定派、虚构派、中间派三派“斗法”与二元“争论”局面,虽延续至今,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越辩越明,被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所接受。无论日本政府的公开声明,还是绝大多数日本历史教科书,都承认南京大屠杀,这一结果是虚构派始料未及的。三是受到中国社会的高度关注,推动了中国学界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发展。 中国学界组建南京大屠杀研究机构和积极培养相关研究人才,出版南京大屠杀研究系列成果,基本形成以南京学者为主的中国南京大屠杀研究学派。他们对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认识有了越来越理性的观察,这既体现了中国学术的进步与发展,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和拓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广度而言,我们既要将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认识置于长时段的历史中考察,思考他们对近代日本制造历次大屠杀的认识与反应,又要联系世界范围内的大屠杀事件,如亚美尼亚惨剧、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等,对比加害方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各国之间的历史“和解”。从深度而言,我们既要通过战场日记、文学作品、学术论著等,分析与解构日本人个体认识南京大屠杀的心灵世界,也要深挖战时日军集体残暴和战后日本社会三派“斗法”、二元“争论”的思想根源,以免其恶性基因重组。就面向未来而言,中日学术研究与对话似乎未能阻止日本政客、右翼分子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歧路上“狂奔”。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认识仍是影响中日关系和两国民众感情的一个重要因素。破解这一难题,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中日学界扎实研究、持续努力,需要彼此联合、相互交流、扩大共识、影响民众。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注释从略。 图片均来源于百度图片 责任编辑:刘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