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年:他相信下一本“玫瑰”在空白纸里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带玫瑰的小说都有啥书名 › 《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年:他相信下一本“玫瑰”在空白纸里 |
《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年:他相信下一本“玫瑰”在空白纸里
|
原创 傅小平 文学报 文学报  最近,关心作家翁贝托·埃科的读者会发现相关新闻又多了起来,不仅国内出版社首次引进出版了“继《玫瑰的名字》之后最精彩的小说”《布拉格公墓》,也是《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意大利忒修斯的船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新版。作为迄今最完整的一个版本,该版本恢复了当初邦皮亚尼版中删除的部分文字,还首次以影印方式收入了大约二十页的埃科创作笔记、迷宫地图和作者手绘的书中人物画像。 最近,关心作家翁贝托·埃科的读者会发现相关新闻又多了起来,不仅国内出版社首次引进出版了“继《玫瑰的名字》之后最精彩的小说”《布拉格公墓》,也是《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意大利忒修斯的船出版社推出了该书的新版。作为迄今最完整的一个版本,该版本恢复了当初邦皮亚尼版中删除的部分文字,还首次以影印方式收入了大约二十页的埃科创作笔记、迷宫地图和作者手绘的书中人物画像。今天夜读,从这两部作品出发, 回溯埃科的文学人生。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果有一天去了另一个世界,最想把哪本最钟爱的书带走?翁贝托· 埃科回答说,他可能带上的是《玫瑰的名字》(1980),不是因为钟爱,而是因为讨厌。他写了这么多书,人们说来说去就是这本,因为不断有人提,他不想听到有人再提了,但他不能不说,他所有的名声都来自这本书,所以如果只能带上一本,他一定得把它带上。 今年是《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意大利忒修斯的船出版社推出该书的新版。作为迄今最完整的一个版本,该版本恢复了当初邦皮亚尼版中删除的部分文字,还首次以影印方式收入了大约二十页的埃科创作笔记、迷宫地图和作者手绘的书中人物画像。这些速写形式的画像是埃科在创作过程中为了给笔下人物以具象,以便用文字加以描摹而在笔记本上画出来的。而《玫瑰的名字》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在2017年2月19日埃科逝世一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虽意在推广埃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试刊号》,却选择“以玫瑰之名”来纪念他。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次采访中,埃科还给采访他的记者,看了一本他最想给读者看的书,一本还只是一张张白纸的书。他诙谐地说,他还没有写的这本书,会是他最好的一本书。那时,他多半没有想到,《试刊号》成了他的“天鹅绝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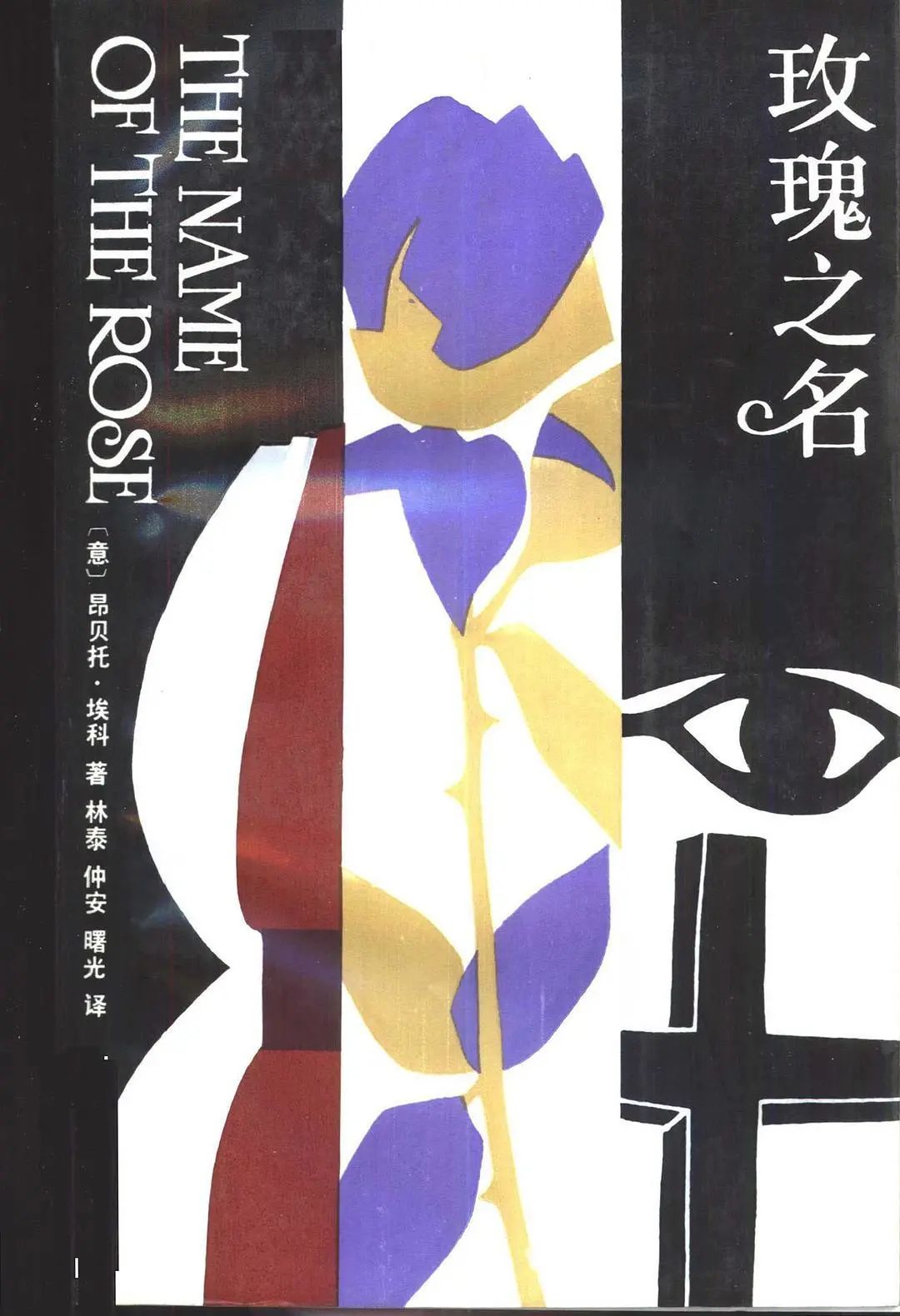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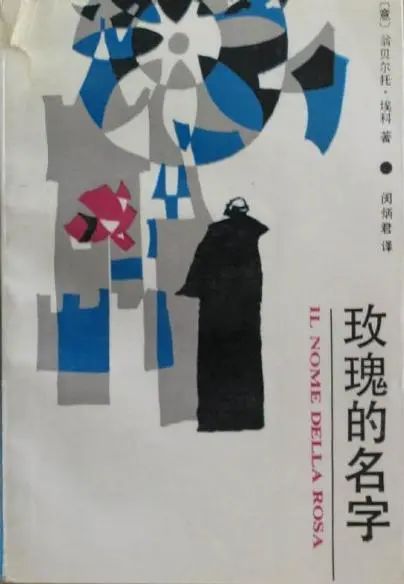  《玫瑰的名字》中文版部分版本封面书影 《玫瑰的名字》中文版部分版本封面书影埃科式的反讽于此可见一斑。这位充满智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公众场合与人交谈时,埃科经常口出妙语:他说“上帝躲起来了,因为他不想上《VOGUE》杂志”;他说“现实比梦好:假如有东西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而不会怪罪于你”;他说“要建立不朽的声名,你首先需要宇宙性的无耻”。在《试刊号》中文译者魏怡看来,埃科对人对事总是持一种善意嘲笑的态度。“他生前的留影也大多是微笑的,毫无疑问是智慧的微笑。”而《试刊号》,某种意义上也是埃科和大众媒体开的一个并非恶意的,却是力度很彻底的玩笑。 《试刊号》故事背景设在1992年的米兰。主人公科洛纳和其他几名记者一起,受雇于一份正处筹备中的报纸《明日报》。他们研究过去的新闻,试图编造出一份模拟的“创刊号”。但在实验过程中,种种现实却不容置疑地跃入眼前。“人们都以为墨索里尼已经死了,而自1945年以来,意大利发生的每一件大事背后,都飘荡着他的幽灵…… ”某天早晨,提出这惊人假设的记者惨遭杀害。实际上,这份报纸不过是用以煽风点火、诽谤和勒索的工具,是身为传媒巨头的幕后老板打入意大利政治核心的垫脚石。 虽然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遥远异国,但读者自会会心地意识到,小说里的描述同样照见当下新闻业的种种弊病。诚如书评人btr所说,在某一刹那,我们仿佛借由小说进入了时空隧道。“今昔对照,你不由会怀疑埃科其实活在当下。他是那个揭露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孩子。” 相比而言,在出版于2010年,最近才由该社推出中文版的《布拉格公墓》里,埃科的戏谑讽刺还要辛辣得多。小说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主人公西莫尼尼一觉醒来,发现忘了自己是谁,失忆的恐慌与不安让他决定仿效弗洛伊德,对自己进行精神治疗。他通过写日记的方式,逐步从记忆的迷雾中寻回那个孤独的童年,被生活抽打的青年,以及在成为秘密警察的眼线以后,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背信弃义、随意出卖朋友、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人。他为各方所用,周旋于秘密警察、教会、阴谋家、革命者和御用文人之间,在半个欧洲从事间谍活动,策划暗杀,伪造反对犹太人和共济会的文书,谋取钱财。但正是他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居然成为十九世纪后半叶整个欧洲政治和历史发展的导向。  恰如有论者所言,小说以多重人格日记体串联起意大利复兴运动、巴黎公社、德累斯顿事件等历史疑云,在虚构与历史之间,以伪造者的身份对反犹主义、共济会、耶稣会、烧炭党人进行“阴谋论”式的辛辣戏谑讽刺,“必须如此捏造阴谋”的动机思路看似荒诞又真实还原了煽动者和投机分子的嘴脸。埃科更是借人物的口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各种原因,其中有一句话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像西莫尼尼这样的人,“干脆跟你说了吧,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 恰如有论者所言,小说以多重人格日记体串联起意大利复兴运动、巴黎公社、德累斯顿事件等历史疑云,在虚构与历史之间,以伪造者的身份对反犹主义、共济会、耶稣会、烧炭党人进行“阴谋论”式的辛辣戏谑讽刺,“必须如此捏造阴谋”的动机思路看似荒诞又真实还原了煽动者和投机分子的嘴脸。埃科更是借人物的口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各种原因,其中有一句话足以让人不寒而栗,像西莫尼尼这样的人,“干脆跟你说了吧,他仍然活在我们中间。”某种意义上说,埃科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源于他的博学通识,这自然在他的小说里有所体现,如果你读过他的《康德与鸭嘴兽》《树敌》《密涅瓦火柴盒》《帕佩撒旦阿莱佩: 流动社会纪事》等“跨文体”著作,就更可以叹为观止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博学通识,埃科得以看清假相,并且把假相产生的过程揭示给你看。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符号学家,这一身份也使得他洞悉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隐秘联系。Btr以《试刊号》为例表示,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就是在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事物中被炮制出来的,埃科要告诉读者新闻业里是怎么操作阴谋论的。“所以,读这本书有点像我们看拆西洋镜。对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看魔术的人,他会警示说,你看到的只是幻觉。而即使你知道自己看的是魔术,你可能并不清楚这魔术是怎么变出来的,埃科给你揭示了这个过程。所以说,在真假界限不是那么分明的时候,埃科不仅让你意识到有些看似真的东西,很可能是假的,他还告诉你怎么来辨别真假。”   埃科部分“跨文体”著作中文版封面 埃科部分“跨文体”著作中文版封面显而易见地,透过小说的背面,你会发现,埃科不只是停留对新闻业的批判,就像该书编辑李月敏说的,在《试刊号》里,真相是什么无所谓,新闻本身并不是问题,权力才是。而生前接受NPR电台的连线采访时,埃科也表示,这本小说触及了现代人的道德问题。埃科说,过去三十年,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听闻之后却仍然很冷漠,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而不是哪里发生了爆炸,或者死了多少人。“要知道,现在的媒体其实有些病态,周一我们读到的新闻,到了周二我们就已经忘了。这确实是悲剧。新闻并没有像它应当做的那样影响我们。” 要是从戏仿式写作的角度理解,揭露新闻业弊病的小说,理当像新闻一样往“精简”里写。当然,埃科把这部小说写得前所未有的短,也很可能只是他有意改变一下风格,他一改过去“大笔墨描写秘传、谜题或者文字游戏”的手法,脱离中世纪厚重历史与符号学的冒险,仅用短短两百页篇幅,就生动构建了一场阴谋重重的办报实验。在评论家王宏图看来,像埃科写的《傅科摆》这样的小说,事实上也可以删减成《试刊号》这样的篇幅。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删减的部分是注水的内容。以魏怡的理解,埃科注入的不管是知识,人生体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趣味,都是有营养的。“这些东西,你读起来可能觉得没单纯读故事那样痛快,但读完以后,你会享受到各种欢乐,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这些收获里,更是包含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回味。王宏图表示,读埃科的作品,你会觉得跟美国一些作家,尤其是丹·布朗的作品有比较相似的地方,比如都写的悬案,都包含了诸如圣殿骑士这样的内容,但他们的追求是完全不同的。“丹·布朗你看完一篇,不会再想看第二遍。但埃科的作品却会引你一读再读,因为里面总是有很多让你回味的地方。”  《玫瑰的名字》电影剧照 《玫瑰的名字》电影剧照事实上,埃科生前就经常被问到,《玫瑰的名字》相比《达·芬奇密码》如何,十年前访华时,他又被问到这个问题。艾柯回答说:“这不是问孔子和米老鼠有什么不同吗?丹·布朗写小说太认真了,在我那儿,也许有的只是些符号。” 但埃科写小说一样“太认真”,不同之处只在于是不一样的认真。而他说的符号,显然是有所指的,他或许真正在意的正是符号背后的东西。在《玫瑰的名字》初版时,意大利出版方一度想删掉开头的历史部分,但遭到埃科反对。他说:“修道院通常在山的高处。我希望读者能经历和我一样的磨难,直到爬上山顶。如果他们不愿这样,那他们就不是我的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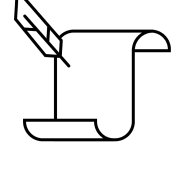 如其所言,《玫瑰的名字》的故事恰恰以一所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原本就已被异端的怀疑和僧侣的个人私欲弄得乌烟瘴气的寺院,却又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事件。一个博学多闻的圣方济格教士负责调查真相,却被卷入恐怖的犯罪中……小说除了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外,还充满了各种学问,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还涉及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等不同的思想。 如其所言,《玫瑰的名字》的故事恰恰以一所中世纪修道院为背景。原本就已被异端的怀疑和僧侣的个人私欲弄得乌烟瘴气的寺院,却又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死亡事件。一个博学多闻的圣方济格教士负责调查真相,却被卷入恐怖的犯罪中……小说除了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外,还充满了各种学问,涉及神学、政治学、历史学、犯罪学,还涉及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培根等不同的思想。《玫瑰的名字》使“翁贝托·埃科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有意思的是,关于这部小说的各种研究论文和专著源源不绝,特别是关于“玫瑰之名”的阐释几乎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这部实在是太出名了,尽管埃科还写了大量其他著作,但大众读者最关心却始终是这部侦探、哲理、历史三位一体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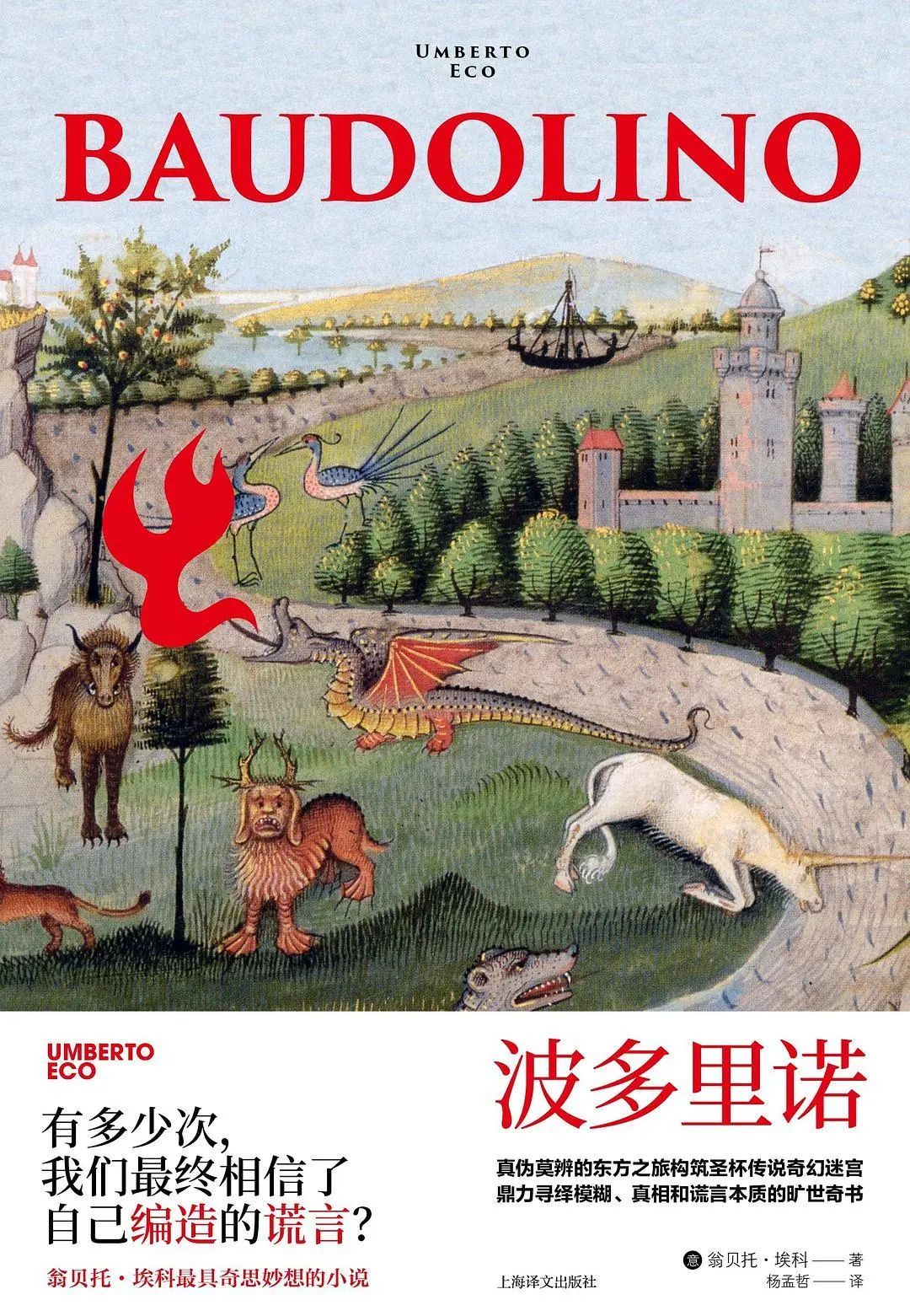 2009年,埃科访问中国,适逢他的另一本小说《波多里诺》中译本出版,但在新书媒体见面会上,记者提问的焦点,依然集中在《玫瑰的名字》上。现场有记者问他,《玫瑰的名字》和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如此相似,它们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埃科打断提问者说:“这是我来中国听到的第六个同样的问题,我从不读帕慕克,不了解他的风格,还好我的作品比他早出版。” 2009年,埃科访问中国,适逢他的另一本小说《波多里诺》中译本出版,但在新书媒体见面会上,记者提问的焦点,依然集中在《玫瑰的名字》上。现场有记者问他,《玫瑰的名字》和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如此相似,它们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埃科打断提问者说:“这是我来中国听到的第六个同样的问题,我从不读帕慕克,不了解他的风格,还好我的作品比他早出版。”有鉴于埃科的博学,读者也想知道他最喜欢哪些作家。埃科说:“通常情况下,我努力不予回答,这个问题就像是‘谁是你最喜欢的当代作家?’如果说只有一个作家对我具有最大的影响,那么我太愚蠢了。在20岁的时候,的确有对我影响很深的作家,乔伊斯是我的文学偶像。当代作家中,我比较喜欢卡尔维诺,虽然他是我的朋友。随着年龄渐长,感觉很多事情都在重复。我也读当代小说,但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差,我会被激怒,如果他们写得比我好,我也会被激怒。” 实际上,埃科有自己最喜欢的作家,那就是法国作家钱·德·奈瓦尔。他坦言,自己一生都在不断地阅读和重读奈瓦尔的《西尔薇娅》,他甚至还翻译了这部作品,因为他太热爱那些文字了。“我花了一生的时间读它,研究它,终于在几年前又翻译了它,介绍给意大利读者。奈瓦尔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的每一部作品,要么某个章节的标题,要么文中某个词汇,都直接引自奈瓦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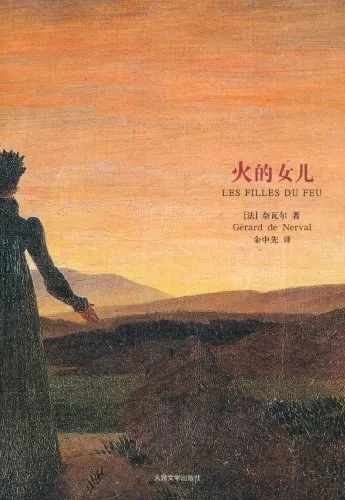 奈瓦尔与收入其代表作《西尔薇娅》的作品集《火的女儿》中文版封面 奈瓦尔与收入其代表作《西尔薇娅》的作品集《火的女儿》中文版封面那么以埃科“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见解,他读《西尔薇娅》是否也只是误读呢?这样问,不只是因为埃科写过一本名为《误读》的书,还因为埃科还有个显著的头衔:符号学家。有专家称,艾柯的符号学为大众文化、传播科学和信息理论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1971年,艾柯回到校园,为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开设了符号学课程。然而当被有关符号学的问题时,埃科显得非常无奈,因为大众读者对符号学的理解实在是太有限了。 但对于翻译问题,埃科却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说,他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翻译,因为翻译很难准确传达出另一种语言所具有的精髓。“如果说存在一种完美的语言,那纯粹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话虽如此,翻译毕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搭建起了桥梁。但近些年来,东西方在相互理解上并没有在全球化进程中加深,代沟依然存在。然而在埃科看来,要把文化交流寄希望于语言隔阂的消失,那是不现实的。埃科说:“近些年,我们发现不断有语言在消失,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要有一种语言一统天下,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尽管身份和头衔众多,埃科应对起来却是游刃有余。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日常生活方面的提问时,艾柯说,他安排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不像有些作家的生活是循规蹈矩的。他的写作没有缜密的安排,他可以在火车上、厕所里写,只要灵感来了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我觉得生活有很多间隙,就好比一个银河系,如果把星系间的空间抽掉了,银河系就会变得很小。我用的就是这些间隙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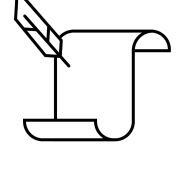 无可疑义的是,埃科也很善于在小说里利用各种“间隙空间”,并让他讲述的故事变得真假难辨。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小说《傅科摆》里,上世纪70年代的米兰,精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卡索邦博士与他的两位朋友——加拉蒙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勃和迪奥塔莱维,负责出版一套旨在赢利的“赫耳墨斯丛书”。在雪片般涌来的稿件中,在与一个个神秘学爱好者的接触过程中,一个不断重复而又歧义丛生的“圣殿骑士阴谋论”反复出现。 无可疑义的是,埃科也很善于在小说里利用各种“间隙空间”,并让他讲述的故事变得真假难辨。在他出版于1988年的小说《傅科摆》里,上世纪70年代的米兰,精通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卡索邦博士与他的两位朋友——加拉蒙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勃和迪奥塔莱维,负责出版一套旨在赢利的“赫耳墨斯丛书”。在雪片般涌来的稿件中,在与一个个神秘学爱好者的接触过程中,一个不断重复而又歧义丛生的“圣殿骑士阴谋论”反复出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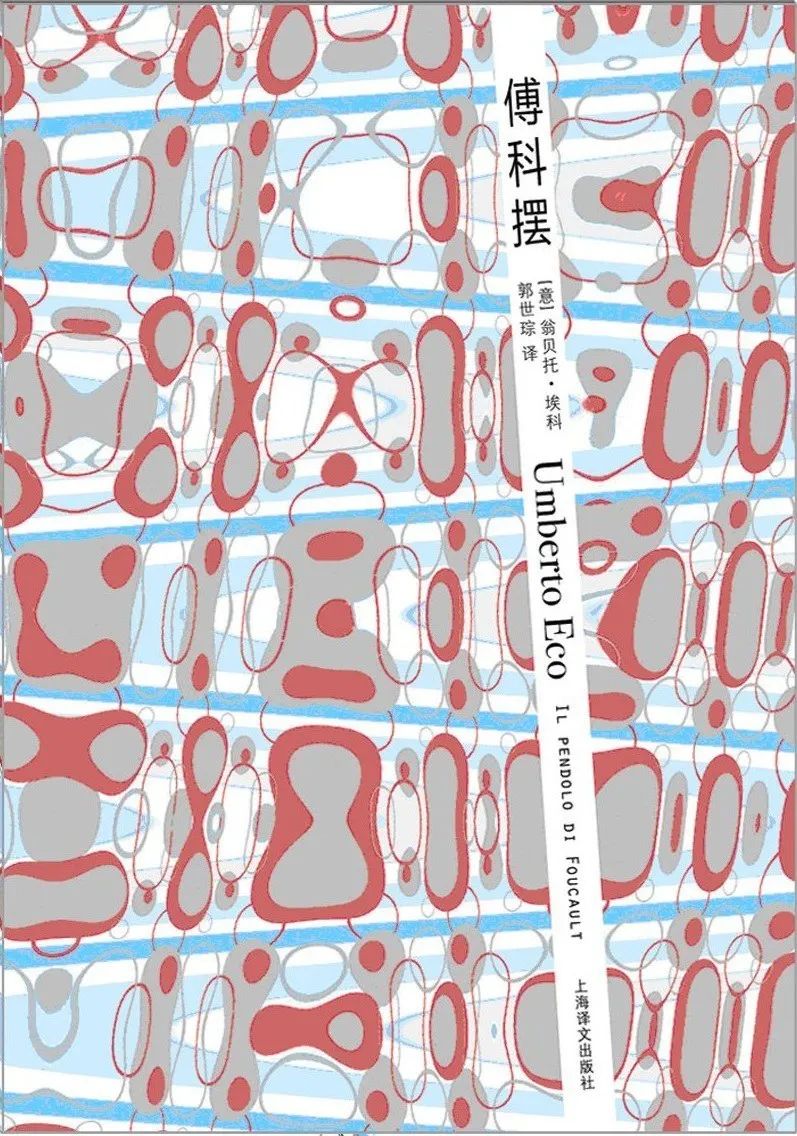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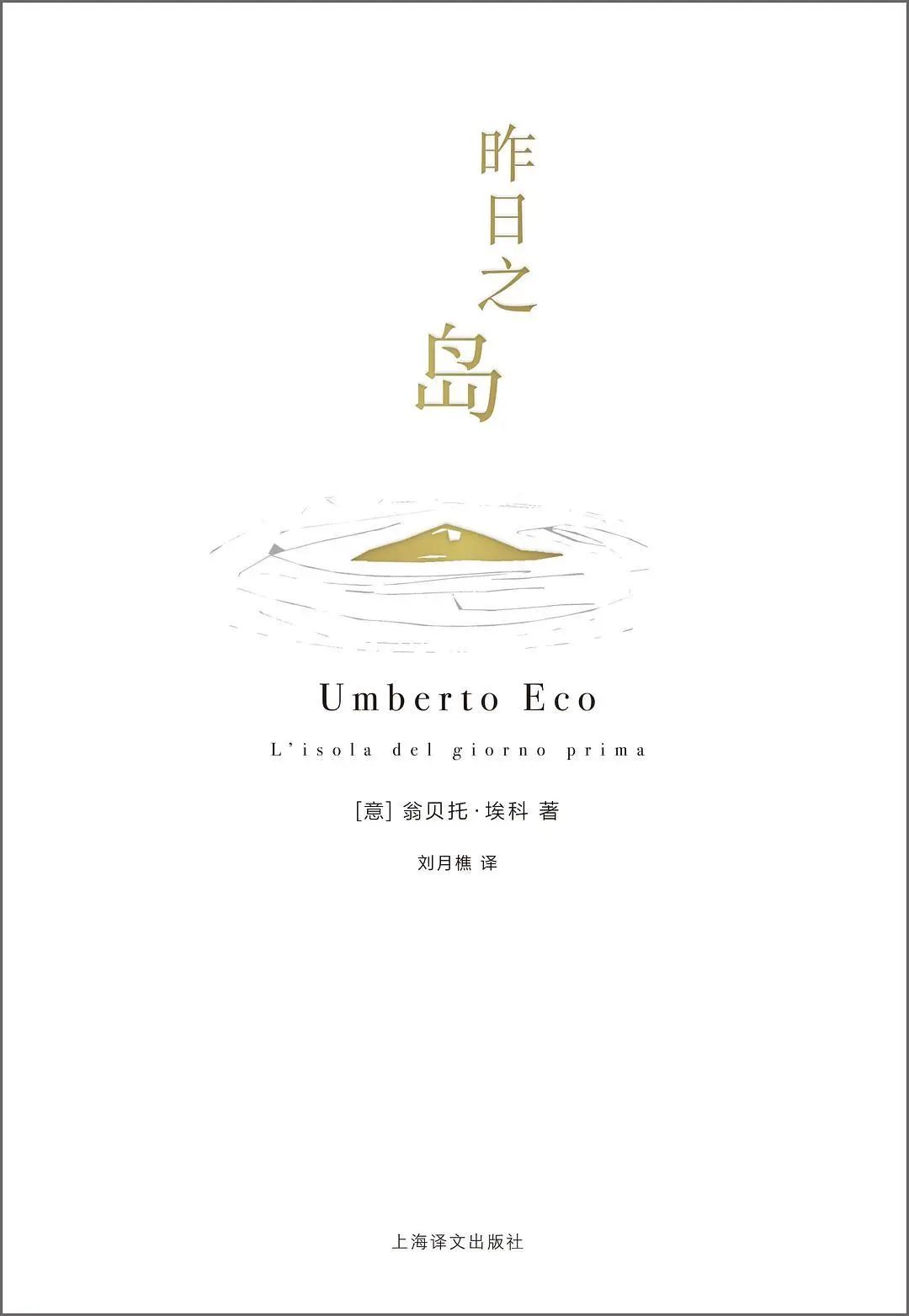 三个伙伴自诩博学、技痒难耐,本着玩笑心理,将历史中流传着的众多神秘事件、人物和社团编织成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几乎“重写”和“改写”了整部世界历史。为了让“计划”更为圆满,他们臆造了一个秘密社团:“特莱斯”。没有料到的是,神秘主义者照单全收,真的组织了“特莱斯”,追踪卡索邦和贝尔勃,并将在全世界搜寻“计划”中那张子虚乌有的“秘密地图”。 三个伙伴自诩博学、技痒难耐,本着玩笑心理,将历史中流传着的众多神秘事件、人物和社团编织成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几乎“重写”和“改写”了整部世界历史。为了让“计划”更为圆满,他们臆造了一个秘密社团:“特莱斯”。没有料到的是,神秘主义者照单全收,真的组织了“特莱斯”,追踪卡索邦和贝尔勃,并将在全世界搜寻“计划”中那张子虚乌有的“秘密地图”。随后的《昨日之岛》(1994)的故事发生在1643年,一艘担负着寻找180度经线任务的商船遇到海难,年轻人罗贝托成了惟一的幸存者,他被浪潮冲上了另一艘弃船达芙妮号。罗贝托患有疑心病、妄想症和畏光症,所以尽管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岛,但是罗贝托可望而不可及。他勉强依靠达芙妮号上残存的东西维生,每天靠书写打发时光。他写情书,写回忆、最后演变成写小说、写一切样式和内容的小说,甚至还幻想出一个弟弟“费杭德”……真实与虚构渐渐分不出界限。到最后,他离开达芙妮号,奋力游向未知的结局。 《波多里诺》(2001),同样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从十字军东征、圣杯传说,到基督教城市的兴起、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再到修道院阴谋、阿基米德的镜子、传说中的东方祭司王国。小说可谓如银河系般包罗万象。书中主人公——意大利历史名城的守护人波多里诺是一个天才的骗子,他声称自己讲述的一切都是假的,但有趣的是,他的谎言总是一出口就变成真…… 埃科的独特,正在于如有评论所说,他将学术和虚构之深浅两极共冶一炉,小说中有学术,学术中又有叙事性。也因为此,《玫瑰的名字》中文译者沈萼梅表示,和别的作家比,埃科的特别在于他维护了文人的尊严。“文人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非为了迎合谁,或者得到什么。他通过讲一个过去的故事来表达他的理念、宣告他的价值观。”有意思的是,小说名为《玫瑰的名字》,“玫瑰”只在书里出现了一次。翻译时沈萼梅甚至把书名抛到了九霄云外,译完才意识到这本书叫《玫瑰的名字》。  以“放大镜”窥探人世和洞察人性的埃科 以“放大镜”窥探人世和洞察人性的埃科倘使做点符号学的猜想,埃科在48岁的年龄,发表了平生第一部小说《玫瑰的名字》,取了这样一个书名,或许是暗示了一点什么。就像沈萼梅说的,世界上天地万物,留给人类的、历史的,不过就是个名字罢了。人也好,事也好,再伟大的最后留下的都只是名字而已。《玫瑰的名字》里写道:“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在纪念该书问世四十周年之际,或可告慰的是,埃科毕竟以“玫瑰之名”,在世上留下了他的名字,还有远要比他生命久远的作品。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书影  文学照亮生活 网站:wxb.whb.cn 邮发代号:3-22 原标题:《埃科《玫瑰的名字》问世四十周年:他总相信下一本“玫瑰”还在空白纸里 | 此刻夜读》 阅读原文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