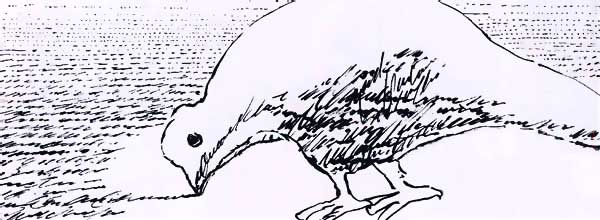10又1/2章世界史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巴恩斯老婆叫什么 › 10又1/2章世界史 |
10又1/2章世界史
|
我们审视历史程式,为的是发现给人以希望的结论,找到前进的路径。
10 1/2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 1/2 Chapters-朱利安·巴恩斯著Julian Barnes(英国) 这部小说是巴恩斯被研究和讨论得最多的作品。 全书以挪亚方舟的传说为主线,包含十章故事和一章“插曲”(所谓1/2章),或戏说《圣经》,或品评名画,或演义历史,或虚构未来,以文学的方式揭示了历史的虚构性以及虚构的历史是如何产生并变身为“真实”的,以方舟的隐喻讲述了人类在历史的汪洋中孤独漂流,寻求救赎的命运。作者在“插曲”中将挽救历史的希望寄托于爱情,它是人类最后的“方舟”。 全书如同一组拼贴画,呈现出一部寓言式的“世界史”。 10章世界史序言: 前言: 用一部小说来写世界历史,而且居然只有十卷半,这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乍一看《10 1/2卷人的历史》这个篇名,似乎作者是真的在写一部世界历史,但只用偌大的篇幅就想把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尽揽笔底,难免让人想起中国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以为这个作家是不是脑袋里出了什么大毛病,其实不然。小说通篇览后,掩卷而思,当觉是方家治“史”,若烹小鲜。 朱利安·巴恩斯绝非等闲之辈。他不仅是小说家,也是文学评论家和电视批评家。他1946年1月19日在英国莱斯特出生。父母都是法语教师。1968 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获现代语言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找到一份编纂牛津英语词典补编的工作。1972年巴恩斯成为自由作家,同时也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观察家报》撰写文学和艺术评论,并在《新政治家》和《星期日泰晤士报》兼职。1980年巴恩斯以“臭名昭著的丹·卡瓦纳”为笔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达菲》。这是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系列恐怖侦探小说中的第一部。他接着在1981年发表《小提琴城》,1985年发表《小船下水》,1987年发表《沉沦》。也是在1980年,巴恩斯第一次以自己的真名发表小说《梅特兰》。尽管评论界对小说毁誉参半,它还是在1981年获得毛姆文学奖。1982年他发表了小说《她遇到我之前》。1984年发表的《福楼拜的鹦鹉》完全是实验性的,发表时受到批评界和公众的普遍赞誉。该书列入布克奖最后入选名单并获得杰弗里·费伯纪念奖。此后,巴恩斯继续发表一系列小说:《凝视太阳》(1986);《10 1/2卷人的历史》(1989);《有事好商量》 (1991);《豪猪》(1992);《穿过海峡》(1996);《英格兰,英格兰》 (1998)。他的最新小说《爱及其他》(2000)又获得布克奖提名——在这些小说创作中,巴恩斯尝试了多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主题,而且都获得成功。除了这里提到的文学奖,他还在美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获得著名的文学奖。虽然巴恩斯现在是职业作家,但他仍然是一位活跃的新闻记者和专栏作家。20世纪90年代,他以《纽约人》伦敦记者的身份出现。他写的关于现代英国的报道选编结集成《伦敦来信》于1995年发表。此外,他当了一小段时间的教师,曾到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创作。直觉可以告诉你,像这样的一个作家,是不可能拿自己的创作来开玩笑的。他要用10 1/2卷的篇幅来写世界历史,那么世界历史就肯定可以用10 1/2卷的篇幅来描述。这不取决于他选择的题材,而取决于他表现题材的方式。 以文学的方式来写世界历史,这本身就意味着世界历史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成了“文学”。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表达系统。当世界历史被做出文学的处理之后,“历史”所发生的演变决不仅仅是真实与虚构的区别,可能还有现象与本质、体例与编排方式等方面的区别。当你带着好奇心把这部小说读完,不难发现它既不是一部按年代顺序写的编年史,也不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小说。书中有虚构也有事实,有散文、小说,也有随笔。全书10 1/2卷,看起来是互不相干,各自独立,或者说像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但细读起来它又是一个整体,小说中一再出现的挪亚方舟以及方舟的变体成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意象和情节主线。而正是这个贯穿于小说始终的基本意象和情节主线,概括了人类生存的本质,概括了一部世界历史。 朱利安·巴恩斯选择挪亚方舟来作为一个具有极高概括性的形象,显然包含着西方作家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相当普遍的救赎主题。在洪水滔天的世界性灾难面前,挪亚方舟的意义当然不只是在于所救出的那些人和动物,而是人类这个整体,以及对后来的历史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10 1/2卷人的历史》中,曾在第一卷出现的挪亚方舟到第二卷变成了恐怖主义者劫持的旅游船,到第三卷则变成主教的宝座,到第四卷变成一个女子所乘的一艘小船,到第五卷变成法国护卫舰梅杜萨号,后来又变成籍里柯画中的梅杜萨之筏;在第六卷,方舟残骸变成一位爱尔兰的女子1840年参拜圣地阿勒山的理由,在第七卷又成了泰坦尼克号、鲸鱼和圣路易号,在第八卷是电影演员拍戏乘的木筏。在《插曲》中,“爱情是许诺之地,是一条两人借以逃脱洪水的方舟”。第九卷出现了一座方舟外形的教堂,一位宇航员似乎得到了神谕,于1977年到阿勒山寻找挪亚方舟。如果说爱情是一条两人借以逃脱洪水的方舟,那么在第十卷,“我”梦里的天堂也许正是现代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方舟。朱利安·巴恩斯试图以方舟来概括一部世界历史的意图是再明显不过了。方舟和方舟的变体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一再出现,并与人类的命运密切关联,它与死亡、灾难、救赎、爱情、精神追寻等人类的生存问题构成一幅幅高度概括化了的历史图景,正是整部世界历史迄今为止最基本的展开方式。 从叙事手法上看,全书各卷都有不同的叙述者。读者可以听到许多不同的声音,了解到他们各自叙述的不同历史。他们所叙述的历史没有一个是绝对权威的,也没有一个是绝对可靠的。这正体现了巴恩斯小说的主题:历史是不可靠的。第一卷《偷渡客》,作者以偷渡到挪亚方舟上的七只木蠹为第一人称叙事者,以十分不敬的口气讲述一段与《圣经》完全不同的人类初始历史。它们把挪亚描绘成一个活了七百多年的贪酒老无赖,“他是个怪物,是个虚荣的老昏君,一半的时间讨好上帝,另一半时间拿我们出气。”上帝是个暴君,挪亚酗酒是上帝造成的。《圣经》中蛇的故事“只是亚当的黑色宣传”,而且“挪亚——或者说是挪亚的上帝——宣布动物分为两个等级: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洁净动物允许七个上方舟,不洁净的上两个”。这正是人类社会不公平与分裂不和的开始。第二卷《不速之客》以第三人称叙事,语言也比第一卷更正式,更传统。在这里世界历史成了弗兰克林·休斯个人编撰的历史,“谁也搞不清楚他的学识专长是什么,但他却在考古、历史和比较文化几个学术界里漫游。他最拿手时下的典故引喻,把死透了的题目再搬出来,让它们在一般电视观众眼前活起来,像什么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海盗藏在东英格兰的珍宝,希律的宫殿,等等”。在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劫持旅游船的戏剧性事件中,休斯曾为了保护女友和阿拉伯人达成一笔交易,可是“那个领头的和他的副手都没活下来,所以,不管弗兰克林·休斯怎样解释,找不到见证人证实他和阿拉伯人达成的交易。特里西娅·梅特兰莫名其妙地做了几个小时的爱尔兰人,在弗兰克林·休斯作宣讲时,她将戒指套回原先那个手指,她再也没有跟他讲话”。这也说明历史的真实性有的时候是讲不清楚的。第三卷《宗教战争》根据的是E.P.伊凡斯1906年著《动物的刑事诉讼和死刑》一书中所描述的法律程序和案例。也是用第三人称,模仿历史手稿的手法,转述法国贝藏松教区居民状告木蠹的庭审记录,由两位律师各自按自己的观点叙述历史,所用语言多是宗教和法律方面的。然而,辩词是翻译的,不完整的。译者注中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由各个律师的书记员执笔的原始提案,而为第三方所作,也许是一个法庭官员,他可能省略了辩词中的一些段落。”这再一次说明:历史总是在某种转述中改变面貌,没有一种转述可以声称是完全可靠的。第四卷《幸存者》虚构一个女人为逃离遭受核蹂躏的西方而作的一次疯狂的海上旅行,交替使用第三和第一人称叙事,究竟应该相信谁说的历史呢?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历史是扑朔迷离的。第五卷《海难》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详细叙述法国护卫舰“梅杜萨”号1816年遇难的情况,一部分分析籍里柯名画《梅杜萨之筏》,仍用第三人称叙述。在分析籍里柯名画时,作者评论说,“画作斩断了历史的锚链”,“灾难变成艺术”,将“木筏上极度痛苦的瞬间,选做题材,经过改造,通过艺术演绎,变成一幅有力度和深度的图画,再上光、装帧、镶玻璃,悬挂在著名的美术展馆内,用于阐释我们的人类状况,固定不动,最终地,永远在那儿。这就是我们拥有的?”把历史的叙述演变成艺术的叙述,这是另一种改造历史的手法。在这个被艺术化了的历史画面中,真正的“历史 ”已经所剩无几了。第六卷《山岳》虚构一位爱尔兰女子1840年参拜圣地阿勒山并死在那里的故事,还是第三人称叙述,在这里现实和《圣经》传说交织在一起。“凡事都有两种解释,每种解释都要借助于信仰,给我们自由意志就是为了让我们在两者之间选择。以后的许多年里,洛根小姐对这道难题百思不得其解。”在这里,历史又与信仰、自由意志等人类的精神活动关联在一起。经过了人类精神活动的熔炼与锻造,历史更是成了精神性的产品。 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说他的熔炼与锻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呢?第七卷《三个简单的故事》,第一个故事讲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我过去常常把编造出来的板球得分告诉他。”这位年轻人可以杜撰历史。“那年秋天,我在学院宿舍卧室兼起居室的镜子上嵌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生活是一场骗局,世上万事都是这样,我过去曾这样想过,现在看来就是这样。’比斯利的例子提供了确证:泰坦尼克号的英雄在毛毯上作假,是个异装癖骗子;这么看来,我报给他虚假的板球得分是很合适而有理的。从更大范围上讲,理论家们认为,生活的本意是适者生存:比斯利的虚伪难道不是证明了‘适者’只不过是最狡猾的人吗?英雄们、具有卫士美德的坚贞可靠的人们、具有良好家世和教养的人们,甚至船长(特别是船长)——都表现高尚地与船同沉大海;而懦弱胆怯的、惊慌失措的、欺诈蒙骗的都能找到理由躲进救生船里。这难道不是典型地证明了人类的基因库是如何不断地恶化,坏血统如何排斥好血统?”劳伦斯 ·比斯利想挤进重现泰坦尼克号下沉的电影中充当群众演员,结果被导演赶出来,“于是,劳伦斯·比斯利发现自己一生中第二次赶在泰坦尼克号下沉之前离船而去”。历史又重演了,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第二个故事可谓《圣经》故事新编,讲约拿和1891年的一个水手,他们都被鲸鱼吞下过。这里也是用第三人称叙述,然而这约拿被鲸鱼吞进肚子的故事“就像差不多整本《旧约》的内容一样,哪儿也不见自由意志,简直害死人——连自由意志的幻觉都没有。上帝把所有的牌都抓在手里,不管玩什么花招都是他赢”。可是“我们知道怎样区分神话和现实,因为我们很成熟老练”。然而历史又会重演,“1891年8月25日,东方之星号船上三十五岁的水手詹姆斯 ·巴特利在福克兰群岛海域被一条巨头鲸吞吃”的故事又使“神话会变成现实,不管我们持什么样的怀疑态度”。第三个故事讲1939年圣路易斯号上的犹太乘客设法逃离纳粹德国的悲剧,素材取自戈登·托马斯和麦克斯·摩根 -威茨合著的《亡命之旅》,用第三人称,以史实报道的形式来写。历史在这里又一次重演,又要把人分为洁净和不洁净:“圣路易斯号轮本来就不打算扔下九百三十七个移民之后空船离开哈瓦那。大约有另外二百五十个乘客买好了回程航班的船票,经由里斯本去汉堡。有一种建议是,至少可以让二百五十个犹太人下船,给岸上那些乘客腾出地方来。可是,你又怎么挑选出二百五十个准许走下方舟的人来?谁来分开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是用抽签的办法吗?”在这个世界里人的命运捉摸不定,圣路易斯号上有多少人活下来也没人能说准:“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圣路易斯轮上的乘客们陷入和全欧洲犹太人同样的命运。他们的运气是好是坏取决于他们被分派到哪个国家。有多少人活下来也没一个准数。”因此,在历史记载中,常常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说法。第八卷《逆流而上》是关于现代电影演员在委内瑞拉的丛林拍摄外景的故事,用第一人称,以书信和电报形式叙事。查利拍的电影是要重现两位牧师逆流而上深入丛林传教的故事,然而“我的绳子拉住了,马特的绳子断了。就是这么回事,算我命大”。历史又重演了,人的命运捉摸不定。《插曲》可谓一篇爱的随笔,用第一人称,像是巴恩斯本人以亲切、诚恳的语气倾诉心声,发表自己对爱情和世界历史的看法。其中提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历史时说,“出发前曾经许诺,第一个看到新大陆的人可以得到一万个金币的奖赏。本来一个普通水手赢得了这份赏金,但等到船队返回之后,哥伦布却自己领了赏金(鸽子还在把乌鸦排挤在历史之外)。那个水手失望之下去了摩洛哥,据说他在那儿成了一个叛逆者。1493是个有意思的年份。”这个普通水手的命运实际上成了对官方的历史或人们已经接受的历史的一次辛辣嘲讽。所以,“历史并不是发生了的事情。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对我们说的一套。”第九卷又是一个虚构的探险,叙述一位宇航员在1977年到阿勒山寻找挪亚方舟,用第三人称讲述,但在开头和结尾都是把读者称做 “你”,涉及朝鲜战争、广岛原子弹袭击、莱特兄弟的飞行,直到人类登月的世界历史。作家所选择的都是人类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却用一个宇航员的视角,以及与读者对话的形式,使得历史在这里被个人化了。第十卷的主角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前面的章节里巴恩斯一直在回顾历史,可是他无法理解历史,现在又展望未来,做了一个梦,想像死后会怎样,同样也感到迷惘。“我”在梦中来到一个现代消费者的天堂,“一切都是非常舒心的:购物,高尔夫,做爱,会见名人,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永生不死。”可是“ 过一段时间之后,一直要什么就有什么,跟一直要什么就没什么二者相差无几了”。“后来,他们都选择死?”结尾一句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梦见我醒了。这是最老掉牙的梦了,而我才做了这梦。” 在《10 1/2卷人的历史》中,巴恩斯采用了各种叙述人称,采用了各种引用材料的方式,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视角,甚至采用了各种不同的笔调来写世界历史。毫无疑问,巴恩斯处理历史的方法是非传统的。他认为我们不能相信当权者和权威讲述的历史,不能相信官方和已被人接受的历史,不能相信宣传。我们应该考虑到那些遭受过历史磨难的人的困境。“我们大家都知道,客观真实是无法得到的,某一事件发生时,我们会有众多的主观真实,经过我们评点之后编成历史,编成某种在上帝看来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这一上帝眼里的版本是虚假的——可爱诱人但毫无可能的虚假,就像中世纪那些绘画,表现基督受难的各个阶段在画中的各个部分同时发生。”实际上不同的叙事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会说出不同的历史。“你黑暗中怎样偎依拥抱决定了你怎样看待世界历史。就这么简单。”“世界历史?就是一些回荡在黑暗中的嗓音。”“我们编造出故事来掩盖我们不知道或者不能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一些事情真相,围绕这些事实编织新的故事。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抚慰性的编造功夫得以减缓;我们称之为历史。”巴恩斯还要我们注意到历史是在不断循环重演,比如从方舟到阿拉伯恐怖主义分子劫持的旅游船,到遇难的梅杜萨号,到犹太人乘的游轮,以及爱尔兰女子乘的小船,我们看到人们总是在茫茫的大水中漂流挣扎。我们总是在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为什么?我们不能再让希特勒这样的野心家上台,可是我们还是让这种人上台了。“历史会不会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不对,这种过程过于宏大,过于考究。历史只是打个嗝,我们又尝到它多少个世纪前咽下的生洋葱三明治的味道。”在巴恩斯的小说中很少有具体的日期,在《插曲》中他说他恨日期,“年代日期并不说真话。它们对我们大声吆喝——左,右,左,右,把它们捡起来吧,你们这些可怜虫。它们想让我们以为,我们总是在进步,总是在前进。”“我们让那些年代日期骑在我们头上。”不过他同时又称道历史,因为“历史有的是时间,时间和科学。不管我们怎么拼命涂改我们早先的思想,历史总有办法解读。” 除了讨论历史的性质,巴恩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讨论爱的性质。这是从救赎的主题引申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副主题。通过爱来拯救人类于各种困境,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在这个方面已经有过太多的经典。巴恩斯好像也不能越过这一点。关于爱的主题几乎每卷都谈到,但作者比较集中地谈爱的问题还是通过《插曲》中叙事者坦率而朴实的独白。首先他认为爱是神秘的,他引用加拿大作家梅维斯·加兰特的话说:“关于夫妻实情的奥秘几乎是我们仅剩的真正的谜,如果连这个谜也被我们穷尽,就再也不需要文学了——真是那样,也不需要爱情了。”接着他又对菲利普·拉金的诗句:“ 我们留存后世的是爱情”表示怀疑。他要“对这一华彩诗句设问:这是真的吗?我们留存后世的是爱情吗?”他认为,“拉金身边留存的不会是爱情,而是他的诗。”不过他还是确信“我爱你”这几个词“是堂皇的字眼,我们必须确保自己配得上它们”。“男人会说‘我爱你’,用意是叫女人上床;女人会说‘我爱你’,用意是叫男人娶她们;二者都会说‘我爱你’,目的是为了抵御恐惧,为了通过语言使自己相信真有其事,为了使自己确信做出的许诺已经实现,为了欺骗自己以为许诺还没消失。我们要留心这类用法。 ‘我爱你’不应该弥漫世间,成为通货和股份交易,为我们获取利润。如果我们允许,它就会这么做。”他还嘲笑女权主义者和大男子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在动物王国里寻找无私行为的范例,看到此处彼处雄性动物做着被人类社会视为‘女性’的工作。想想大企鹅吧!孵蛋的是公企鹅,把蛋放在脚上带着走,用自己的下腹部包裹好几个月,使其免受南极的严寒天气……是啊,大男子主义者答道,那公海象又怎样呢?整天价就在海滩上到处躺着,看到母海象,见一个就操一个。遗憾的是,海象的行为比公企鹅的更带普遍性,这看来确属真实。像我这样了解自己这一性别的人,我倾向于对公企鹅的动机持怀疑态度。公企鹅可能是这样盘算的,如果你要在南极呆上好几年,那么,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在家孵蛋,而把母企鹅派出去到冰冷的水里逮鱼。它这样安排事情可能就是为自己图方便。”对人类之爱的怀疑与责问,构成了救赎的重要一翼。那种试图以泛爱来规范人类、拯救人类的想法,曾经十分流行,但却没能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真正发挥作用。在更多的时候,那只是人的为了自己获取利益的工具而已。 在巴恩斯看来爱情并不是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他几次提到“心脏不是心形的”。“心脏不是心形的,这是我们的问题之一。我们难道不是想像有某种巧妙的两瓣合一体,其形状体现了爱情如何将两个各自分开的一半融合为一个整体吗?”其实,“这个器官沉甸甸、胖墩墩、血淋淋,紧凑密实,像个凶猛的拳头。这真东西可不像教科书里的地铁图,而是秘而不宣、含而不露。”“心脏也从来就不是心形的。”它不是我们正常想像的那样,那么,爱情正常吗?“从统计学上看,当然是不正常。”他建议人们看看婚礼照片:“婚礼照片上那些有意思的脸并不是新郎和新娘的脸,而是簇拥四周的宾客们的脸:新娘的妹妹(这终身大事会不会临到我头上?),新郎的兄长( 她会不会冷落他,就像那贱货冷落我?),新娘的母亲(这真让我想起当年) ,新郎的父亲(要是这小子知道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要是我那时知道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就好了),牧师(奇怪的是,就连张口结舌的人也会受这些古老誓词的感染而变得能说会道),皱眉头的青春少年(他们要结婚做什么? ),等等不一而足。当中的这一对处于一种非同小可的不正常状态;可是跟他们这么讲试试看。他们的状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觉更加正常。他们都对对方说这才是正常的,这之前的所有时光,我们曾经以为是正常的,其实根本就不正常。” 既然爱是不正常的,爱为什么又这么重要呢?巴恩斯说,“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要爱。因为世界历史没有爱便荒诞无稽,这样的世界历史只停留在刚建造一半的爱的房屋前,将它平夷为碎石瓦砾。世界历史若没有爱就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他认为“宗教和艺术必须让位于爱情。爱情赋予我们以人性,还赋予我们以玄想。爱情给予我们许多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 “爱还能做什么?如果我们在推销它,我们最好点明它是公民美德的出发点。你要爱某个人就不能没有富于想像力的同情心,就不能不学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世界。没有这种能力,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好恋人,好艺术家,或好政治家(你可以蒙混过关,但那不是我的意思)。”他还认为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爱与真是连在一起的,“那是黄金搭配。”人在爱的时候,往往能表现出真正的自我。 那么“爱情使你幸福?不对。爱情使你所爱的人幸福?不对。爱情使一切变好?完全不对”。“后来,我认清了我所认为的爱情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当做一种活力。我的爱情促使她幸福:她的爱情促使我幸福:这还能有错?就是错了;这样就造成一种错误的观念模式。这就寓意着,爱情是一根变幻魔杖,能解开错综复杂的死结,能让大礼帽填满手帕,能在空中变出翩翩的白鸽。但是,这种模式不是来自魔术!而是来自粒子物理。我的爱情没有,也无法使她幸福;我的爱情只能释放出她内心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一生已爱过两次(这在我看来够多的了),一次幸福,一次不幸福。正是那次不幸福的爱给了我最多有关爱情实质的启示——但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很多年之后。”正是这种亲身体验使他感受到“爱情给人昂首挺胸的信心。你感觉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挺挺地站立起来;只要这种感觉还在,你就无所不能,你可以对付整个世界。(我们是否可以弄清这点区别:爱情增强信心,而性占有只是扩张自我?)再者,爱情让人看得更清:它是眼球的雨刮器。 “爱使我们看到真,把说真话当做我们的责任。”可是“如果总统连自己的裤子拉链都锁不紧,他还有权来统治我们吗?如果社会公仆有外遇而瞒着老婆,他是不是更有可能欺骗选民?”巴恩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观点,不然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克林顿在发生性丑闻之后没有被赶下台:“以我自己来说,我宁可由一个奸夫,某个好色的流氓来统治,也不愿由一个正经八百的光棍或裤子拉链锁紧的配偶来统治。因为罪犯往往专门从事某些方面的犯罪,因此腐败政客通常在干腐败勾当时也各有专长:淫猥恶棍专搞淫乱放荡,受贿者专搞贪污受贿。这么一来,推选那些已被证实是奸夫的人,而不是把他们从公众生活中排斥出去,就更讲得通了。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正好相反,我们需要张扬他们的罪过。 但是,通过利用这种有用的情感,我们把他们的罪恶限制在贪色范围内,从而造就他们诚实正直的政德作为补偿。” 心非心形,爱情是捉摸不定的。“我不知道审慎的爱和草率的爱哪一种更好些,阔绰富有的爱和一文不名的爱哪一种更可靠,异性的爱和同性的爱哪一种更性感,婚内的爱和婚外的爱哪一种更强烈。我可能很想开导你们,但这不是咨询专栏。”虽说不是咨询专栏,巴恩斯却又劝诫世人:“我们必须信奉它,否则我们就完了。我们可能得不到它,或者我们可能得到它而发现它使得我们不幸福;我们还是必须信奉它。”史非史实,历史是不可靠的。“但是,在知道这一点的同时,我们还是必须相信,客观真实是可以得到的;或者我们必须相信它99%可以得到,或者说,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必须相信43%的客观真实总比41%的客观真实好。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完了,我们就陷入模棱两可,我们就对不同版本的谎言不分彼此同样看待,我们就在所有这些困惑面前举手投降,我们就承认胜利者不仅有权获得战利品,而且有权控制真相。”“否则我们就只好向世界历史缴械投降,向别的什么人的真相缴械投降。” 《10 1/2卷人的历史》确实是一本奇怪的小说。它在表达作家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时充满了怀疑主义的态度,对历史,对爱这些在一般人看来是“早有公论”的思考对象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当作家把真实与虚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精神、灾难与拯救、爱情与死亡等都囊括于小说之中,当作家把宗教传说、故事新编、历史记载、个人叙述等都拼贴于小说之中时,这种斑驳陆离的形态在带有后现代文学的显著特征之同时,也构成了巴恩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感知和体验的态度。有意思的是,巴恩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在运用后现代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写小说。 后记: 第三章根据的是E.P.伊凡斯一九○六年著《动物的刑事诉讼和死刑》一书中所描述的法律程序和案例。第五卷第一部分中的素材和语言取自萨维尼和科里亚合著《塞内加尔远征记》一书一八一八年伦敦译本;第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洛伦茨·艾特纳的典范之作《籍里柯:其生平和作品》(奥毕斯一九八二年版)。第七卷第三部分的素材取自戈登·托马斯和麦克斯·摩根-威茨合著的《亡命之旅》(霍德一九七四年版)。我感谢丽贝卡·约翰在研究方面的大力帮助;感谢安尼塔·布鲁克纳和霍华德·霍奇金审阅本书有关艺术史方面的内容;感谢里克·奇尔斯和杰伊·麦金纳尼审阅本书有关美国方面的内容;感谢杰基·戴维斯博士对本书中有关外科手术方面的内容提供的帮助;感谢阿兰·霍华德、盖伦· 斯特劳逊和雷德蒙·奥汉隆;还要感谢赫米奥那·李。 文摘: 他们把巨大的河马象连同犀牛、河马和大象都关在舱内。用它们来压舱倒是个合情合理的主意,不过你可以想象那股恶臭。也没人去打扫畜舍。男人们轮班喂食已忙得不可开交,而他们的女人又太娇贵,其实在那些动物不断跃动的火舌发出的臭气中,她们身上的味道跟我们一样难闻。所以要打扫畜舍,就只有我们自己来了。每隔几个月他们用绞盘吊起后甲板的厚舱盖,放进清垢鸟。不过,先要把臭气放出去,没有几个愿意去开盖的。七八只不太讲究的小鸟先在舱盖四周小心翼翼地扑腾一会,然后一个猛子扎进去。我记不得这些鸟叫什么,事实上,其中一种已经是绝种的了,不过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一种。你有没有见过河马张大嘴,伶俐的小鸟像口腔清洁师一般忙不迭地在它牙缝间剔垢?试着把那景象放大,画面也更加龌龊,你就可以想见了。我并不是一个很容易恶心呕吐的人,但一看到那甲板下的境况也会毛骨悚然:一长溜两眼眯斜的怪兽在阴沟洞里让人修剪指甲。 方舟上纪律严明,这是第一点要强调的。这可不像你小时候在儿童室里玩彩色积木时见到的景象——一对对动物喜气洋洋,住着干净舒适的棚圈,隔着栅栏向外张望。别以为我们是在地中海游轮E玩那种令人倦怠的轮盘赌,晚餐时一个个都要衣冠楚楚。方舟上只有企鹅才穿燕尾服。要记住这是一次漫长而危险的航海,哪怕事先订好了一些规则也仍有危险。还要记住整个动物王国都在船上:你该不会把猎豹放在羚羊近旁,一跳就能够着吧?一定程度的保安措施是少不了的,采用双销锁,检查畜厩并实行宵禁,但可悲的是还有惩罚和禁闭室。头头脑脑中有人特别着迷于搜集情报,同路的就有愿意充当告密者的。说起来令人伤心,有时向当权者通风报信的事还相当普遍。我们那只方舟可不是什么自然保护区,有时倒更像囚船。 说到这,我意识到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你们这一族有自己百讲不厌的说法,连怀疑论者都被迷住了,而动物们也有许多浪漫的神话故事。但它们毕竟不会惹是生非吧?它们被当做英雄,它们无一例外可将自己的宗族谱系一直追溯到方舟,有这等荣耀,何苦还要惹是生非。它们被选中,经历磨难而存活下来,因此它们掩饰难堪的往事,为省事省心而淡忘也不足为奇。可我就不在此限。从来没人选中我。事实上,我和其他几种动物都属特意不选的。我是个偷渡客,也存活下来,又逃离(离舟一点不比登舟容易),而且活得很好。我同其余的动物社会有点两样,它们还会重聚怀旧,有些从不心存芥蒂的动物甚至还办个老水手俱乐部。我回首那次航海绝不感到有什么义务,也不会因感恩戴德而歪曲真相。我的说法你尽管相信。 你大概知道“方舟”不只是一条船吧?这是我们用来称呼整个船队的名字(你不能指望把整个动物王国塞进长不过三百肘尺的东西)。雨下了四十个日日夜夜,是吗?喔,当然不是这么回事——要是这样,那就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英格兰夏天了。不是四十个日日夜夜,按我的算法是下了一年半。 大水淹没世界一百五十天,是吗?应该把这个数字加到大约四年。如此等等。你们这一族算日期总是不行。我看问题出在你们对七的倍数特有的癖好。 方舟起初有八条船:挪亚的大帆船拖一条储藏船,四条稍微小一些的船由挪亚的几个儿子各任船长,之后是医护船,保持一定安全距离(挪亚一家对疾病有本能的恐惧)。第八条船一时间让人迷惑不解:这是一条灵巧的单桅小帆船,整条船后部檀香木上镶金嵌银,行船时溜须拍马似的紧随含的方舟。如果你在下风,有时会闻到阵阵怪异的香水味,像是在挑逗你,有时夜间暴风雨缓和时,你会听到悠扬的音乐和尖笑声。这些声音令我们感到费解,因为我们以为挪亚所有儿媳都安置在各自的船上。不过这条香气四溢、笑声阵阵的船并不结实,它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中下沉了。此后几星期,含一直闷闷不乐。 接下来丢失的是储藏船。那是一个寥无星辰的夜晚,风已平息,观察哨睡眼矇眬。次日早上,挪亚旗舰后面拖着的就只剩一段被咬断的粗绳子,咬断绳子的家伙既有利牙,又能紧附湿绳而不舍。我可以告诉你,这事可引来一番相互指责,也许就因为这事,第一次有一个物种从船上消失了。此后不久,医护船也丢失了。私下议论认为这两件事有联系,含的老婆脾气不太好,就把气出在动物们身上。看来她一生制作的绣花毯都已随储藏船沉人汪洋。但没有一项指责得到证实。 但是,最糟糕的灾难要属法拉第的丢失。你熟悉含、闪和另一个名字以 J打头的,但你不一定知道法拉第吧?他是挪亚几个儿子中最年轻力壮的,当然这样一来他在家里就不是最讨人喜欢的了。他还有幽默感,至少是笑口常开,这在你们这一族通常就能说明问题了。不错,法拉第整日兴致勃勃。 有时可见他在后甲板大摇大摆地踱步,肩上一边一只鹦鹉;有时他会温柔地拍拍四足动物的屁股,动物们就会发出会心的吼叫以示回应。据说他那只方舟比别的船管得要宽松得多。可是,你看:一天早上,我们醒来发现,法拉第的船从海平面上消失了,连同五分之一的动物王国一起消失了。我想你应该喜欢那智慧鸟,喜欢它那银灰色的头和孔雀的尾;可是巢居智慧树的鸟抵御海浪的能耐一点不比花斑鼠强。法拉第的兄长们咬定是他的航海技术不行,说他把时间全花在和兽类厮混上了。他们甚至暗示可能是上帝惩罚他,因为他在还只是个八十五岁的孩子时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不管法拉第失踪的真相如何,这对你们这一族是个重大损失。他的基因本来可以帮你们的大忙。 对我们来说,这整个航海之旅是在我们得到邀请在某时到某地报到时开始的。那是我们第一次得知有这么个计划。我们对其政治背景一无所知。上帝对自己的造物发怒在我们听来是件新鲜事,我们糊里糊涂卷入其中。我们没有任何过错(你该不会真的相信那蛇的故事吧?那只是亚当的黑色宣传),可后果对我们一样严重:每样物种都被灭绝,只留一对续种,而且发配到公海,受一个活了七百多年的贪酒老无赖管制。 话就这么传开了。但跟以往一样,他们还是那德性,不对我们讲真话。 你以为地球上每种动物都有代表正好住在挪亚宫殿(哟,那位挪亚可不算穷) 附近?拉倒吧。他们只好做广告,而后从应征者中选择最佳配对。因为不想造成普遍恐慌,他们宣布组织一次结伴竞赛(类似选美比赛),像伴有专家小组加上一对慈祥老夫妇即席回答问题的那种活动,要求参赛者在某个月份到挪亚的门前报到。你可想象那一大堆的问题。首先,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性好胜,所以赴赛者弄不好都是些最热衷于争名夺利的。那些没有机灵到悟出其中奥妙的动物觉得,它们本来就不想赚一个双人免费航海豪华游,多谢啦。 挪亚和他手下一帮人也不顾及有些动物每年到时要冬眠,更不理会各种动物行动速度有快有慢这个更显而易见的道理。譬如有一只特别慢悠悠的树懒— —是个很不错的家伙,我可以发誓——还没磨蹭到树底下就被上帝复仇的怒涛卷走了。这你该怎么讲——自然淘汰?我说是专业能力所限。 老实说,事情组织得乱七八糟。挪亚建造方舟拖了工(工匠们得知没有足够舱位供他们搭乘,事情就没那么好办了),这么一来对选拔动物的事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过来一对只要看着还说得过去,就选定了——就是这么个选法,最多再瞄一眼家谱。还有,他们说是每种动物带两个,但真做起来… …有些压根就不准同行。我们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只好偷渡。不知多少动物论理论法都完全应该单独算一个物种,但没人理睬。它们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免了吧,我们已经有两个了。得了,尾巴上多几个圈,或是脊背上多几簇毛,这都算什么?你们这一种我们已经有了,抱歉。 还有些很漂亮的动物,因为没有配偶同行,也只好被留下了;也有的一大家子不肯与子女拆散,宁可死在一起;还有那医检,常常是对人身的野蛮侵扰;挪亚的栅栏围圈外一片落选动物的哀号声,彻夜可闻。等到最终搞清楚为什么要用这种装模作样的比赛来折腾我们,你能想象那种局面吗?你可以想象,少不了嫉妒和不良行为。有些高贵动物索性扬长而去,进了丛林,拒绝按照上帝和挪亚有辱尊严的条件保全性命,情愿在洪水中灭绝。对鱼类有各种尖刻和嫉羡的议论;两栖类开始洋洋自得;鸟类加紧锻炼长时间续飞能力。不时能看到有些猴类为自己制作简陋筏子。有一个星期,入选动物大院内莫名其妙地爆发了食物中毒,有些不太强壮的物种只好再来一次选拔。 P3-7 … 10又1/2章世界史书摘: 历史向来更象是多种媒体的拼贴,涂抹油彩的是粉刷滚筒,而不是鸵毛笔。 只有能看清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那些人才能生存,规律肯定是这样。 样样事情都相连,武器和噩梦。 未来在于过去。 也许这世界要用很多世纪的良好表现才能重新唤回春天和秋天。 如果你已经闭上眼睛睡觉,还要再闭眼,把噩梦关在外面。 我恨他们这样,没办法对付的事情就假装没听见。 这就是命运最无情的打击:太阳正在升起,但不是为了你。 福楼拜说:“我们一来到这世界就开始一点一点脱落。” 凡事都有两种解释,每种解释都要借助于信仰,给我们自由意志就是为了我们在两者之间选择。 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神话并不是叫我们对某个经过集体记忆而添油加酱、改头换面的事件追根到底;而是叫我们向前看那种将会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神话会变成现实,不管我们持什么样的怀疑态度。 他们的漂浮世界能否脱险不是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狂风怒涛,冰上暗礁。 我爱你不应该弥漫世间,成为通货和股份交易,为我们获取利润。 正是那次不幸福的爱给了我最多有关爱情实质的启示——但不是在当时,而是在很多年之后。 但你身在一辆错误的车里,停在错误的车库前,等在错误的住宅外面。这么多的麻烦当中有一项是:心脏不是心形的。 如果说,那些从别的东西中获得最大满足的人过的是空虚的生活,是装腔作势的寄居蟹,用不属于自己的贝壳包裹着在海底招摇过市,这种说法肯定不是什么“该死的谎言”。 我们能否明确这点区别:爱情增强信心,而性占有只是扩张自我。 公企鹅可能是这样盘算的,如果你要在南极呆上好几年,那么,最聪明的做法莫过于在家孵蛋,而把母企鹅派出去到冰冷的水里逮鱼。 世界历史使我们认识到战争的决定因素是新式的箭头、精明的将军、吃饱的肚子、对掠夺的期盼,而不是思乡的愁绪。 那么,爱情是不是一种和平年代冒出来的奢侈品,如同绗缝棉被?令人愉悦,复杂,但又无关紧要。 如果我们不用为爱情操心,性欲就会简单得多。婚姻就会更加直截了当——说不定还更加持久。如果我们不为爱情折腾,不为其来临而狂喜,不为其离去而恐惧。 也许爱情正因为并非必不可少才至关重要。 一张相片在一盘液体中显影。在此之前,这只是一张空白相纸,密封在不透光线的袋子里;现在它具有了功能、影像、确定性。我们赶紧把相片滑入定影盘中,固定住那个清晰而又脆弱的瞬间,使那影像更加结实,不易剥落,至少维持它几年。可是,如果你把相片掷入定影液,而药剂不起作用,又会怎样呢?这一进程,你感觉到的这种爱的动态,就不会固定下来。你有没有见过相片一直不停的显影,直到它整个变黑,那精彩的瞬间全被抹煞? 婚礼照片上那些有意思的脸并不是新郎和新娘的脸,而是簇拥在四周的宾客的脸:新娘的妹妹(这终身大事会不会临到我头上?),新郎的兄长(她会不会冷落他,就象那贱货冷落我?),新娘的母亲(这真让我想起当年),新郎的父亲(要是这小子知道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要是我那时知道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就好了),牧师(奇怪的是,就连张口结舌的人也会受到这些古老誓词的感染而变得能说会道),皱眉头的青春少年(他们要结婚做什么?),不一而足。当中的这一对处于一种非同小可的不正常状态;可是跟他们这么讲试试看。 你在黑暗中怎样偎依拥抱,决定了你怎样看待世界历史。 历史只是打个嗝,我们又尝到它多少个世纪前咽下的生洋葱三明治的味道。 人们更情愿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该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他们对天堂的期望当中,有一部分好象是别人都该下地狱。 生活是一场骗局,一切都在证明,过去我只是猜想,现在我已确定。 一直要什么就有什么,跟一直要什么就没什么二者相差无几。 这就是人生,唯一能让你丢脸的人就是你自己。 —— [英国]朱利安.巴恩斯 10 1/2章世界史书评: 用隐喻拼贴的“世界史” 对于历史的叙述,我们总是持有复杂的心态。信任它,这其中必定藏有许多精心的谬误与刻意的误导;否定吧,那我们又该相信什么呢?或许,潜入历史的幽微之处,以隐喻的方式拼贴出自己的历史文本,是与常规叙述达成的一个互文的默契。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显然也是于历史抱有质疑的态度,他选取了自己的方式,以诺亚方舟以及方舟的变体为意象,重构了巴恩斯式的“世界史”。 《10 1/2章世界史》是一个古怪的书名,但倒也直截了当地点明了巴恩斯要以10 1/2章的篇幅书写世界历史,野心勃勃且匠心独具。小说与随笔的杂糅,足可见这是一部文学化的历史,虚构与纪实之间,有一缕无形的丝线连接,表象的虚妄或可透视出本质的扎实。朱利安·巴恩斯以诺亚方舟的传说为主线,讲了十个故事和一个插曲,有对圣经故事的颠覆式书写,对现实故事的叙述,对名画成因的分析,以及未来生活的虚构。各个故事间表面互不相关,而方舟的隐喻作为一条线,将碎片拼贴出一个关于人的历史以及漂流与救赎的命运。 人的漂流的命运源于外因亦起自本性,因之既有身体的漂泊亦有精神的游荡。洪水滔天使人们避入方舟,于漫无涯际的空间中惶恐不定;而巴恩斯描述的未来,在永生不死的天堂,置身其中者在无限的时间中“一直要什么就有什么,跟一直要什么就没什么二者相差无几了”,在物质的丰裕或贫乏之间,人的精神总是摇摆无停息,较之身体或更有漂移之态势。我想,巴恩斯于此洞若观火,在此种语境下,传统历史叙述的唯一性和一元化,是大可怀疑的。 历史可能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以巴恩斯也就老实不客气地解构着先前貌似斩钉截铁口吻的煌煌“正史”。如方舟的领导者诺亚“是个怪物,是个虚荣的老昏君,一半的时间讨好上帝,另一半时间拿我们出气”;法国画家籍里柯名画《梅杜萨之筏》滤清了海难的细节,“画作斩断了历史的锚链”,静止在美术馆的墙壁上。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什么?自然还是历史,不过这历史却是残缺的、谬误的、有意或无意遮掩、修改和涂抹的。即使如我们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也曾绘声绘色地描写过历史人物的密室谈话,不免遭受后人质疑:既为密谈,汝从何知之?史书的尴尬一面正在于此,更不要说许多刻意的篡改了。难怪巴恩斯取怀疑的态度,以自己的视角解构权威化与固化的历史文本。 自然,巴恩斯也不是一味地颠覆与解构,将历史作为一个笑话来谈,他想从虚妄中寻求属于自己的隐喻。因之,在十个故事中,诺亚方舟变为恐怖主义者劫持的旅游船、主教的宝座、法国护卫舰梅杜萨号、泰坦尼克号等,虽不断变形复象,但方舟的漂流与救赎寓意贯穿始终,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际遇中与方舟的汇合或许是碎片式的,却可拼贴出一个独特的文学化的“世界史”。 将历史文学化,似乎是个蹊跷的事情,但面对客观事实的难以再得,主观意识的介入或可带来另一种真实也未可知。所以,巴恩斯重新演绎圣经故事、讲述《梅杜萨之筏》的形成,乃至虚构未来的故事,解构或幻想之意昭然,在根底上却着意于重构独特的真实,虽然这是巴恩斯式的。文学化的好处还在于,我们可以不再拘泥于事物表面的现象,以不羁的想象直指历史的虚伪与精神的本真,探求人类生存景况的感知与体验,巴恩斯的碎片式拼贴即意在实现这样一个野心。 而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如朱利安·巴恩斯这样持有怀疑主义态度的作家,在对历史大表质疑与解构之后,于“插曲”(即1/2章)中,将挽救历史的希望寄托于爱情,认为这是人类最后的“方舟”,“世界历史没有爱便会陷入荒诞,没有爱就变得自高自大,野蛮残忍。”这自是作家的天真之处,亦是执着之处。爱未必能够挽救整个世界,但漂泊的心灵应可于此中觅出救赎之道,获得个体的温暖。我们对生存境遇感知的探寻在“个”与“群”之间交织出斑驳陆离的况味,于无中生有,或可开出另一种可能性。 附作者简介: 朱利安·巴恩斯(1946- ) 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生于英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他著有十余部长篇小说,其中《福楼拜的鹦鹉》最为脍灸人口,奠定了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他的创作以对历史、真实、真理和爱情的思考著称,这在《10 1/2章世界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尝试多种实验方法,打破传统的小说创作模式。他自己的小说也部部特色鲜明,风格绝不雷同。 [请保留:后时代 http://www.houshidai.com/]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