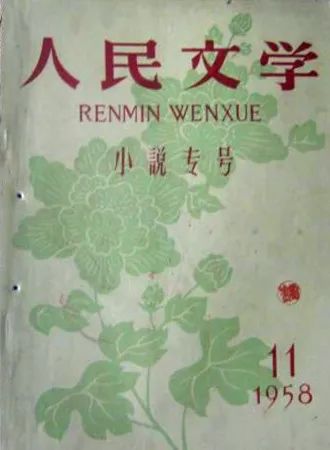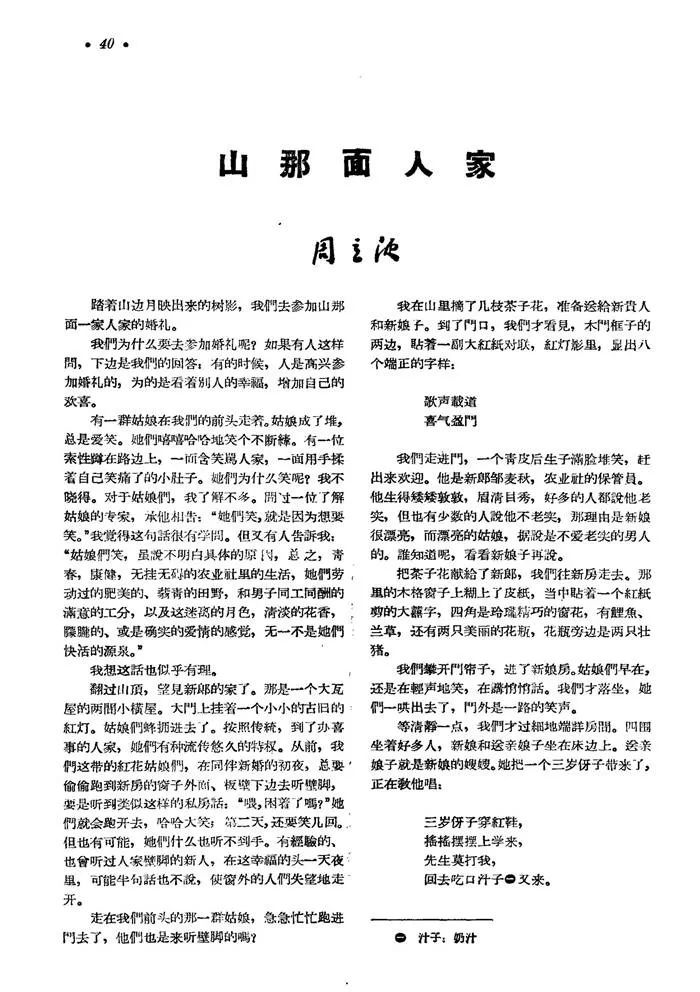【经典重读】纪念周立波诞辰111周年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周立波放出来了没有 › 【经典重读】纪念周立波诞辰111周年 |
【经典重读】纪念周立波诞辰111周年
|
周立波 (刊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11期) 踏着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我们去参加山那面一家人家的婚礼。 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婚礼呢?如果有人这样问,下边是我们的回答:有的时候,人是高兴参加婚礼的,为的是看着别人的幸福,增加自己的欢喜。 有一群姑娘在我们的前头走着。姑娘成了堆,总是爱笑。她们嘻嘻哈哈地笑个不断纤。有一位索性蹲在路边上,一面含笑骂人家,一面用手揉着自己笑痛了的小肚子。她们为什么笑呢?我不晓得。对于姑娘们,我了解不多。问过一位了解姑娘的专家,承他相告:“她们笑,就是因为想要笑。”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学问。但又有人告诉我:“姑娘们笑,虽说不明白具体的原因,总之,青春,康健,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翡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的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活的源泉。” 我想这话也似乎有理。
翻过山顶,望见新郎的家了。那是一个大瓦屋的两间小横屋。大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古旧的红灯。姑娘们蜂拥进去了。按照传统,到了办喜事的人家,她们有种流传悠久的特权。从前,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们,在同伴新婚的初夜,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板壁下边去听壁脚,要是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喂,困着了吗?”她们就会跑开去,哈哈大笑;第二天,还要笑几回。但也有可能,她们什么也听不到手。有经验的、也曾听过人家壁脚的新人,在这幸福的头一天夜里,可能半句话也不说,使窗外的人们失望地走开。 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一群姑娘,急急忙忙跑进门去了,她们也是来听壁脚的吗? 我在山里摘了几枝茶子花,准备送给新贵人和新娘子。到了门口,我们才看见,木门框子的两边,贴着一副大红纸对联,红灯影里,显出八个端正的字样: 歌声载道 喜气盈门 歌声载道 喜气盈门 我们走进门,一个青皮后生子满脸堆笑,赶出来欢迎。他是新郎邹麦秋,农业社的保管员。他生得矮矮敦敦,眉清目秀,好多的人都说他老实,但也有少数的人说他不老实,那理由是新娘很漂亮,而漂亮的姑娘,据说是不爱老实的男人的。谁知道呢,看看新娘子再说。 把茶子花献给了新郎,我们往新房走去。那里的木格窗子上糊上了皮纸,当中贴着一个红纸剪的大囍字,四角是玲珑精巧的窗花,有鲤鱼、兰草,还有两只美丽的花瓶,花瓶旁边是两只壮猪。
茶子花 我们攀开门帘子,进了新娘房。姑娘们早在,还是在轻声地笑,在讲悄悄话。我们才落座,她们一哄出去了,门外是一路的笑声。 等清静一点,我们才过细地端详房间。四围坐着好多人,新娘和送亲娘子坐在床边上。送亲娘子就是新娘的嫂嫂。她把一个三岁伢子带来了,正在教他唱: 三岁伢子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学来, 先生莫打我, 回去吃口汁子(注:奶汁)又来。 三岁伢子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学来, 先生莫打我, 回去吃口汁子(注:奶汁)又来。 我偷眼看了看新娘卜翠莲。她不蛮漂亮,但也不丑,脸模子,衣架子,都还过得去,由此可见,新郎是个又老实又不老实的角色。房间里的人都在看新娘。她很大方,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样子。她从嫂嫂怀里接过侄儿来,搔他胳肢,逗起他笑,随即抱出房间去,操了一泡尿,又抱了回来,从我身边擦过去,留下一阵淡淡的香气。 人们把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点起,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房里的陈设。床是旧床,帐子也不新;一个绣花的红缎子帐荫子也半新不旧。全部铺盖,只有两只枕头是新的。 窗前一张旧的红漆书桌上,摆了一对插蜡烛的锡烛台,还有两面长方小镜子,此外是贴了红纸剪的囍字的瓷壶和瓷碗。在这一切摆设里头最出色的是一对细瓷半裸的罗汉。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他们为什么笑呢?既是和尚,应该早已看破红尘,相信色即是空了,为什么要来参加人家的婚礼,并且这样欢喜呢? 新房里,坐在板凳上谈笑的人们中有乡长、社长、社里的兽医和他的堂客。乡长是个一本正经的男子,听见人家讲笑话,他不笑,自己的话引得人笑了,他也不笑。他非常忙,对于婚礼,本不想参加,但是邹麦秋是社里的干部,又是邻居,他不好不来。一跨进门,邹家翁妈迎上来说道: “乡长来得好,我们正缺一个为首主事的。”意思是要他主婚。 当了主婚人,他只得不走,坐在新娘房里抽烟,谈讲,等待仪式的开始。
刊发《山那面人家》的《人民文学》1958年第11期“小说专号” 社长也是个忙人,每天至少要开两个会,谈三次话,又要劳动;到夜里,回去迟了,还要挨堂客的骂。任劳任怨,他是够辛苦的了。但这一对新人的结合,他不得不来。邹麦秋是他得力的助手,他来道贺,也来帮忙,还有一个并不宣布的目的,就是要来监督他们的开销。他支给邹家五块钱现款,叫他们连茶饭,带红纸红烛,带一切花销,就用这一些,免得变成超支户。 来客当中,只有兽医的话多。他天南地北,扯了一阵,话题转到婚姻制度上。 “包办也好,免得自己去操心。”兽医说。他的漂亮堂客是包办来的,他很满意。他的脸是酒糟脸,红通通的,还有个疤子,要不靠包办,很难讨到这样的堂客。 “当然是自由好嘛。”社长的堂客是包办来的,时常骂他,引起他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社长是对的,包办不如自由好。”乡长站在社长这一边,“有首民歌,单道旧式婚姻的痛苦。” “你念一念。”社长催他。 “旧式婚姻不自由,女的哭来男的愁,哭的长江涨了水,愁的青山白了头。” “那也没有这样的厉害。”社长笑笑说。 “我们不哭也不愁。”兽医得意地看看他堂客。 “你是瞎子狗吃屎,瞎碰上的。”乡长说。“提起哭,我倒想起津市那边的风俗。”乡长低头吧口烟,没有马上说下去。 “什么风俗?”社长催问。 “那边兴哭嫁,嫁女的人家,临时要请好多人来哭,阔的请好几十个。” “请来的人不会哭,怎么办?”兽医发问。 “就是要请会哭的人嘛。在津市,有种专门替人哭嫁的男女,他们是干这行业的专家,哭起来,一数一落,有板有眼,好像唱歌,好听极了。” 窗外爆发一阵姑娘们的笑声,好久不见的她们,原来已经在练习听壁脚了。新房里的人,连新娘在内,都笑了,乡长照例没有笑。没有笑的,还有兽医的堂客。她枯起了眉毛。 “你怎么样了?”兽医连忙低头小声问。 “脑壳有点昏,心里象要呕。”漂亮堂客说。 “有喜了吧?”乡长说。 “找郎中没有?”送亲娘子问。 “她还要找?夜夜跟郎中睡一挺床。”社长笑笑说。 “看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还当社长呢。”兽医堂客说。 外边有人说:“都布置好了,请到堂屋去。”大家拥到了堂屋,送亲娘子抱着孩子,跟在新人的背后。姑娘们也都进来了。她们倚在板壁上,肩挨着肩,手拉着手,看着新娘子,咬一会耳朵,又低低地笑一阵。
堂屋上首放着扳桶、箩筐和晒簟,这些都是农业社里的东西。正当中的长方桌上,摆起两枝点亮的红烛。烛光里,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两只插了茶子花枝的瓷瓶。靠里边墙上挂一面五星红旗,贴一张毛主席肖像。 仪式开始了,主婚人就位,带领大家,向国旗和毛主席像行了一个礼,又念了县长的证书,略讲了几句,退到一边,和社长坐在一条高凳上。 司仪姑娘宣布下面一项是来宾演说。不知道是哪个排定的程序,把大家最感兴味的一宗——新娘子讲话放在末尾,人们只好怀着焦急的心情来听来宾的演说。 被邀上去演讲的本来是社长,但是他说: “还是叫新娘子讲吧。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新婚是什么昧儿,都忘记了,有什么说的?” 大家都笑了,接着是一阵鼓掌。掌声里,人们一看,走到桌边准备说话的,不是新娘,而是酒糟脸上有个疤子的兽医。他咬字道白,先从解放前后国内的形势谈起,慢慢吞吞地,带着不少的术语,把辞锋转到了国际形势。听到这里,乡长小声地跟社长说道: “我还约了一个人谈话,要先走一步,你在这里主持一下子。” “我也有事,要走。” “你不能走。都走了不好。”乡长说罢,向邹家翁妈抱歉似地点点头,起身走了。 社长只得留下来,听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就跟旁边一个办社干部说: “人家结个婚,扯什么国际国内形势罗?” “你不晓得呀,这叫八股;才讲两股,下边还长呢。”办社干部说。 “将来,应该发明一种机器,安在讲台上,爱讲空话的人一踏上去,就遍身发痒,只顾用手去搔痒,口里就讲不下去了。”社长说。 隔了半点钟,掌声又起。新娘子已经上去,兽医不见了。发辫扎着红绒绳子的新人,虽说大方,脸也通红了。她说: “各位同志,各位父老,今天晚上,我快活极了,高兴极了。” 姑娘们吃吃地笑着,口说“快活极了,高兴极了”的新娘,却没有笑容,紧张极了。她接着讲道: “我们是一年以前结婚的。” 大家起初楞住了,以后笑起来,但过了一阵,平静地一想,知道她由于兴奋,把订婚说做了结婚。新娘子又说: “今天我们结婚了,我高兴极了。”她从新蓝制服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小册子,摊给大家看一看,“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 “真不儿戏。”一个青皮后生子失声叫好。 “真是乖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后生子这样地说。他忘了自己真是个孩子。 “这才是真正的嫁妆。”老社长也不禁叹服。 “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我是过来劳动的。我在社里一定要好好生产,和他比赛。” “好呀,把邹家里比下去吧。”—个青皮后生子笑着拍手。 “我的话完了。”新娘子满脸通红,跑了下来。 “没有了吗?”有人还想听。 “说得太少了。”有人还嫌不过瘾。 “送亲娘子,请。”司仪姑娘说。 送亲娘子搂着三岁的孩子,站起来说: “我没学习,不会讲话。”说完就坐下去了,脸模子也涨得鲜红。 “要新郎公讲讲,敢不敢比?”有人提议。 “新郎公呢?” “没有影子了。”有人发现。 “跑了。”有人断定。 “跑了?为什么?” “跑到哪里去了?” “太不像话,这叫什么新郎公?” “他一定是怕比赛。” “快去找去,太不像话了,人家那边的送亲娘子还在这里。”社长说。
晚年周立波 好几十个人点着火把,拧亮手电,分几路往山里,塅里,小溪边,水塘边,到处去寻找。社长领头,寻到山里的—路,看见储藏红薯的地窖露出了灯光。 “你在这里呀,你这个家伙,你……”一个后生子差点要骂他。 “你为什么开溜?怕比赛吗?”老社长问他。 邹麦秋提着一盏小方灯,从地窖里爬了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抬抬眉毛,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与其坐冷板凳,听那些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看烂了没有?” “你呀,算是一个好的保管员,可不是—位好的新郎公。不怕爱人多心吗?”社长的话,一半是夸奖,一半是责备。 把新郎送回去以后,我们先后告辞了。踏着山边斜月映出的树影,我们各自回家去。同路来的姑娘们还没有动身。 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她们一定开始在听壁脚了,或者已经有了收获吧? 1957年11月
唐弢 (刊于《人民文学》1959年第7期) 作者有了丰富的生活,像弄潮儿熟悉水性一样熟悉他的题材,这个题材吸引着他,纠缠着他,通过思想感情的铸冶,逐渐地形成一个胚胎,然后用他自己的表现方法把它抒写出来,如果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艺术家,这种铸冶的过程也就是产生风格的过程.资产阶级批评家说艺术家的唯一本领是说谎,是善于编造,我们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艺术的生命是真实。所谓写真实,一方面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也要从思想高度上写出作者自己的感情的真实,进一步求得两者的统一。在这里,作者的世界观就起着深刻的作用。服从主观,从偏见出发,一味迁就个人情趣,这样的作品是歪曲现实的,不真实的,它的结果是个人放诞和自我扩张,谈不到什么风格。相反地,自以为忠实于客观,掩藏了个人的感情,或者对生活勉强凑合,自然主义地不加判断和掩盖倾向,这样的作品同样没有什么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还是一个不真实。风格呢,当然也谈不到。 如果说得通俗一点,不妨拿书法作个比喻。把生活当作法帖,像临摹法帖一样临摹生活,即使笔肖划似,写得再好,也不会有真正的独立的风格;反之,没有临过法帖,不讲究书法的规律——在创作上是生活的规律和艺术的规律,任意涂抹,虽然写来每人不同,或如蝌蚪,或如蚯蚓,甚至自命为野兽派或者恶魔派,能不能说他们已经像成熟的书法家或者艺术家一样,有了自己的风格呢?也不能。马克思同意布封的话:“风格是人”,因为人的个性是组成风格的二个重要的条件,然而个性并不等于风格,风格是自然形成的,但不可能不求而得,也不可能一蹴即就。所谓成熟,指的是作者在思想上、艺术上、性格上、趣味上都有一定的锻炼,主观世界的感情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于客观世界的生活的真实。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感情,因为由我看来,一个作家不仅要有正确的思想,还要进一步让这种思想渗透到感情里去,作者灌注在作品里的感情,爱什么,恨什么,往往不只是依靠单一的正确的思想,而是根源于他的整个世界观——从思想到感情的全盘的变化。布封又说:“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论文笔》,《布封文钞》第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从这点上说来,尽管组成风格的因素很多,然而首先离不开在世界观指导下作者感情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联系。
唐弢(1913-1992),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和文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立波的短篇。 除了长篇《山乡巨变》外,立波在这一时期里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就以《禾场上》(见一九五六年《人民日报》)、《山那面人家》(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号《人民文学》)、《北京来客》(见一九五九年六月号《人民文学》)三篇而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是有意识地在尝试着一种新的风格:淳朴、简练、清新、隽永。从选材上,从表现方法上,从语言的朴素、色彩的明远、调子的悠徐上,都给人以一种不事雕琢,独具意趣,恰似古人说的“从绚烂到平淡”的感觉。然而立波的风格的特征,却决不止于“平淡”,而是通过平淡的故事,寄托了深厚的感情,字里行间,处处跳跃着发自作者内心的对生活的喜悦。不错,作者没有直接表达他的激动,他的思想深入到故事的内容,使感情的真实和生活的的真实和谐地糅合在一起,既写出了客观的现实,也写出了作者的感情。三个短篇的故事并不惊险,色彩并不绚丽,情调并不强烈,他写的是最平凡同时又是最根本的变化,伸入日常生活深处的变化。隐藏在纸墨背后的作者的感情,我看还是十分激动的,三篇中的任何一个短篇,就其内容实质来说,都是作者一往情深的对社会主义的颂歌。 我说得过分了吗?不!我没有说得过分。 就以《山那面人家》来说,当然,小说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作者在渲染生活情趣时,某些笔触,匠心中还不免透露做作,或多或少地留下了斧凿的痕迹。例如:一开头说姑娘们为什么要笑,问了一位“专家”,说是“她们笑,就是因为想要笑”。因此就——“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学问”;新房里摆着一对细瓷罗汉,头上戴了“红星帽子”,于是便——“我想,他们一定已经改造了。”这种地方显得作者是在故意缠弄笔头,读起来趣味不高。但在其它方面,整个小说的调子是和谐的,通过生动的细节的描写,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东西,每一段情节,都蘸满了作者的喜悦的感情,创造了掩盖不住的欢乐的气氛。如果说,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激情,作者曾经淋漓尽致地歌颂了土地改革,展开了绚烂多彩的长卷——《暴风骤雨》;现在,同样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激情,作者却余味无穷地赞美了农村新气象,在《山乡巨变》之外,又提供了安详轻松的小幅。这是生活的继续,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作者为自己的艺术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建立了新的风格。生活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永远是开广的,读到这些短篇的时候使我想起了门采尔·阿道夫。门采尔是德国十九世纪绘画全盛时期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和同时代许多画家比起来,出现在门采尔笔下的是一个非常丰富和无比深邃的时代,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足以束缚画家的思想。门采尔描绘了历史的重大事件:他为弗朗茨·库格雷尔的《腓列特二世的史实》一书制作了蜚声艺苑的插图,在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中创造了《阵亡烈士葬仪图》,普法战争后,当德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门采尔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幅以重工业工人为主题的《轧铁工厂》,得到了广泛的赞扬。但是,构成画家全部风格的却不光是这些画幅,门采尔还以更多的心力正视现实,以大量素描勾下了和这些重大题材不可分割的社会的图景,他以朴素的笔调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刻画他们的勤劳和坚韧,描摹他们的痛苦和忧虑。老人,儿童,妇女,肮脏的街角,简陋的农舍,拥挤的车厢,往往以独创的意境构成动人的画面。他以为日常生活的中心主题应该是劳动,在许多小幅素描里,工人便成为他速写的主要的对象,从共同操作(《工作台旁的三个五金工人》《正在盖房子的泥瓦匠》《吊架上的油漆工人》《两个石匠在加工一块石板》等等)到个体形象(《系皮围裙的轧铁工人》《一个拿大钳子工人的背影》《老泥水匠》等等),一个姿势结合着一种动作,看去莫不栩栩如生。以那幅《跪在地下操作的工人》为例,我们看不到他手里的工具,甚至也看不到他脸部的表情,但是从弓起的背部和支地的两腿里,作者表现了劳动的强度,使我们的感觉接触到一股少有的力的遒劲。艺术的力量是内在的。在平静的画面底下潜伏着不平静的生活,这正是门采尔风格的特点。我以为我们也应该这样来读立波的短篇。有些人只爱看直接描写,不许有侧面烘染,更有些人认为作者没有写农村的剧烈斗争,却去写一对青年人的婚礼,是“游离于阶级社会之外,脱离了政治”。这些看来不免都是偏见。不直接描写阶级斗争并不等于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姑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人要结婚,有人要参加婚礼,说不上“游离”不“游离”,今天,“山那面人家”的一对青年人,有了称心满意的结合,姑娘们“看着别人的幸福,增加自己的欢喜”,“嘻嘻哈哈地笑个不断纤”,年轻一代的生活沉浸在欢乐愉快的气氛中,这又是怎么得来的呢?难道这里面就没有一点政治吗?
(德)阿尔道夫·门采尔:《轧铁工厂》(1875),布面油画,158x254cm 不!这是政治,这是隐藏在作者世界观里最根本的东西:旧的沉下去,新的升上来,不过这回是偏重后者,因而不是采用“暴风骤雨”的形式,而是表现了风和日丽的风格。由于作者对社会主义的倾心,对农村新气象的情不自禁的赞叹,笑,成为贯串整个小说的一条红线。姑娘成了堆,总是爱笑。一路上是嘻嘻哈哈地笑,到新房是轻声地笑,哄往门外去一路笑,躲在窗外又爆发了一阵笑,到堂屋里肩挨着肩,咬着耳朵笑,听新娘讲话时吃吃地笑,一直到婚礼结束,客人散去,微风还送来她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声。她们为什么笑呢?正如作者所描写的:“青春,康健,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翡青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的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蒙胧的、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活的源泉。”那么,她们又为什么不笑呢?不仅她们,新郎也笑,新娘也笑,客人们也笑,送新娘子的一个三岁伢子,也被逗得高兴地笑,满屋子的人都笑,连挺着胖大肚子的一对细瓷罗汉,也在哈哈大笑。只有一个人不笑:乡长。然而这个不笑的乡长偏偏又是最会说笑话的人,看来,他也正是“快活的源泉”。作者挑选了一个这样的环境,通过一对青年的婚礼,渲染了“歌声载道,喜气盈门”的农村的新面貌,刻画了人们在新社会里的精神状态,这是作者眼里看出来的生活的特征:淳朴、轻松、愉快。风格从哪里来?我看首先就是通过现实生活的印证,在人们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培育下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作家立波的风格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由于他适当地运用了农民的语言,描画了农村的风习,使整个小说洋溢着朴紊的乡土的气息。立波对农村生活的谙熟,知识的丰富,写来得心应手,好比搓泥丸子一样,搓得烂熟,这就大大地有助于他的风格的创造。譬如写听壁脚,写送新娘子,写哭嫁,写窗格、锡烛台、小镜子、瓷壶、瓷碗上贴红纸囍字,写新房里的陈设,一切都是土生土长,展示了农民的风俗和习惯。然而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些的同时,又给所有风俗习惯涂上了一层十分匀称的时代的色泽,使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土生土长的,然而在土生土长的上面,又时时反射出一种新的光彩。这是什么呢?是人的精神面貌的折光吗?你看,新娘子掏出她的劳动手册来了,两千工分,还说她不是吃闲饭靠人来的,是过来劳动的;你看,新郎公趁着婚礼进行,大家一不留神,偷偷地溜到山边地窖里,检查红薯种去了;你看,除了那位还在改造中途、目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的牛郎中外,所有参加婚礼的人,从老社长到后生子,他们在为什么叫好、为什么拍手呵!正是这些生活习惯、精神面貌上的细节,织成了作者心头的喜悦,成为他的风格的要素。有人说,这篇小说存在着“严重的笔墨浪费现象”,写了太多“与主题无关紧要的东西”,“用五六百字”就可以写完,而且主题思想可以“更为鲜明”。我并不认为《山那面人家》不能再压缩,倘说可以压到“五六百字”,使主题思想“更鲜明”,却实在使我吃惊。如果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能手,我极愿立刻卷起铺盖,登门执弟子礼,好好地学会这个本领。只怕事实并不如此。因为一篇有风格的小说,它的细节描写往往和人物的性格相联系,也和作者的思想感情胶合在一起,不可能拆散分开。加以删削,不仅风格将完全失去,而且主题思想也不会“更鲜明”,怕是会更模糊。《山那面人家》里的细节,那些有关风土人情的描写,基本上合乎这个要求,作者并没有太多地浪费自己的笔墨。我完全赞成把小说写得短些好些,但是短些不应该妨碍好些,好比写字——哦!我又谈到书法上来了——,大概是苏东坡说的吧,他说:写大字要收紧,写小字要放松。我看这句话很有道理。在艺术创作上也一样。所谓放松,当然不是说短篇就可以拖沓,而是谈写短篇时作者的意境要开广,撒得开,看看得远。惟其是短篇,题材的限制很大,作者不仅要深入眼前的对象,还得像《水浒》里公孙胜使唤天兵天将一样,从自己的全部经验里,唤起所有的生活知识——新鲜的、生动的、具有民族特征的、经过严格选择的形象,来支援艺术风格的诞生。我以为立波的长处,是他对中国农村生活有丰富经验,对民族风习有广泛知识,运用起来十分熟练。所以他的风格除了淳朴厚实之外,还能够有含蓄,饶余味。
唐弢漫画像(丁聪绘) 作者的意境要开广,读者的意境也要开广。如果表现在作品里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加以批评,这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不应该流于俭啬和狭隘。我并不是说立波的短篇已经写得那么好,没有一点缺点。我只是就风格说明一点自己的意见。和《山乡巨变》一样,这些短篇也是作者整个风格的体现。在《山那面人家》里,社长不同意兽医在婚礼上大谈国内外形势,有人说这是“不关心政治”;社长称道新娘的两千工分是真正嫁妆,有入说这是“金钱观点”;新娘讲话时说“我快活极了,高兴极了”,有人说这是宣扬“结婚就是幸福主义”;姑娘们来“听壁脚”,有人说这是“低级趣味”的“庸俗观点”;新房全部铺盖,只有两个枕头是新的,有人说这是歪曲农民生活;用了五块钱社长还要监督,有人说这是诬蔑干部和群众关系;写月光花香树影,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称空口白话为“八股”,有人说这是修正主义。总之,“主义”一大堆,“观点”满天飞,片面地根据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原则,去判断丰富复杂的生活,判断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品,不但割裂了生活,实际上也是割裂了作者的世界观,把作者思想感情里错综衔接、互相统一的关系,还原到一个简单的公式。这样,生活干瘪了,思想枯竭了,作品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它的结果必然是:风格的萎缩。 然而我们是要有风格的,我们党提倡风格,赞成艺术园地里出现多种多样的风格,在一切成熟的——不管是年轻的或者年老的作家的笔底,新的风格正在成长。暴风骤雨是一种风格,风和日丽也是一种风格;绚烂是一风格,平易也是一种风格。不同的风格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服务得很好。布封还说“历史只画人,并且画得恰如其分。”(《论文笔》,《布封文钞》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生活是多彩的,人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希望看到正在进行的斗争,也愿意欣赏斗争得来的成果;既赞成奔放、雄伟、刚健、热烈,也赞成淳朴、厚实、清新、隽永。这一切都符合于我们的民族气派与时代精神。我们要求的是多种多样恰如其分的人,也要求多种多样恰如其分的风格。但自然,如果有人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寄情“枯树”,托意“小园”,从生机蓬勃中追求虚无空灵的风格,那就干脆告诉他:我们不赞成! 一九五九年六月于上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