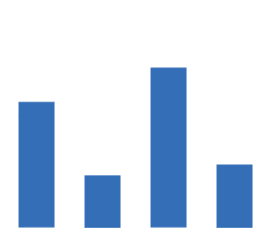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告子人性论和孟子性善论你支持哪个观点 › 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
梁涛:以生言性”的传统与孟子性善论
|
一、“以生言性”的意蕴及其不同命题表述 在古汉语中,“生”、“性”乃同源字。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只有“生”字而无“性”字,“性”字是从“生”字派生而来。徐灝《说文解字笺》:“生,古性字,书传往往互用。《周礼》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读为性。《左氏》昭八年传,‘民力雕尽,怨讟并作,莫保其性。’言莫保其生也。”故古文中先有“生”字,后有加心旁的“性”字,“生”、“性”二字的含义存在密切的联系。所以“以生言性”从字源的角度看,乃表示“性”字源自于“生”字;从思想的角度看,则表示古人是从“生”来理解“性”。由于“生”、“性”的这种密切联系,古代思想家往往通过“生”来理解“性”,如告子的“生之谓性”。 不过,告子虽提出“生之谓性”,却没有对其内涵作具体说明。从字面看,“生之谓性”乃是以上之“生”解下之“性”,也可以表述为:性,生也。而“生”字在古语中的含义十分丰富:作为动词,它可指出生、生长;作为名词,可指出生以后的生命,以及生命所表现的生理欲望等(《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这里的“生”即有“欲”之意)。而如何理解“生”或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生”,往往又会影响到如何理解“性”。所以,“生之谓性”实际只是一个形式的命题,它只是表明“性”就是“生”;但“性”何以是“生”,或在何种意义上是“生”,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说明。根据《孟子·告子上》,告子关于人性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告子曰:“生之谓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东西也。” 从告子的论述来看,他是从“食色”等自然生理欲望来理解性的,故他所谓“生之谓性”的“生”,应是指天生、出生,同时也指生理欲望。告子的“生之谓性”可以表述为“生之然之谓性”。而告子提出“生之谓性”,显然是源于古代“以生言性”的传统。 由于“生”、“性”具有密切联系,而“生之谓性”又只是一个形式命题,所以古代思想家往往通过对“生”、“性”的关系作进一步说明,以表达其对“性”的理解。如《荀子•正名篇》云: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这里,荀子对于“性”下了两个定义:一是“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一是“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其中前一个定义显然是对“生”、“性”关系的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所以学术界往往认为,荀子对性的理解与告子的“生之谓性”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告子对“性”的理解却并非属于同一个层面。有学者将“生之所以然”改为“生之所已然”,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生来就是这样的叫做性”。(张岱年,第96页)如此改字解经,并不可取。盖荀子对“性”的定义是“生之所以然”,而非“生之然”或“生之所然”,更非“生之所已然”。“生之然”或“生之所然”是就生之表现、现象言,而“生之所以然”是就生之现象、表现更进一步求生之原因、根据;“生之然”或“生之所然”是情、是欲,而“生之所以然”则是理。所以黄彰健先生认为,“《荀子》所言‘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也只是说‘生之所然的那个道理',或者是‘所以生之理’谓之性而己。”(黄彰建)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此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生之所以然’,乃是求生的根据,这是从生理现象推进一层的说法。此一说法,与孔子的‘性与天道'及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的性,在同一个层次,这是孔子以来,新传统的最根本的说法。”(徐复观,第203页)徐先生认为“生之所以然”是从生理现象推进一层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他将其等同于孟子的道德义理之性,则缘于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理。廖名春先生根据对语义的分析,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即“生之所以生者谓之性”而“生之所以生者谓之性”,变换一下句式,可作“性者生之所以生也”(廖名春第98页),这种看法无疑对理解荀子的定义很有启发。但他认为“生之所以生”的“性”是指人的形体器官,包括目、耳、口、鼻、身等(同上),则失之偏颇。 古人意识到不同生命物皆有其生,并进一步由此联想到其有不同的性。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云: 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 “长”同“胀”。牛生体形庞大,雁生脖子长,即是它们的性使然。这正是“以生言性”。故唐君毅先生说:“一具体之生命在生长变化发展中,而其生长变化发展,必有所向。此所向之所在,即其生命之性之所在。此盖即中国古代之生字所以能涵具性之义,而进一步更有单独之性字之原始。既有性字,而中国后之学者,乃多喜即生以言性。”(唐君毅,第27-28页)生乃一具体生命之存在,而此生命之所以如此生,即是其性。“以生言性”之涵义,包括“有生即有性”、“性由生见”之意。所以古人言性,不是通过概括、抽象,以求客观存在之性质、性相,如圆性、方性等等,而是重生命物之生,并从其生来理解其性。如草木之生长可开花结果,即可说草木有开花结果之性:当草木未开花结果时,可说其有开花结果之性向;当草木开花结果时,则可说其实现了性。所以古人所言之性,不是抽象的本质、定义,不是“属加种差”,而是倾向、趋势、活动、过程,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 由于性是一生命物之所以如此生长的内在规定,而生命物的生长也往往体现在其形色、形体中,所以性也可以兼指形色、形体。如孟子所谓“形色,天性也”(《孟子•尽心上》),即是说“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之性“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又如,《吕氏春秋•壅塞》:“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高诱注:“性犹体也。”《淮南子•修务训》:“曼颊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性可悦者,西施、阳文也。”高诱注:“性犹姿也。”《孔丛子•居卫》:“人之贤圣在德,岂在貌乎!且吾性无须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损其敬。”“性无须眉”即“身无须眉”,这是以“性”为“身体”的例子。廖名春先生认为形体是生之所以生的物质载体,所以荀子的性是指形体,这种看法乃是倒因为果,颠倒了性与形体的关系。了解了古代“以生言性”的传统,荀子关于性的第一个定义便容易理解了:“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翻译过来就是:“(一生命物)之所以生长为这样的原因就是性。” 荀子“性之和所生”一句,杨倞的注释是:“和,阴阳冲和气也。……言人之性和气所生。”目前的《荀子》注本和涉及到荀子人性论的论著,一般将该句理解为:“本性是由阴阳二气相和产生的”,或“本性的阴阳二气相和所产生的”。按前一种理解,该句实际应为“性,和之所生也”,而不是“性之和所生”。后一种理解则颇有增字解经之嫌,亦不可取。该句的“和”应是对“性”的限制、修订:“性之和所生”就是指性是在和谐状态下产生的,这和下一句“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是一致的。这样,荀子关于性的第二个定义是说,性在和谐状态下,精神与外物相合感应,不经过人为努力或后天教化,自然产生出来的就是性。这一定义下的性,与前一定义下的性显然有所不同,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前一定义下的性是从生理现象推进一层,是求“生之所以然”的根据,实际是自然之理,是事物的型构之理。后一定义下的性,则是前一种性的作用和表现,是从生理现象以言性。故“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中的前一个性,是“生之所以然谓之性”的性,是作为生之根据和原因的性;后一个性则是前一个性“所生”,也就是前一个性的作用和表现。荀子在一个定义中,前后使用了两个性字,其内涵实际是不一样的。严格说来,告子“食色,性也”的性,只能算是荀子第二个定义下的性,而不是第一个定义下的性。 董仲舒对“以生言性”的理解,也反映了这一点。其云:“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春秋繁露•深察明号》)董子将性理解为质,认为若其天生而具有的自然之资质便是性。质是材质、质地之意,故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实性》)“质朴之谓性。”(《董子文集•贤良策三》)此“质”构成事物的内在规定,同时也决定其以后的生长、发展。从这一点看,其对性的理解与荀子关于性的第一个定义有相近之处,二者属于同一个层面。不过其所谓“自然之资”却是包括善端和仁性的,如,“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春秋繁露•玉杯》)“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深察明号》)这点与告子、荀子不同,反倒更接近孟子。故其“自然”主要是指“不事而自然”,是未加人为的意思,而不是指生理自然。另外,董子所说的“生”是指上天所生,实际是蕴涵了一个有目的、有意志的神学天,如,“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同上)这与告子、孟子、荀子均有所不同。 综上所论,“以生言性”乃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这一传统又可概括为“生之谓性”。它既表示“性”字源自“生”字,也说明古人是从“生”来理解“性”,而如何从“生”来理解“性”,对此不同思想家的见解则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别。所以,“生之谓性”只是一形式命题,而要使其成为一个有效命题,还需对“生”、“性”关系作进一步限定和说明。这样,由“以生言性”或“生之谓性”便衍生出以下命题形式:其一,“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或“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指生命物之所以如此生长的根据、原因或生而所具的自然本质为性,这是对性的实质规定;惟有具有了此规定,以上命题才能成为一个有效命题,才能对不同事物作出区分与规定。其二,“生之然之谓性”,或“性,生而然者也”(《论衡·本性》)指生而所具的生理欲望或生理现象为性,也就是指前一种性的作用、表现为性,这是对性的形式规定。告子虽提出“生之谓性”,但其具体所要表达的却是这一层含义。而“生之谓性”之所以可以包涵这一层含义,是因为当时人们主要是从自然生命来理解性的,而谈自然生命不能不谈其具体表现,故“食色,性也”便成为“生之谓性”的当有之意。至于董子将善端、仁性也包括在“生之自然之资”中,则可能是一种后起的看法,是对孟子性善论的一种回应,而在孟子之前,“生之谓性”主要是针对自然生命而言的。由此可见,由古代“以生言性”传统引伸出的以上两种不同命题表述,前一种更为根本、重要,后一种则相对次要。而告子的“生之谓性”实际表达的只是后一命题的含义,而不具有前一命题的含义,其对“性”的理解是不够全面、准确的。相比较而言,荀子对“性”的理解则更为全面。虽然他对“性”、“伪”作出的严格区分未必符合当时学者的一般看法,但他将“性”区分为“生之所以然”和“性之和所生”,从生理现象背后的根据及生理现象两个层面来理解“性”,确实符合古代“以生言性”的传统,其观点更值得关注与重视。
二、孟、告“生之谓性”之辩疏解 根据《孟子·告子上》,孟、告辩论的具体内容是: 告子曰:“生之谓性。” 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 曰:“然。” “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 曰:“然。” “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历史上,有些学者从思想出发,往往将孟、告之辩与其各自的人性论主张联系在一起,以论证孟子性善论之是,告子性无善恶论之非。如东汉赵岐在“生之谓性”一句下注曰:“凡物生同类者皆同性。”在“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一段下,赵岐注曰:“孟子以为羽性轻,雪性消,玉性坚,虽俱白,其性不同。问告子,子以三白之性同邪?”在最后一句下注曰:“孟子言犬之性,岂与牛同所欲?牛之性,岂与人同所欲乎?”并总结该章章旨曰:“言物虽有性,性各殊异,惟人之性与善俱生,赤子入井以发其诚。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理学兴起后,由于提出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将“性”作形上、形下的区分,对此段文字的解释更为清楚明白。 另有学者则提出孟子的推理是否合理的问题,如北宋司马光的《疑孟》对孟子多所驳难、质疑,其“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告子当应之云:色则同矣,性则殊矣,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来犬、牛、人之难也。孟子亦可谓以辩胜人矣”(《疑孟下》),认为孟子实际是“以辩胜人”,其推理在逻辑上未必成立。近代以来,由于学者受到形式逻辑的训练,其分析更为细致、严密。如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的推理实际存在“两步跳跃或滑转”,盖因为“‘生之谓性’并不同于‘白之谓白',告子辨别不清而答曰‘是’(即认为生之谓性同于白之谓白),实则非是。这是孟子的误解(想得太快),把‘生之谓性’(性者生也)误解为像‘白之谓白'(白说为是白,白者白也)一样。这是第一步错误。至于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这是无问题的,……但由此亦推不到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这是孟子的第二步错误。”不过“孟子之推论虽不合逻辑,然而其心中所想人之所以与牛犬异者仍然对;依其所想之异而断‘性者生也’之说之不足以表示出此‘异’,这亦依然成立。”(牟宗三,1985年,第7-8页)换言之,孟子的推理虽不合逻辑,但其结论却是正确的。 以上思想、逻辑两种分析,其实都强调孟子性善论与告子“生之谓性”说的差异,并肯定性善论凸显“人之异于禽兽者”的积极意义。只不过逻辑的分析提出了孟子的推理是否合理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显然较之前者有所深入,其观点也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几乎成为一种定论。不过,上引牟先生的分析是否符合孟、告之辩的具体语境,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孟、告的辩论中,关键的是“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一句。这句既是孟子的设问,又是以下推论的前提,后面的结论便是由此推导出来的。若将该句看作是类推,确实如牟先生所言,是把两种不同类型的句子放在一起,存在着推理的错误。不过在原文的语境中,孟子并不是要作一类推判断,而是提出一设问;孟子之所以有此设问,又与告子对“生之谓性”的理解密切相关。盖因为告子是从“生之然之谓性”,而不是从“生之所以然者之谓性”来理解“生之谓性”。“生之然”或生而即有的生理欲望只是生命物的生理现象、外在表现,并不足以概括其全部的特质、特征,所以还需要由“生之然”进一步推论其“所以然”,由生理现象推论其背后的原因、根据,这便是“生之所以然者之谓性”命题的含义所在。告子的思想缺乏这一层面,其对“性”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孟子曾与其就人性善恶进行辩论,对这一点显然有所了解。所以孟子可能已注意到“生之谓性”只是一形式的命题,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完整观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说明,故要问:你是在什么意义下来理解“生之谓性”的?“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一句的“犹”,是“好比”的意思,它表示一种比喻,而不是类推。它是说,你所说的“生之谓性”好比“白之谓白”吗?因告子主张“食色,性也”从自然欲望、生理现象来理解性:凡生而所具的“食色”等生理欲望表现都可称为性,正好比凡具有白色外表或属性的都可称为白一样。孟子的这个比喻式判断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它不是孟子个人的主张,而是对告子观点的比喻式说明,意在使其观点明确起来。所以孟子的这一设问并不是一种“误解”;告子答曰“然”也不是其“辨别不清”,而是题中应有之意。若是在以上第一个命题即“生之所以然者之谓性”的意义上,“生之谓性”确实与“白之谓白”不等值,二者的确不可以进行类推;但若是在以上第二个命题,即“生之然之谓性”的意义上,“生之谓性”与“白之谓白”又是等值的,二者可以进行类推孟子的设问与告子答曰“然”皆由此来。 下一句“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中的“犹”,是“如同”的意思,表示类推。该句中的两个类推是由“白之谓白”而来,而不是由“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而来。再下一句“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虽是由上一句“白羽之白,犹白雪之白……”顺带而出,但其推理的根据则是“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告子既承认这一根据,则必然推出“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的结论。所以孟子这里实际使用的是归谬法,是从告子自己认可的主张推出告子自己也无法接受的结论,以批驳其仅仅从“生之然”、从生理欲望来理解性。焦循在“凡物生同类者皆同性”一句下注曰:“赵氏盖探孟子之旨而言之,非告子意也”认为“物生同类者皆同性”实际是孟子的主张,告子的“生之谓性”反倒不包涵这一层含义,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以往学者在论及孟、告之辩时,往往要联系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孟子是从性善论来批驳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不过,从当时的具体语境来看,孟、告之辩的焦点并不在于人性善恶的问题,而在于如何看待、理解“生之谓性”。孟子强调的是,不能从“白之谓白”的意义上理解“生之谓性”,即不能仅仅从生理欲望来理解性,认为这样势必会混同犬性、牛性与人性,因犬、牛、人均有“食色”等生理欲望,但却不意味着有相同的性。而且即使从犬、牛、羊的生理欲望有表现之不同,来区分其有不同的性,也依然不能成立。因这种不同是量上的,而不是质上的,不影响其同为性,正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可能有量上的差别(别白),但不影响其同为白一样。所以,还要从“生之然”进一步推求其“生之所以然”,以确立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及价值和尊严。至于人之为人的独特性在于其有善性,虽可能已蕴涵在孟子的思想中,但却并不是其驳倒告子的必要条件。 三、孟子性善论与“以生言性”传统 从孟、告之辩来看,孟子对于“以生言性”传统并非一概否定,而只是对告子关于“生之谓性”的具体理解提出批评。在儒学史上,“以生言性”亦不是儒家人性论的消极面,而是后者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由于“以生言性”是从“生”来理解“性”,“性”指生之所以生,此“性”非抽象的本质,而是动态的活动和过程,“以生言性”即包含有“性”有生长、成长之意。故“性”具体表现为生命物的材质、质地,此质既非材料之材质,亦非抽象之形式,而毋宁是有形式的材质;它非静态的质地义,而是动态的活动义、生长义。所以古人谈“性”,不是将本质、现象,形式、质料截然区分开来,而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盖因为其重“生”也。由于“性”有“生”,其在“生”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需要、种种表现,由于这些需要是“性之和所生”,是“性”在自身和谐生长中产生的,故满足这些需要乃是“天之经,地之义”也,是天所赋予人的权利。如“性”有“食色”之表现和需要,便应“制民之产”、设媒妁之言,以满足其生理欲望之需要;“性”有“喜怒哀乐”之表现和需要,便应使民交往、制礼作乐,以满足其情感表达之需要,“重生”、“养性”乃早期儒学的重要特征。郭店竹简《唐虞之道》云:“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养生。夫唯顺乎肌肤血气之情,养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养生而弗伤。”“养生”也就是“养性”,因为有“生”即有“性”,“性”规定了生之所以生,“生”的过程也就是“性”的实现过程。而“性”需要养,恰恰是因为其有“生”,正如树木需要培养,是因为其有生长一样。若“性”是抽象的本质,是脱离内容的形式,养性便不好理解,因为“性”改变,事物的性质也发生改变。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古代人性论的传统,“以生言性”主要是从自然生命来理解“生”和“性”的,上引竹简称“顺乎肌肤血气之情”,便是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血气的运行,血气乃自然生命的内在基础与动力。所以古人提出,要从“生之然”(主要表现为“食色”等生理欲望)进一步推求“生之所以然”,从生命物不同的“生”来理解其有不同的“性”,如牛之性在于其生而体型庞大,雁之性在于其生而脖子长等等。顺此思路,亦可以说,人之性在于其生而两足直立。不过,这种区别乃是形式、外在的,是纯粹生理、型构上的,还不足以真正将人与禽兽作出区别。故人之为人的特殊性在哪里,人与禽兽的真正区别在哪里,便成为古代哲人不断思考的问题,前引竹简《性自命出》在谈到“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后,接着说“人而学或使之也”,便是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前者自觉,后者不自觉。所以人与禽兽虽然都有“生”,但禽兽之“生”只是一种自然本能,而人之“生”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和创造,故人之特殊性在于其能自觉地塑造、完成、实现其性,能“动性”、“逆性”、“实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性自命出》);正因为如此,人有自由,而禽兽没有自由。 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对人禽之别的看法是,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有道德自觉。“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提出“仁”也是要揭示人的道德意识与道德生命,故“仁”也成为人之为人之所在。孟子虽然直接承继孔子所开启的仁性、德性,更关注于人的道德生命,但在对人性的理解上,孟子又不能不受到古代“以生言性”传统的影响,所以孟子一方面超越了“以生言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袭取“以生言性”的思维方式,从道德生命的“生”而不仅仅是从自然生命的“生”来理解人的“性”。孟子性善论及作为性善论核心的“四端”说,即来自于此。在孟子看来“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仁的道德意识体现于心之中,是通过心表现出来的,所以人之为人之所在,不仅在于其有四体之“生”,同时还在于其有心之“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从生而所具的禀赋来看,人与禽兽是相差不远的;人之为人之所在,人与禽兽的真正区别,只有在四端之心的生长、扩充、实现中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所以四端之心虽然只是道德意识、道德生命的根芽、幼苗,但却蕴含着道德生命生长、发展的全部可能性。自然,这种可能性要在后天的扩充、培养中才能真正实现、完成。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这是说“根于心”的仁义礼智有一个“生”的过程,并将其“生”体现于形色和行为之中。其中“根于心”、“生色也睟然”,形象地道出仁义礼智“生”的特点。 孟子曰: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而已矣。(《告子上》) 这是以谷物的生长为例,说明仁也有一个“生”的过程。所以孟子又有“粪心”之说:“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说苑•建本》)所以孟子并非一概地否定“以生言性”传统,而毋宁说是超越、发展了“以生言性”传统。孟子虽然即心言性,从心之生来理解人之性,但在孟子那里,心与身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大体”与“小体”的区别。孟子虽然也讲“生”与“义”、自然生命与道德生命的冲突与对立,但那往往是针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境地,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特殊选择,所以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生”与“利”。孟子虽然重视良知良能,重视道德生命,但道德生命与自然生命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毋宁是超越的关系,是低层次需要与高层次需要的关系。从自然生命的“生”固然可以引出财产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健康快乐的需要,然而从道德生命(四端之心)的“生”,同样可以引出不食嗟来之食、维护人格尊严的需要,“处士衡议”、社会批判的需要,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实现终极关怀的需要,这些需要共同构成了人格健全发展亦即人实现其“生”的全部内容。 文章选自《哲学研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