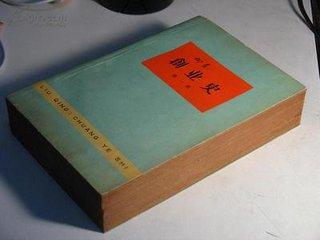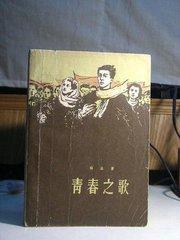政治与文学的博弈和媾和:“十七年文学”(1949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十七年文学的流派 › 政治与文学的博弈和媾和:“十七年文学”(1949 |
政治与文学的博弈和媾和:“十七年文学”(1949
|
除此之外,解放区文学需要的是“ 为工农兵服务” 、为革命服务的惧有当前功利性的作品, 因而作家的主要任务不是“表现自我” , 而是“讴歌他者”; 不是“宣扬自我” , 而是“宣传革命” 。文学有了一个外在的共同目标, 从此,文学便从纯粹个人创作的芜杂局面开始走向共同、单一的绝对外向式创作了。内向性的自我无用武之地,显得多余, 便开始退隐于幕后,并逐渐变得无足轻重、遮蔽不明起来了。这种情况沉积到五六十年代,就使得在十七年文学中“ 自我” 这个词都被遗忘了,自我失落了也不为人所知。 当然,十七年文学中还是有“人和自我”意识的体现的,不过这种体现是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进行的。如赵树理的小说就以《锻炼锻炼》为例,小说中塑造了“小腿疼”、“吃不饱”两个好吃懒做、爱占便宜的落后妇女形象及王聚海、杨小四等两种干部形象。从作者笔调来看,与农民的偷懒消极相比,作者显然更着墨对干部堕落的指责,他认为农民大众身上的美好人性是被这些“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给逼走的,而农人们看重踏实生活、重视个人权利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作者包容的。这不得不说是十七年文学中对“人” “自我”情怀抒发的一大亮点。 英雄模式化与中间人物缺失 自解放区文学开始,文学便为政治所膨胀, 所扼杀。这种膨胀和扼杀集中体现在文学的人物形象描写上——英雄模式化与中间人物缺失。如果要问十七年文学写了多少种人? 可以很简单地回答: 两个: 好人和坏人。或者再极端点地回答:没有一个。当然, 说十七年文学完全没有写出一个人, 似有些偏激。不过, 说十七年文学所写的“ 好人”或“ 坏人”都存在“非人化”倾向或事实上即“非人”, 却言之有据。现实中的“人” ,应该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他既有政治性的层面,也有非政治性的层面, 而且,后者在构成“人”这个系统中还占着更大的比重。 但是,英雄和先进难道不是个人存在吗? 表面看来似乎如是,不过只要多翻几篇作品,便会让人惊讶: 这些英雄和先进俨如一个模子里塑造出来的。他们都长得威武高大, 一脸正气, 连说话的腔调都几乎相同。《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 《红岩》 中的许云峰,《艳阳天》中的肖长春… … 除了时代、环境的不同,几乎难以区分出“这一个”和“那一个”来: 他们都是“一个人”的不同变体而已。而“这一个”,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提及英雄,便是长得威武高大,一脸正气,提及坏人,便是出身剥削阶层,欺男霸女,形象猥琐。“人” 失落了。文学中“个人”的消失, 又与此一时期文本个性的消失相响应: 对人理解的“模式化” 、“ 概念化” 必然带来创作的“ 模式化” 、“ 概念化” 。事实上, 整个十七年均可视作对先进“ 规范” 的公式表达: 或单纯讴歌之; 或写某人从“ 非规范” 向“ 规范”的努力、转换。 英雄模式化与中间人物缺失,这是时代和文学的悲哀,也是政治与文学的博弈的必然结果。 小结 对待在政治与文学的博弈中发展出来的十七年文学,我们不妨如果换一个角度, 即从文学的挣扎的角度来看, 十七年文学也许不只是一出乏善可陈的悲剧, 它可能还是一出有声有色的壮剧。它在面对文学政治化、政治左倾化的双重压力, 没有丢弃文学的理念,没有放弃文学的抗争, 相反却见缝插针地作着努力, 不屈不挠地争取生存与发展的权利。由此来看, 十七年的文学不仅在政治的压力下坚韧地生长着, 顽强地活着, 而且还因为其探求者的不畏强压, 忍辱负重,表现出一种“盗火者” 的奋斗精神与献身风度。这一切,就很值得我们以一种敬而重之的态度, 去重温他们那不同寻常的表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