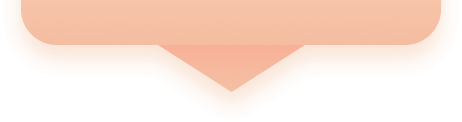中华诗词研究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余光中作品中的乡愁 › 中华诗词研究 |
中华诗词研究
|
一、立体的乡愁 余光中是著名的乡愁诗人,关于其诗歌的主题,诗人自己总结为三大焦点:“中国结、台湾心、香港情”[①]。对中国的乡愁乃是余光中诗歌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特征。然而,很多人理解这位诗人的乡愁,大多以为是思念着多年来归不得的中国大陆的深深哀愁。这是将余光中的乡愁看得单薄了。如果不是只盯着《乡愁》等几篇名作,愿意阅读更多的作品,便很容易能发现这位诗人的乡愁是很丰富、很立体的。2002年,余光中为百花文艺版的《余光中集》作序时特别讲到了这个误会:“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②]诗人又说:“两岸开放交流以来,地理的乡愁固然可解,但文化的乡愁依然存在,且因大陆深化的一再改型而似乎转深。……两岸开放,解构了我的乡愁主题。”[③]脍炙人口的《乡愁》:“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首诗写于1972年1月21日,此时诗人是回不到大陆的孤岛浪子,乡愁因为地理的隔绝而深浓。但是,当两岸开放交流以后,余光中的乡愁仍然未能得到纾解,这说明诗人的乡愁不仅是“地理的乡愁”,更加浓厚而持久的是“文化的乡愁”。下面的两段话则将他的“乡愁观”表达得更加明确: 中年人的乡思与孺慕,不仅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不仅是那一块大大陆的母体,也是,甚且更是,那上面发生过的一切。 所谓乡愁,原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等层次,……乡愁并不限于地理,它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了时间。[④] 很明显的,余光中思念和孺慕的不仅是空间性的,还是时间性的,包含“民族、历史、文化”等多重层次。这种立体的“乡愁观”外化为文字,体现为余光中诗歌中为中国古典文化的具体而丰富的“造像”。诗集《隔水观音》的后记中写到:“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既然余光中的乡愁是立体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所谓“为中国文化造像”的一类诗歌,不过是广义上的乡愁主题的作品。 余光中之所以在新诗中不断地加入“古典”的成分,其思想和情感的根源也正在于“乡愁”。关于这一点,余光中自己也有清晰的自觉:“我在处理古典题材时,常有一个原则,便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求其立体,……这样的做法,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心境,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⑤]余光中的乡愁是超越地理空间的、文化的、时间性的乡愁,这种立体的乡愁观表现为“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一种历史归属感”。文化和时间两个维度帮助余光中将中国古典文学锁定为寄托乡愁的对象。文化的浪子为了寻找归属之地,便在诗歌中努力捕获和熔铸古典文学的芳魂,以慰藉漂泊无依的孤独。 二、曲折的回归之路 基于文化乡愁的心境而写作新诗,于是“现代”对“古典”的接受和反叛便成为了余光中诗歌特有的意趣。在写作新诗时,要不要吸收中国古典文学?要在多大的程度上吸收?要以什么方式吸收?这样的问题一直在余光中写作诗歌的历程中纠纠缠缠,“古典”的成分在其新诗中时隐时现,或浓厚,或淡薄,或直露,或隐约。 余光中关于古今文学关系的认识,及其诗风的转变虽然有多次的反复和曲折,欲进还退,但是从其个人经历和诗集序跋来看,其诗歌观念和创作的变化还是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据其对“古典”态度的亲疏,可分为四个阶段:现代化实验期、新古典初期、新古典深化期、新古典成熟期。 在求学的时候,余光中虽然念的是外文系,但是对旧诗也很喜欢,他回忆:“(厦门大学时期)还在七言五言的平平仄仄里和缪斯捉迷藏。他们笑我的落伍,我也看不惯他们那种新诗,因为那实在是兑了许多水的诗意太稀的分行散文。”[⑥]后来,余光中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新诗和英诗,余光中的现代化开始了。在一九五二年出版的处女诗集《舟子的悲歌》后记中,余光中指明了“现代化实验期”的开始:“三年前我的兴趣转移到英诗。也在那时,我开始认真地写新诗。”五十年代伊始,余光中说:“我无日不读英诗”。于是,在旧诗的根底之上,余光中通过阅读英诗,经受着现代的洗礼,他的诗歌创作更加强调“现代诗的气候”,希望能够为现代诗开辟疆土。并且,还常常撰文为现代诗辩护。他说:“如果老妪们的耳朵失去了贞操,我们是非常抱歉的。我们的作品颇为野蛮,颇为桀骜不驯,那些听惯了神话和童歌的’听众’,是无法适应现代诗的气候的。”[⑦]老妪们耳朵的贞操大抵是指中国古典文学中“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诗人创作的现代诗是“颇为野蛮,颇为桀骜不驯”,正是对“温柔敦厚”的反叛。 如此激烈地与古典文学决裂的态度,在进入六十年代之后发生了关键的转变:“那几年(按,指1960-1964)正是我风格的转型期。大致说来,《莲的联想》以前是我的现代化实验期,到了《莲的联想》,便算是进入新古典期了。”[⑧]从“反古典”到“新古典”的转变与诗人的个体经历关联密切。1958到1971年之间,余光中曾三度赴美。《余光中传》中评价诗人的赴美经历时说到:“三次赴美,虽然停留的时间不算长,不过对于余光中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尤其是第一次赴美,30岁的余光中遭遇生命中的最大冲击,对他的思想及日后的写作风格,都导致了重大转捩。”[⑨]事情往往是这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异域,反而刺激了余光中对中国文化的孺慕之情。余光中回忆初赴美国的情境说:“隔着遥远的距离,反而看清孤立的台湾,那种渴望紧拥中华文化的情怀更强烈。”六十年代,余光中出国四处讲学,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在备课的时候,不免加深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和理解,进而刺激了诗人的创作。在诗集《敲打乐》新版自序中余光中写到:“《火山带》的末段说到在灯光下面对圣人的经典,那是指作者当时教中国古典文学,夜间备课的心情。”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和教授中,在增加的接触中,古典文学对余光中诗歌的创作影响日深。 “一九六一,那正是台湾现代诗反传统的高潮。”[⑩]而余光中却在西化的现代诗运动中竖起了一面“古典”的旗帜,1961年,余光中发表了《再见,虚无!》一文,正式宣告回归中国古典的路子。从“现代化实验期”到“新古典期”的转型,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传统”中汲取养料,奠定了余光中此后的诗歌风格和独特的诗坛地位。余光中诗歌的知音流沙河就评论:“就其主脉,一般而言,余光中的诗作,纳古典入现代,藏炫智入抒情,儒雅风流,有我中华文化独特的芬芳,深受鄙人偏爱。”[11]而余光中所谓的“新古典”,用他自己评论诗集《五陵少年》的话来总结最为贴切:“在内涵上,可以说始于反传统而终于吸收传统,在形式上,可以说始于自由诗而终于较为节制的安排。” 进入“新古典期”后,诗人不断地斟酌和拿捏“反传统”和“吸收传统”之间的尺度,故其“新古典期”又可分为初期、深化期和成熟期。旗帜鲜明地表明回归古典的决心的六十年代是新古典初期,在香港的十一年是深化期,之后是成熟期。1974年8月,余光中应香港中文大学的聘请来到香港,出任中文系教授。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在中国人的学校教中文。在确立了回归古典的路线,又借着教授中文的机缘,余光中在回归古典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而深入。余光中对此很有自觉,诗集《敲打乐》的自序中说到:“在主题上,直抒乡愁国难的作品减少了许多,取代它的,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探索,一方面也许是因为作者对中国的执着趋于沉潜,另一方面也许是六年来身在中文系的缘故。”这正是地理上的乡愁向时间、文化的乡愁的多向的深化。流沙河在《诗人余光中的香港时期》中说:“余光中是在九龙半岛上完成龙门一跃,成为中国当代大诗人的。”[12]如果说余光中是在香港时期完成跻身中国当代一流诗人的“龙门一跃”,那么无疑诗人身在中文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沉潜是重要的助力。 三、古今之辨:中国的文艺复兴 随着诗歌创作经验的积累,进入“新古典期”后,余光中对古今文学、旧诗与新诗的关系的看法也渐趋成熟,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关于古今文学关系的主张。关于现代与传统之异和同,余光中有正面的论述: 痖弦先生曾称我为“复辟派”。覃子豪先生以为我在向后转。……我主张扩大现代诗的领域,采用广义的现代主义。我坚决反对晦涩与虚无,反对以存在与达达相为表里的恶魇派。我认为,用现代手法处理现代题材的作品固然是现代诗,用现代手法处理传统题材的作品也是现代诗,且更广阔而有前途。……我认为,一位诗人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之后,应该炼成一种点金术,把任何传统的东西都点成现代,他不必绕着弯子去逃避传统,也不必武装起来去反叛传统。 …… 我认为:反叛传统不如利用传统。狭窄的现代诗人但见传统与现代之异,不见两者之同;但见两者之分,不见两者之合。对于传统,一位真正的现代诗人应该知道如何入而复出,出而复入,以至自由出入。[13] 一方面,余光中肯定新诗之于旧诗有明显的差异性。为了开辟现代诗的疆土,余光中很重视新诗的现代性,他认为新诗是在大量吸收欧美的文艺思潮之后,“中国文化之现代化的一支运动”。新诗之异于旧诗,重要的不在于外在语言形式的文白之变,其核心在于思想内容与美学标准的改变。《摸象与画虎》一文中说:“技巧成分多于内容,而现代诗的所以异于古代诗,乃是在于思想内容与美学标准的改变。有新内容,新精神,始有新形式,新技巧。”[14]现代精神是新诗走出旧诗范式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余光中认为更重要的是,新诗的创作应该脱离狭义的现代主义,扩大现代诗的天地。在中国现代诗运动的思潮中,余光中独树一帜之处在于,将现代诗发展的焦点从“西化”转化为“现代化”,从“中西”的矛盾,转而关注“古今”的关系。从“现代化”出发,主张脱离狭义的现代化,采用广义的现代主义,而所谓“广义的现代主义”,换一种说法,就是指“新古典主义”,指“始于反传统而终于吸收传统”的主义。在《迎文艺复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一文中他提到:“问题不是中国之西化,而是中国之现代化。如是则中西文化论证殆亦今古之争,而今古之争是自古至今,自今而后永无休止的争执。”[15]在厘清古今文学、中西文学的关系之后,余光中正式提出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说,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诗的前途: 我们的理想是,要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少壮的艺术家们必须先自中国的古典传统里走出来,去西方的古典传统和现代文艺中受一番洗礼,然后走回中国,继承在自己的古典传统而发扬光大,其结果是建立新的活的传统。 …… 一直要到这样的一天:当新诗即诗,西画即画,西乐即乐,一切艺术不分中西,皆纳入我国的传统,一直要到这样的一天,中国的现代文艺才算取得嫡系的正统地位,而中国的文艺复兴才算正式开始。到那时,传统的会变成活的,活的也自然而然地汇入传统。[16] 余光中的理想其实是要实现现代诗对古典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霸权主义”,比之那些反对传统、反对旧文学、反对旧诗的人更加霸道。他对中国现代文艺的期望是“取得嫡系的正统地位”,而不是一直不尴不尬地和古典文学的传统对峙。中国的现代诗,推而广之到中国的现代文艺,要从中国的古典传统中“走出”,经过“西方”和“现代”的洗礼,再“走回”传统,激活传统,“始于反传统而终于吸收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会变成活的,活的也自然而然地汇入传统”。 至于现代诗应该如何“走回”传统,余光中勤加琢磨并躬身实践。在现代诗的创作中,余光中将古典文学作为素材和宝库,内容方面,用经过现代洗礼的眼光去处理、翻新古典的素材;形式和技巧方面,也对古典诗歌多有借鉴。而余光中在走回传统的每一步,辨证的思考一直贯穿于他的主张和创作中,所以余光中不是“现代主义”而是“广义的现代主义”,不是“古典”,而是“新古典”。《艺术创作与间接经验》中说:“古典文学更是一大宝库,若能活用,可谓取之不竭。理想的结果,是主题与语言经过蜕变,应有现代感,不能沦为旧诗的白话翻译,或是名言警句的集锦。”可见,余光中对传统的利用有两个特点,一是“主题与语言经过蜕变,应有现代感”,二是利用传统不可流于表面。诗集《隔水观音》后记中有一段话则简明扼要概括了他走回传统的方式和原则: 我在处理古典题材时,常有一个原则,便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求其立体,不是新其节奏,便是新其意象,不是异其语言,便是异其观点,总之,不甘落于平面,更不甘至于古典作品的白话版。……在另一方面,写今人今事,我又常用古人古事来印证。[17] 在利用古典文学时要“赋经典以新的意义”,达到“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的效果。最终,现代与古典的对比成为了余光中诗歌中最戏剧化的张力和艺术效果。 依照“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的原则,余光中诗歌中利用联想、影射和对比等思路,接通了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将古典文学卷入现代诗,开拓了现代诗的疆域。诚然,余光中立体的乡愁中孺慕的是整体的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然而我们不妨做一点脚踏实地的“考证”,以其现代诗的创作为分析对象,检测其中的古典文学的基因。所以,下文将结合余光中的创作实践,从具体的诗歌创作出发,对余光中诗歌进行“古典文学DNA”的检测和分析。 四、古诗句的现代穿越 余光中喜欢读中国的古诗,从李杜到韩愈、苏轼,古诗的阅读经验也常常在诗歌中加以表现。多年的喜爱和浸淫,使得诗人在创作新诗时往往会联想到那些熟读的诗句,并通过嫁接、改写等方式使古诗成句融入到新诗中。 先谈对古典文学最直接的利用方式“嫁接”。在一些诗作中,余光中直接把古诗的成句,或是古典文学中的名句原样移植,形成了文白对照和古今对照的格局,例如《秦俑》: 严整的纪律,浩荡六千兵骑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 修我戈矛 慷慨的歌声里,追随着祖龙 统统都入了地下,不料才三年 外面不再是姓嬴的天下[18] “嫁接”的古诗成句出自《诗经》。诗人用单独成段的方式突出古诗嫁接的痕迹。对以往经典的因袭古已有之,但古人袭用前人成句往往默而不言,且努力使前人的成句和自己的创作融合一体,羚羊挂角,不着痕迹。但是,余光中采用了写论文时候的引证的方法,强调了“嫁接”的行为,这种现代化的改造手法,虽然降低了融合度,但反而使得诗歌有了复调的表达效果。以《秦俑》一首为例,白话文的部分是诗人视角的叙事,明显引用《诗经》的痕迹,形成了间离效果,仿佛是地下秦俑的“慷慨的歌声”,与白话诗行形成鲜明对比,历史的纵深和遥远在反差中得以展现。 除了直接的嫁接之外,余光中的诗歌中更常见对古诗成句的改写。第一种改写是翻新古典素材,“将旧诗的韵味点化为更新的事实”,使其具有时代感。如《五陵少年》:“千金裘在拍卖行的橱窗里挂着/当掉五花马只剩下关节炎”。李白吟唱的是:“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而“换”,落在现代的场景中,就成了悬挂在“拍卖行的橱窗”的千金裘。“关节炎”,现代的病名,当掉了代步的五花马的痴狂酒徒,穿越到现代,被诗人诊断出患了关节炎。今古场景的交错,诗人成了现代的五陵少年,成了醉酒的李白。现代诗改写古诗,融合古典素材和现代精神,形成了“新古典主义”的现代诗。《布谷》也有类似的构思:“扫墓的路上不见牧童/杏花村的小店改卖了啤酒”。晚唐的杜牧行走在雨中的清明,行走在酒家、牧童、杏花村构成的意境中。同样是清明,二十世纪的余光中却遇不到牧童,古典诗歌中的杏花村也改卖了啤酒。清明扫墓的情节触发诗人接通了古典诗歌的意境,换来了天才的一句“杏花村的小店改卖了啤酒”:虚构的“杏花村”中贩卖着现实的“啤酒”。诗人通过对古诗成句颇具时代感的改写,使诗歌具有了古今对立的张力,展示了在时间的变迁中,存在的与逝去的。 第二种改写是赋予现代题材古典的内涵。较古诗而言,现代诗的题材有巨大的扩展,现代生活和现代事物不断地被新诗表达。而余光中因为心中怀着对古典文化的乡愁,在新诗中赋写现代的日常生活体验时,往往联想到古典的表达,便以古证今地赋予了日常题材古典的内涵。《鱼市场记》写的是诗人逛鱼市场看到屠杀待卖的死鱼的心理活动,末几句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鱼,安知鱼之苦?/子在濠上,鱼在俎上”。诗人先用了《庄子》原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第二句对其进行翻案,“子非鱼,安知鱼之苦”;最后解释子不知鱼之苦与乐的原因:“子在濠上,鱼在俎上。”《庄子》写鱼之乐,而余光中通过在现代鱼市场的见到的屠鱼场面而写鱼之苦。这种从凡俗中的普通生活引申到哲学的思考,从“事”到“诗”的跨越,正是借助了古典文学的助力。 又如写于第一次到美国时期的《新大陆之晨》:“然后踏着艺术馆后犹青的芳草地/(它不认识牛希济),/穿过爱奥华河畔的柳荫/(它不认识桓温),/向另一座摩天楼/(它不认识王粲)。”人在异乡,诗人耳目所见所闻是美国的“芳草地”、“爱奥华河畔的柳荫”和“摩天楼”,但身在异乡,却心怀祖国,于是面对陌生的环境,诗人想到的却是古典的场景。“芳草地”让诗人想到牛希济的《生查子》:“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柳阴”让诗人想到《世说新语》关于桓温的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19]而看着摩天楼,诗人想到的是登楼的王粲。诗人四处被勾引的乡愁,表达出来却是古典文学中的三个名句。可见,将现代的事物赋予古典文学的内涵是诗人寄托乡愁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是对古诗成句原有意义的衍生。当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能够被某一古典文学激发共鸣时,诗人会运用以古证今的方法来演绎诗句;而也有的时候,古典文学的原有涵义刺激了诗人的诗思但却容纳不了诗人新的情感和思考,诗人便会对古诗成句进行翻案或意义的衍生。如《船湾堤上望中大》:“不识庐山,身在庐山的深处/出了庐山,就识得庐山真面目?/隔海回顾如前尘,十年后/隔记忆该是如何的庐山?”苏轼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余光中却提出质疑:“出了庐山,就识得庐山真面目?”言下之意指事实未必如此。而接下来的两句是对“身在庐山”的意义的拓展。在庐山和出庐山之间,苏轼指的是空间上的距离。“隔海回顾如前尘,十年后隔记忆该是如何的庐山?”余光中又增加了时间的维度。 最后谈一谈余光中对古诗句的敷句成篇。从字数上来衡量,对古典文学名句的嫁接和改写,嫁接与改写前后的字数较为均衡;而余光中对于古诗成句的利用还有一种字数不均衡的方式,即以古诗中的一句或一联为“兴”,敷衍成一首现代诗。由句敷衍成篇的利用方式,在余光中的诗集中最常见的是以某一联诗为副标题的做法。如《狂诗人——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满月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变奏》、《下次的约会——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中元夜——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等。此外又有将古诗成句作为开篇的起兴之句进而敷衍成篇的做法,如《坐看云起时》: 坐看云起时,秋之昙日屡目我/以白眼和青睐。我遂遥念阮籍/念他每行至第三世纪的穷途/辄恸哭如我,如我坐在/不知江南是什么的相思树下,看云起时 看云起时,善变的太空能作青白眼/看今之白我者,昔曾青我以晴朗 看云起时,谁在作青白眼/我并未恸哭,并未恸哭如魏人/我适行到水穷处,疑无路/遂坐看云起,测风的方向 “坐看云起时”是王维《终南别业》的结句,而余光中此处却将其拈来作为起句,想象“坐看云起”之所见所感。“看云起时”,诗人看到两种青白眼——太空的青白眼和“谁”的青白眼。太空的青白眼是蓝天白云、阴天和晴天;“谁”的青白眼是友善与恶意。而无论面对的是天灾还是人事的无常,诗人说自己都会坦然面对。诗人在新诗中补白的是旧诗中含义未尽的待续句,敷衍了“坐看云起时”的未完待续的留白。利用古典文学敷句成篇的又有《大江东去》等诗。 五、萤与烛:古典意象的现代化 余光中认为:“意象与节奏,原来是诗之感性的两个要素。”既然引以为要素,那么诗人在创作时对意象必有一番用心的经营。他有一篇专门谈论意象的文章《论意象》,其中说到:“现代诗人莫不需要寻找象征,属于他自己的新的象征。……个人商标式有系统的意象。……利用旧意象也是可行的,……现代诗人就会加入新的成分,使其现代化。”[20]余光中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对传统意象的继承和运用,他运用的方式就是“使其现代化”,即从中国的古典文学中借来意象,赋以一种更新的意义。在余光中的诗歌中常见一些经典的古典诗歌的意象,如蟋蟀、月、茱萸、菊、鹏、烛、萤、蛙、莲等等,这些古典意象的运用无疑是他回归古典的一种重要手法。下面将以萤、烛为中心,探讨余光中诗歌中古典意象的现代化。 本文选取萤和烛作为探讨的中心,或者说余光中诗歌中尤其偏爱赋写萤或烛的原因,正在于萤和烛是不仅是经典的古典意象,也是一种古代社会和古典情调的象征。此说何谓?电和灯是现代文明的心脏,现代生活因为电灯而发生了颠覆般的变化。现代社会的夜晚如白昼,明亮而热闹;而前现代社会的夜晚却是黑暗而沉寂的,能照亮黑暗的无非是星、月、烛、萤等自然光源。于是在夜里还活动的诗人们便经常将这些事物捕捉为诗歌的意象。而对于诗人余光中来说,萤、烛等意象能很好地寄托他对古代文化的孺慕,排解他的时间性的、文化的乡愁。下面就以一组古典的光源——萤、烛——为例,分析余光中对经典的景物意象的现代化改造。 1、意象一:萤 余光中赋写萤的诗歌有十余首,萤是一个为余光中喜爱且常常使用的意象。余光中的“萤”意象有丰富的意蕴,且和古诗中的“萤”意象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关系。从诗集中赋写萤的诗歌来看,余光中诗歌中的“萤”意象主要有四重象征意义。 一是象征骑士的爱情。如《植物园之夜》: 细草沉沉是露水泣吧,/薄雾平牵着一片轻纱;/新月那纤纤的梳儿一把/梳不透夏夜丛树的密发。 小萤孜孜地擎着弱火,/飞来飞去在寻找什么?/树阴里是谁偷哼着恋歌?/啊!/惆怅的原来不止我一个! 这首诗描写一个静谧的夜晚,因为抒情主人公心中有“情”,并以这种甜蜜的惆怅融入植物园夜晚的景色中,故而露水是眼泪,薄雾、新月和夏夜丛树则成为象征女性美丽的一组比喻。与第一段相对,第二段的意象“小萤”是“飞来飞去”寻找美丽女子的勇士,“孜孜”的姿态正象征了诗人热情而执着的对爱情的追求。余光中诗歌中用“萤”来象征男子炽热而不顾一切的痴迷爱恋的用法,更接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情调,抒发的是一种骑士的爱情。这两首诗都写于1951年,正是诗人青春且“无日不读英诗”的岁月,所以这时“萤”的意象还是西方古典文学的舶来品。 二是象征黑夜中的战士,如《夜归》、《矛盾》、《孤萤》等诗。以《夜归》为例: 一颗乍明乍灭的孤星/在汹涌的暗空独自挣泳。/最后它力尽地向我挥手,/转瞬已溺入深阔的乌云。 于是无论上方或下界,/整个宇宙都捉不到亮光。/我已经迷路于黑夜的血管,/盲目地,摸向黑夜的心脏。 但是不久从深邃的草底,/蓦地迸出了一闪流萤,/为我擎一枝清冷的残烛,/殷勤地照着我的归程。 夜归途中,星和月都被阴翳的浓云遮挡,周遭的世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而萤的出现,给黑暗中的诗人带来了光明与慰藉。萤在黑暗中可以发光的物理特性也为古代的诗人赞美,很多咏萤诗一方面歌颂萤火虫不与黑暗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借以表明自己高洁的品质;一方面赞美萤给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和温暖。如唐代的两首《咏萤》: 秋风凛凛月依依,飞过高梧影里时。处暗若教同众类,世间争得有人知。(郭震) 映水光难定,凌虚体自轻。夜风吹不灭,秋露洗还明。向烛仍分焰,投书更有情。犹将流乱影,来此傍檐楹。(李嘉祐) 余光中的诗和这两首唐代的咏萤诗都是从萤火虫的物理特性出发,作诗意的想象和引申。虽然在象征的意蕴上相似,但是很难讲这种根据物理特性引申出的象征意蕴是直接从唐诗中继承而来,说是今古诗心的不谋而合倒是更为妥当。 再看第三种意蕴,象征宫女。这一层意蕴则显然化自古诗。如《星之葬》:“浅蓝色的夜溢进窗来;夏斟德太满。/萤火虫的小宫灯做着梦,/梦见唐宫,梦见追逐的轻罗小扇”。这几句关于萤火虫的描写,源头是杜牧的《秋夕》:“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杜牧的诗写的是深宫里无聊度日的宫人用轻罗小扇扑萤火虫打发时光的画面。余光中用追忆的口吻,从萤火虫的视角回味千年前的这个画面,“梦见唐宫,梦见追逐的轻罗小扇”。同时为了配合这种古典的气氛,描写萤光时的比喻也与前面象征骑士爱情和暗夜斗士不同。前面是“擎着弱火”、“擎一枝清冷的残烛”,而此处是“小宫灯”。诗人正是借助“小宫灯”的比喻,顺利地接通了杜牧七绝的意境,从历史后视的角度将唐诗的意象引入新诗,为现代的夏夜增添了古典的情调。 最后一层意蕴是比喻手榴弹的火光,见《双人床》一诗: 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听榴弹,像一把呼啸的萤火/在你的,我的头顶窜过/窜过我的胡须你的头发/让政变和革命在四周呐喊 这首诗写于1966年,收入诗集《在冷战的年代》,在后记中作者写到:“现代诗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在心理的背景上,仍然不能摆脱巴黎或长安。让萨特或李白的血流到自己的蓝墨水里来,原是免不了也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自己的蓝墨水中只有外国人或唐朝人的血液,那恐怕只能视为一种病态了吧?……现代诗应该吸收机械,像吸收帆船和古堡那样自然。”[21]在六十年代初期诗人已经宣告要回归古典,但是诗人一直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回归古典不是完全的倒退,而是在中西方文明的洗礼之中熔铸一个“新的活的传统”。所以诗人说“让萨特或李白的血流到自己的蓝墨水里来,原是免不了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借鉴浪漫主义诗人的写法,用萤来象征骑士的爱情;或是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写唐宫中的流萤,都是利用中西方文学传统的好例证。然而利用传统并不意味着倒退,新时代的诗人应该学会用自己的笔描写新时代的生活。因为新时代有机械,所以“现代诗应该吸收机械”;因为新时代有“榴弹”,所以余光中的诗便也吸收了“榴弹”。 “萤”在中西文学的传统中都是一个经典的意象,余光中的诗歌也偏爱赋写萤火虫。从余光中诗歌中“萤”意象的四重象征来看,他对“萤”意象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的象征都有所借鉴;同时配合着新时代的新经验,也进一步发展了“萤”意象的内涵。余光中诗歌中“萤”的象征含义的多元化,正印证了余光中之回归古典,是经过西方洗礼的回归。他的目的是要创造“新古典”,创造一个“新的活的传统”。 2、意象二:烛 与“萤”意象包含古今中外的丰富意蕴相比,“烛”的意象更为单纯地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蕴,主要有两重象征,源于四首古诗,一是象征爱情,二是象征时间的流逝。以《古诗十九首》诗句为标题的《烛光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中烛的意象就包含了这两层涵义。 一枝短烛,自晚唐泣到现代/仍泣者,因小杜的那次恋爱/因此刻我也陷在/情网上,尘网上,一只仲夏的蜻蜓 甄甄啊,看蜡炬成灰,不久/我们亦成灰。今夕的约会/没有谁记得,除了玻璃之外/光年之外的更夫,除了这烛台 在古典文学中,因为烛光常为男女幽会的背景,便渐渐固定为象征男女之情的意象。“因小杜的恋爱”而从晚唐哭泣到现代的“一枝短烛”点化的是杜牧写给妙龄歌女的《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烛光照亮了晚唐的杜牧和歌女,又在千年后照亮了约会中的“我”和“甄甄”。此诗又以《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题,因此诗中又充满了对生命短暂的忧虑:“今夕的约会,没有谁记得”。在对时间流逝的恐惧中抒写爱情,于是仲夏的爱情和约会便沉入了离别的气氛。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有的心理结构——在宴游的热闹处感受到生离死别的威胁。这首诗中还点化了李商隐《无题》“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意。依李诗原意,“蜡炬成灰”是献身爱情的宣言,而余光中此处置换了烛意象的象征涵义,用“蜡炬成灰”来表现恋人们生命的终将逝去:“甄甄啊,看蜡炬成灰,不久,我们亦成灰。”余光中在一首诗中将三首写烛古诗的意韵通过改写、以诗为题和涵义置换的方式融会为一体,为现代人的爱情增添了古典的情调。 3、“古今对照”的意象结构 前面已经引述过,余光中总结:“我在处理古典题材时,常有一个原则,便是古今对照或古今互证。”萤和烛这两个代表古代光源的意象很有象征性,它们在余光中诗歌里的出现往往有一个契机:停电。停电意味着现代城市生活节奏的打断,进一步讲,就是“现代”的停顿。在“现代”暂停的时候,常常会激发诗人古典的情怀,外化为诗歌的表达就是对萤或烛的描写。于是,在余光中的多首以“停电”为题的诗歌中,便以“停电”为界限,停电前是灯火通明的“现代”,停电之后是黑暗中有微光的“古代”。诗人通过代表现代的灯与象征古代的萤、烛等意象的组合,结构出了“古今对照”的诗歌格局。下面各举一首写“萤”和“烛”的诗进行具体分析。 《火金姑》一诗写的是停电后的萤光。诗人自己解释:“台语称萤火虫为火金姑”。 多想某一个夏夜能够/一口气吹熄这港城/所有交通灯,霓虹灯,街灯/那千盏万盏刺眼的纷繁 只为了换回火金姑/点着她神秘的小灯笼/从童话的源头,唐诗的韵尾/从树根,从草丛的深处/寻寻觅觅,飘飘忽忽/一路飞来,接我回家去 诗的前一半写港城夏夜的灯火明媚,列数现代社会的各种灯:交通灯、霓虹灯、街灯,描写了现代夜晚的明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火金姑”这个意象,它来自“童话”和“唐诗”,象征着诗人的童年和人类的历史,蕴含着诗人的乡愁。 《停电》写的是停电后的“烛”意象: 猝不及防,下面那灿亮的海港/一下子熄灭了灯光/不料黑暗来突袭/被点穴的世界就停顿在那里/现代,是如此不堪一击 我起身去寻找蜡烛/却忘了杜牧那一截/在哪一家小客栈的桌上/早化成一滩银泪了/若是向李商隐去借呢/又怕唐突了他的西窗/打断巴山夜雨的倒叙/还是月光慷慨,清辉脉脉/洒落我面海的一角阳台/疑是李白倾侧了酒杯 《连环妙计》一文中余光中说:“所谓意象结构,是指一首诗内的许多意象,或因类似而相属,或因相反而对照,或因联想而相应,总之应该此呼彼答,有机发展,成一系统。”[22]余光中在“停电”诗中构筑的正是以现代光源意象和古代光源意象相反、相应而成的意象结构。在《停电》这首诗中,诗人以“灿亮的海港”、“灯光”对比杜牧的蜡烛、西窗烛和李白的月光,形成了“古今对照”的意象结构。 总之,通过对余光中诗歌里萤和烛的意象的微观检测,我们可以发现,余光中利用古典意象,既有对原有涵义的继承,也有置换,还有为传统的意象增添新鲜的涵义。所以,就这些古典意象本身包含的多重象征意义来看,已经具有了“古今对照”的趣味。而同时,余光中一系列的“停电”诗,又将古典意象和现代意象结合在一起,构筑了“古今对照”的意象结构。可见余光中很好地实现了他对要“走回”古典的主张。 六、结语 综上所述,自余光中在现代诗运动中独树一帜地提出“回归古典”的宣告以来,他便通过实际的创作践行他的主张,最终形成了中西交融、古今对照的诗歌风格,奠定了他在当代诗坛的地位。余光中认为古典文学中虽然没有现成的能为现代诗利用的精神和技巧,但诗人们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之后,再走回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传统,便能点化传统,熔铸新诗。从余光中现有的诗歌创作来看,他对古典文学的利用,虽然也有技巧方面的,但是运用娴熟的是将古典文学作为一种素材进行点化和改造,如诗集中颇为多见的对古诗成句的点化和对古典意象的改造。通过将古典文学融贯到现代诗的创作中,余光中开创了有个人特色的一派风格,奠定了他在当代诗坛的地位。 [1]《安石榴》后记。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 [2] 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3]《五行无阻》后记。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页。 [4]《白玉苦瓜》自序。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二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5]《隔水观音》后记。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二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 [6]《摸象与画虎》。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7]《钟乳石》后记。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0页。 [8]《武陵少年》序。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页。 [9] 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年版,第49页。 [10]《天狼星》后记。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11]《读》。见流沙河《南窗笑笑录》,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2] 流沙河:《诗人余光中的香港时期》,《香港文学》1988年12月。 [13]《摸象与画虎》。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14]《摸象与画虎》。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15]《迎文艺复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9页。 [16] 《迎文艺复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第149页。 [17]《隔水观音》后记。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二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47页。 [18] 文中所引余光中诗歌均引自《余光中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后不一一出注。 [19] 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页。 [20]《论意向》。见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21] 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二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22] 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页。 【作者简介】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本文转载自《中华诗词研究(第一辑)》(中华诗词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编,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10月),发表于《武陵学刊》2016年第5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