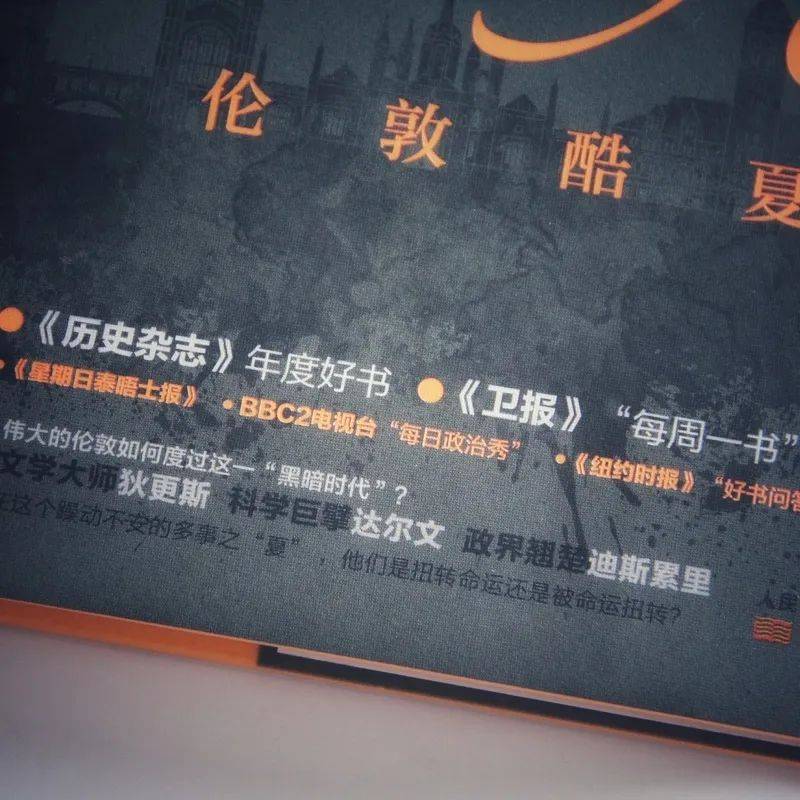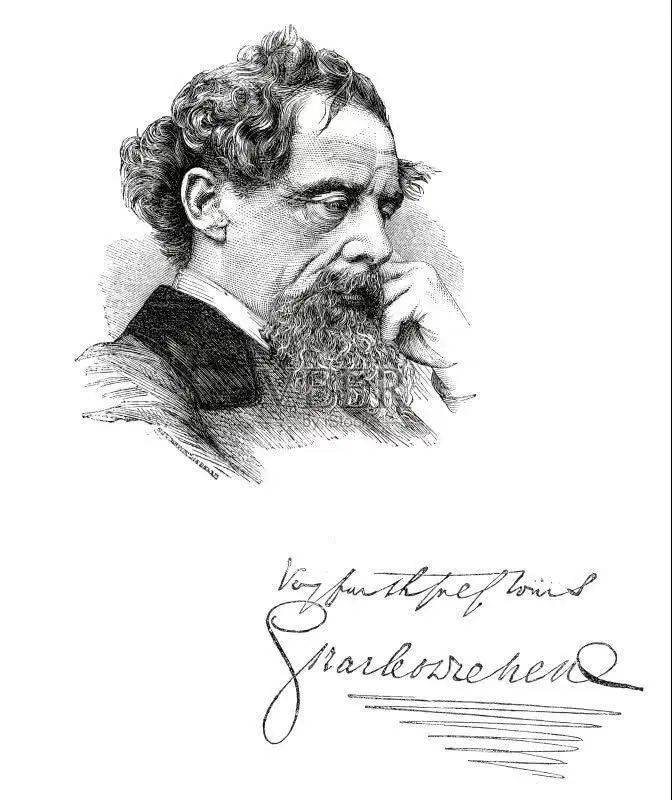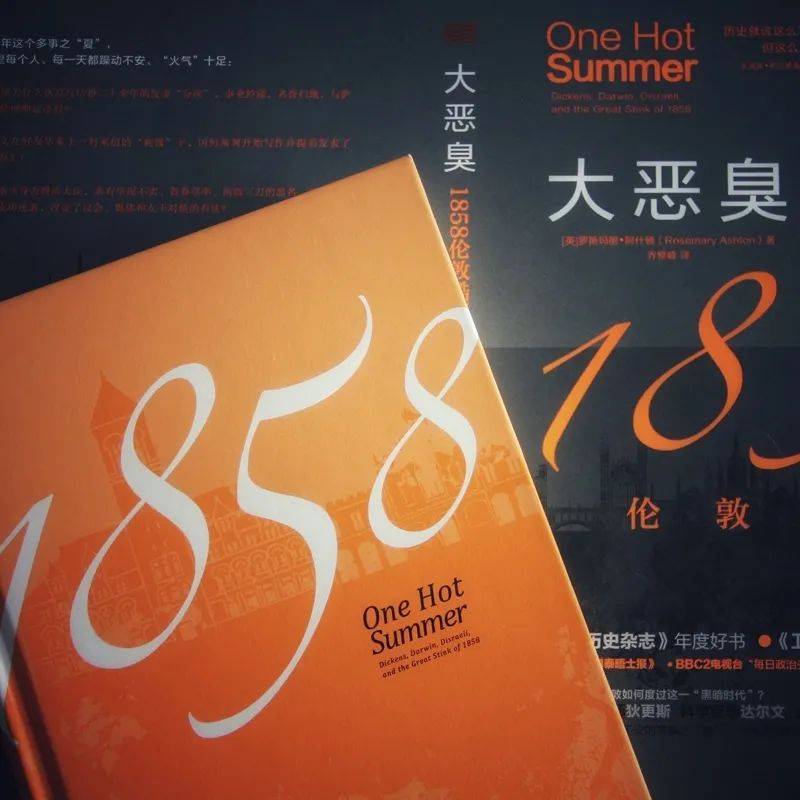黑暗时代城市史:1858年大污染下的伦敦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伦敦街头谋杀案 › 黑暗时代城市史:1858年大污染下的伦敦 |
黑暗时代城市史:1858年大污染下的伦敦
|
“工业时代的七大奇迹”之伦敦下水道系统 那么,“大恶臭”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还要从埃德温·查德威克说起。查德威克是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改革的先驱,1842年撰写了《英国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认为传染病多发与城市卫生条件太差有关,尤其是伦敦等人口密集的城市,卫生状况已经严重危害到了居民的健康。19世纪上半叶,伦敦经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冲击,人口和面积都翻了一番,1858年人口接近250万,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但市政建设明显跟不上城市的扩张速度。不仅街道、河流等公共区域卫生状况很差,家庭排污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当时,伦敦人大都将粪便排到化粪池,由“挖夜土的人”夜间挖走,卖到郊区用作肥料。19世纪40年代,伦敦已经有二十多万个化粪池,很多都已经满溢,成了环境污染的源头。查德威克建议改用抽水马桶,将污物排入下水道,再经下水道排入泰晤士河,最终排入大海。 后来证明,这个建议危害更大,因为伦敦最初修建的下水道主要是用于排雨,增加了抽水马桶排出的污水后,没有经过处理便汇入泰晤士河,加重了河水的污染。这条横贯伦敦的大河也因此被称作“伦敦的化粪池”,制造了1858年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恶臭”。
“大恶臭”漫画 其实,这种恶臭已经存在多年,为什么到1858年就形成了“大恶臭”呢?这还与那年夏天的高温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1855年夏天,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就曾给《泰晤士报》写信,说泰晤士河臭味刺鼻,已经成了“发酵的污水沟”。1858年,伦敦遇到了有史以来最为炎热的一个夏天,气温打破了1846年和1857年的记录。6月16日,格林尼治短时达到了创纪录的39摄氏度。 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说伦敦已经“如炙似烤”;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莫特利也说“没人能想到英国有这么热”。持续的高温加剧了泰晤士河的恶臭。狄更斯过河时就“被熏得头昏脑涨,胃里难受”;约翰·罗斯金庆幸他父亲住在伦敦南部,远离泰晤士河;画家但丁·加布里埃尔·罗塞蒂原本住在河边,现在也为了躲避“臭气熏天的河水”,搬到了朋友家中。 大恶臭引起了伦敦人的恐慌。当时流行“臭气致病”的说法,很多人担心泰晤士河的恶臭会引发霍乱等传染病。伦敦曾多次遭受霍乱等传染病侵扰,最近一次就在1854年,人们的恐惧心理还没有消除。各种报刊报道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报上有很多传言,有的说泰晤士河边的居民正大批地死亡,有的说臭味能把站在河边的人直接熏倒,《笨拙周报》甚至调侃说泰晤士河的恶臭是当时毒性最强的毒药。 不仅普通居民认为臭气能够致病,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和官员也认为霍乱等传染病就是通过空气传播的。1858年,英国科学促进会主席理查德·欧文说,泰晤士河污水漫溢,“污染了空气”,具有“毒害和致病能力”,并随着“一个又一个夏天”的到来而变本加厉。
“大恶臭”漫画 事实上,霍乱等传染病是通过水源而非空气传播的,但当时英国只有约翰·斯诺发现了这一点,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四年前,斯诺发现了污染水源与疾病传播的关系。1854年霍乱爆发时,斯诺发现伦敦索霍区有一个街区死亡率畸高,原因是当地居民都从宽街的水泵打水吃,这些未经处理的水中含有致病的细菌。当时伦敦也有供水公司直接从泰晤河取水。 斯诺调查了两家公司,一个是萨瑟克和沃克斯霍尔公司,另一个是兰贝斯公司,前者水质不洁,后者水质干净,饮用者因霍乱死亡的比例为六比一。虽然大多数人怕的是河水恶臭,而不是饮用脏水,但结果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求政府治理泰晤士河,解决这个“刺鼻扎眼”的公害。 虽然议会和伦敦市政当局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很多既得利益者,如教区委员会、私人供水公司、下水道管理委员会和不愿增加选民负担的议员,都相互推诿,不愿承担治河费用。而且,关于如何解决河水污染问题,政府官员和工程师们也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如狄更斯所说,“人人都有方案,但人人都觉得别人的方案行不通”。 议会大厦就在河边,议员们每年都要忍着恶臭开会。一位下院议员抱怨说,整个6月,乌黑的泰晤士河水就在会议室窗外翻腾,不开窗屋里“就和烤箱一样”,把人“闷个半死”,但一开窗就会被“熏个半死”。终于,在6月最后一天的下午两点,以迪斯累里为首的议员们捂着鼻子,仓皇地逃离了会议室。
即便如此,让议会通过一个治河法案也不容易。6月和7月酷热难耐,泰晤士河臭气熏天,议员们却在治河方案上争执不休,每种方案都要提出质疑,或者要求暂缓表决。迪斯累里出色的口才和谋略发挥了作用,说服议会通过了《伦敦地方管理法修正案》,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泰晤士河净化法案》。 1855年,议会通过了工务大臣本杰明·霍尔提交的“改善伦敦地方管理”的议案,迪斯累里正是在此基础上提交了他的修正案。这也是1858年夏天最重要的政治和公共成就,给伦敦居民的生活和工程建设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巴泽尔杰特的工程奇迹,也让53岁的财政大臣迪斯累里大放异彩。 1858年在英国历史上原本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却因为这场大恶臭出了名。不过,这只蝴蝶引起的反应远不止这些。《大恶臭》能在四个月的时间跨度中呈现众多人物、事件和思想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与罗斯玛丽·阿什顿的微观史研究密不可分。
微观视域下的狄更斯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他的情感生活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但长期未能引起学界重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传记作家和研究者开始关注狄更斯的婚姻问题,克莱尔·托马林的《隐身的女人》(1990)和《狄更斯传》(201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没有详述狄更斯在1858年6月公开宣布与妻子分居后,怎样熬过了那个漫长的夏季,又对他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大恶臭》补充了这方面的细节,并借助狄更斯的亲朋好友、观察者、评论者和竞争者对他的评价,看到了狄更斯的另一面以及这段情感纠葛对他后期小说情节和主题的影响。 对狄更斯来说,1858年夏天是个不堪回首的夏天。46岁的他虽然已经功成名就,却进入了创作的枯水期。这一年,他没有写出任何长篇或短篇小说,甚至没有动笔创作。自1833年开始创作以来,他还是头一次出现这种状况。 1858年初,他还对好友约翰·福斯特说,希望夏天能收回心来,开始创作。但到了夏天,他又与结婚二十二年、为他生了九个孩子的凯瑟琳·霍加斯分居,还在报上公开发表分居声明,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美国和欧洲大陆。阿什顿描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和前因后果,是目前最详细的版本,如她所说,几乎是一份“一天接一天”的记录。阿什顿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情感立场,她同情狄更斯,但更同情被狄更斯伤害了的人。
狄更斯 1858年5月,关于狄更斯的婚姻问题,已经有不少风言风语。伦敦的俱乐部、德比马赛的赛马场和廉价报刊都在传他的绯闻,有的说他跟妻妹乔治娜·霍加斯眉目传情,有的说他跟年轻的女演员朝云暮雨。6月,他在《泰晤士报》和他自己创办的《家常话》上发表分居声明,为自己辩解,说: “这些传言严重不实,极端荒谬,也极其残忍,不仅伤害了我,还殃及一些无辜之人,其中有我至亲至爱的人,也有与我素不相识的人(如果真有其人的话)。” 阿什顿认为,这份声明非但没能平息谣言,反而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只说传言不实,却又不说传言的内容,也没有说那些无辜之人都有谁、是谁杜撰了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导致很多读者都想知道传言是怎么说的、无辜的人有哪些。阿什顿委婉地指出,狄更斯在这份声明中表现得有些虚伪:“他明明很不诚实,却坚持说自己很诚实。” 狄更斯的虚伪还在于他说分居是因为与妻子性格不合,但主要原因是他已经感情出轨。1857年夏天,他在排演威尔基·科林斯创作的戏剧《冰封深海》时,爱上了18岁的女演员埃伦·特南,9月便跑到英格兰北部与埃伦幽会,12月又在信中描述见不到埃伦的沮丧心情: “我希望生在一个有吃人妖的时代,巨龙把守着他的城堡。我希望,长了七个头却没有大脑的吃人妖掠走我心爱的公主——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她——把她关到群山之巅的城堡中,用头发捆住她。我今天就想拿起宝剑,爬上高山,救出公主。如果不成,就血溅当场。这就是我在1857年的心情。” “心爱的公主”让他躁动不安,一直到1858年5月都“没法写作,没法休息”,“从来没有人被一个精灵控制并撕裂成这样”。
狄更斯妻子凯瑟琳 6月,他逼着凯瑟琳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但一直对外宣称是因为与凯瑟琳性格不合才分居的。他对好友安杰拉·伯德特-库茨说,他和妻子“彼此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同情,没有信任,没有感情,更谈不上情投意合”;也对好友约翰·福斯特说,结婚两年后就发现与妻子“根本合不来,毫无希望”。 阿什顿认为这是自欺欺人,只有他自己相信他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福的,因为这样能让他的良心好受些。当时文学界的很多知情者都对狄更斯的做法表示不满。诗人勃朗宁夫人愤怒地说:“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才说性情不合?这算什么借口!我觉得还不如说用情不专呢。”萨克雷也说,狄更斯夫人“做了二十二年的主妇”,生了九个孩子,没犯什么错,“却要被扫地出门”。 狄更斯不仅公开发表了一封毫无诚意的分居声明,还在5月底给阿瑟·史密斯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婚姻问题的“真相”,说夫妻二人琴瑟失调“已有多年”,“从来没有一对夫妻,双方都没有不良习气,却无法相互理解,没有共同语言”。 8月中旬,这封信在美国见报,英国报纸纷纷转载。狄更斯称之为“被泄露的信”。但阿什顿暗示,狄更斯写信时就已经“授权”给收信人史密斯,“允许”他拿给“任何想还我公道的人,或因不明真相而冤枉了我的人”看,并非被泄露了的私人信件。勃朗宁夫人认为,狄更斯就是想公开这封信,拿才华当“棍棒”来对付妻子,“利用人们对他的崇拜,煽动舆论来反对她”。最先发表这封信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也认为,狄更斯的妻子一直默不作声,他自己却咄咄逼人,接二连三地发表声明,自然不得人心。
狄更斯 阿什顿认为,狄更斯在整个分居事件中太过自私和虚伪,不仅不敢承认自己用情不专,还只顾维护自己的形象,丝毫不顾及凯瑟琳的感受,心胸狭隘,言语刻薄。她引用凯瑟琳亲友的话说,公众把狄更斯“奉若神明”,但他的“柔情和慈悲”都只是“童话故事”。 狄更斯的弟弟弗雷德也说他言辞刻薄,心肠太硬:“人们读你的书,还以为你是世上最宽容大度的人。可要是让他们也受你监管,就凭你对亲人的态度,我得说,上帝保佑他们!”同为女性学者的克莱尔·托马林也在《狄更斯传》中说,狄更斯感情出轨后,想表现得像个“单纯的男孩”,反倒暴露了“性格中最阴暗的部分”。 阿什顿还暗示,乔治·艾略特在情感生活上就很有担当,在与有妇之夫乔治·亨利·刘易斯坠入爱河后,能够顶着巨大的压力,与意中人长相厮守,不像狄更斯这样遮遮掩掩,不敢与埃伦公开露面。她认为1858年夏天的这段经历让狄更斯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他后来创作《远大前程》(1860)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就是在探讨罪与耻的主题,尤其是《远大前程》,描写年轻的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痛悔前非,忍受着良心的煎熬。至于她的这些解读是否有说服力,就要由读者自己来判断了。
《远大前程》剧照 19世纪中叶,随着报刊税的取消,涌现出了大量的廉价报刊,它们的《一周闲谈》《俱乐部闲人》等栏目都擅长散布小道消息,既推动了当时对名人的崇拜,也影响了这些名人的行动。 近年来,这些原始的报刊资料很多都实现了数字化,为深入研究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庞大的数据库。《大恶臭》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回顾了“日报、周报、晚报、半月刊、月刊和一便士一份的廉价报纸”对狄更斯分居事件的看法。这恰恰是此前研究比较薄弱的地方。 弗雷德·卡普兰的《狄更斯传》在这方面用的主要是狄更斯等人的书信,彼得·阿克罗伊德的《狄更斯传》虽然提到了英国媒体的报道,但没有具体说有哪些报刊、它们是怎样评价狄更斯的、又对狄更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阿什顿则用大量的例子证明,媒体在这件事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狄更斯的担忧和恐慌,影响了他的判断和行动。一直令狄更斯耿耿于怀的《雷诺兹报》就刊登了一首讽刺诗: “若论用舌头和笔头胡说八道,没人能干得过狄更斯; 但现在他也没法拿道德说事了, 因为从今往后,人们评判他的品行时, 不再依据他的《家常话》,而是依据他的家务事。”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难怪狄更斯竭力要控制媒体的报道。19世纪中叶英国报刊媒体的力量日益壮大,不仅影响了个人生活,也影响了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代表权、外交、婚姻、医疗、城市环境治理等方面的立法。
“大事常成于微隐” 阿什顿的微观史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寻找那些隐微的关联,将很多貌似不相干的话题联系起来。例如,风靡一时的圈环裙时尚影响了盖斯凯尔夫人的短篇小说《克兰福德的鸟笼》;威廉·弗里斯的名画《德比赛马日》借助了摄影术的进步;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亚当·比德》竟然也跟当时著名的德比马赛有关;狄更斯和萨克雷的交恶居然源自街头小报上的一篇文章;达尔文和华莱士不仅同时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还都受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 当然,阿什顿也指出,有些关联和影响纯属偶然。例如,离群索居的达尔文与风口浪尖上的爱德华·莱恩成了莫逆之交;狄更斯的弟弟弗雷德离婚案开庭的那天,同一法庭刚刚宣判了鲁滨逊案;布尔沃·利顿和狄更斯这对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自己的妻子精神有问题。 不管这些关联是明显的还是偶然的,读者都能顺藤摸瓜,找到各种人物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很多不知名或当时有名但现在已被遗忘的人物,如《双城记》中律师斯揣沃的原型埃德温·詹姆斯,以及很多默默无闻的伦敦人,他们都是时代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年夏天公共事件的影响。这些公共事件,从决定治理泰晤士河,到政治代表权、外交、婚姻、医疗等领域的立法,又都受到了日益壮大的报刊媒体的影响。
《双城记》剧照 阿什顿熟稔19世纪英国文学史和思想史,《大恶臭》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史维度,提供了一种时间跨度很小的微观研究,非但没有将文学和历史碎片化,反而借助特写镜头放大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通过一个切面呈现了人物、思想、事件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读者对维多利亚时代有了一种立体的感知。 当然,阿什顿的微观史学研究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可以像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中所暗示的,找到那些知名人物之外的“更全面、也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再现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与活力。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恶臭》的微观视域使历史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 关于19世纪英国和伦敦的史书可谓汗牛充栋,但采用阿什顿这种微观视角的并不多。正如同样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的朱迪思·弗兰德斯所言,“历史就该这么写,但这么写的人太少了”。史学家G. M. 扬格认为, 对于历史,真正的、中心的主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事件发生时人们的感受是什么。这也正是微观史学的一大特色。
《大恶臭》的重心不在于描述历史事件,而是突出事件发生时人们的感受。阿什顿把我们带回到1858年那个燥热的夏天,让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思想、观点和情感。通过那些当事人的直接反应,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变革产生的影响。19世纪是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阿什顿书中讨论的很多问题,大到民主进程、司法改革、医疗改革、环境卫生、市政建设、妇女权益、科学研究和媒体监督,小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婚姻矛盾和时尚娱乐,都值得我们深思。 达尔文晚年写了一本自传,回顾自己的研究生涯,认为大事常成于微隐。在他看来,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随“小猎犬号”出海考察,但这件决定他事业道路的大事却是由两件小事决定的,一是他舅父驾车送他回家,一是船长菲茨罗伊质疑他的鼻型。阿什顿的微观史研究也是要寻找这种不起眼的小事,并在貌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件中找到隐含的关联,呈现出鲜活而又深刻的历史。这一件件小事,也就是1858年夏天在泰晤士河畔扇动着翅膀的蝴蝶。 以1858呈现19世纪英国鼎盛时期的全景风貌 了解英国史、伦敦史与英伦文化与的必读之书 《历史杂志》年度好书 《卫报》每周一书 《星期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推荐 新京报书评周刊、中华读书报推荐 深港书评好书周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