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
您所在的位置:网站首页 › 中国特有的兔子 › 书摘 |
书摘
|
古文献中有一个笼统的集合性质的“大学”概念,其所指向的教育机构及其制度到底是如何演变的呢?这需要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历史性梳理。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学设置于官府之中,实质上为“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西周已设有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大而言之,可分国学与乡学两类,国学又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这种制度一直沿用至晚清。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之称,即中为辟雍,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诸侯设立的称为泮宫。汉初没有固定的教育制度,至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始在长安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可称为大学;后地方陆续设立小学性质或中学性质的学校,聚、乡分别设置序、庠,县、道、邑设立校,郡国设学。太学教师称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或诸生或太学生,高峰时达万余人,教材主要是“孔子之术,六艺之文”。西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初立国子学,与太学并立。至晋惠帝元康元年(291)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六品官以下子弟入太学。隋朝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唐设“六学二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统属于国子监,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具有大学性质,律学、书学、算学具有专科性质;二馆即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崇文馆,属于大学性质的贵胄学校。唐代大学教育发达,外国学生纷纷来留学。宋代教育制度仿效唐代,中央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属于大学性质,统归国子监管辖。明以后,不设太学,只有国子监。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建都南京之时,建校舍于鸡鸣山。永乐十八年(1420),明迁都北京,设置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清因明之旧制,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正如当年光绪皇帝谕旨所言:“国子监即古之成均,本系大学,所有该监事务,著即归并学部。”1905年是古代大学制度改变的关键之年,科举制废止,新学堂兴起,结果导致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崩塌,乃至几千年封建王朝制度的终结。世人曾作如此评价:“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笔者注)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大学”概念只存在于古人学理层面,像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抽象名词。我们既可以说我们古代存在过一种大学教育机构及制度,后人或可称为古典的中国大学模式,又必须承认我们古代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所被冠名为“大学”的具体教育机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只知有辟雍、泮宫、国子学、国子监、书院等名实俱在的具体教育机构及制度,此乃毫无疑义。 二、“大学”语词最初的移译及其概念变化 大学概念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一次变化,就是将其用于西语的移译,从此大学就真正地具有了世界近现代大学的含义,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最早将“大学”一词与英文“university”一词对译的是明代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1582-1649),他于天启癸亥(1623)年译著了《职方外纪》和《西学凡》二书,其中《职方外纪》卷二“欧逻巴总说”在介绍欧洲学制时说:“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其中“大学”就是对“university”一词的移译。《西学凡》则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大学的教育分科体系,其中艾儒略把“哲学”译为“理学”“义理之大学”,《四库全书提要》在介绍《西学凡》时则云:“文科如中国之小学,理科则如中国之大学。”其实艾儒略介绍的西方教育体系对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中文“大学”一词从此与西方“university”开始对译了,令“大学”概念产生了语义变化,从此蕴含了西方近代大学教育机构及其制度的含义,已远超出其原先具有之义。尽管其他传教士后来还用书院等其他中文名词去对译“university”,却没有得到后世的普遍认可,结果只能消逝在历史的尘埃中。 “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文“universitas”。西方的大学诞生于欧洲中世纪,当时的拉丁语称其为“universitas”。“Universitas”在12~14世纪是一个用得很普遍的词,意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团体组织,既可以是一个手工业行会也可以是一个市政团体,最为接近的含义应该是“行会”,所以“它的确是一个中世纪的概念,并为我们了解为什么它只能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提供了线索”。中世纪主要有两种学术行会:一种是以博洛尼亚大学模式为基础的意大利大学,它是世俗的,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由学生聘用并付给薪水,可称为“学生的大学”;另一种是巴黎的比较正统的教会大学模式,教师管理学校,可称为“先生的大学”。后来“学生的大学”模式衰落了下去,“先生的大学”模式却长久不衰。西方“university”概念的内涵同样处于不断地丰富发展过程之中,早已超出了起初的“学术行会”之义,亦大大有别于中国古代的“大学”概念。现在西方人视野中的“university”至少有如下四个含义。 第一,大学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大学确实是历史的产物,并且形成了影响人类的大学传统。西方大学史专家海斯汀·拉斯达尔在一个世纪之前对欧洲大学的经典评价就是:欧洲的大学是中世纪人类精神活动的一个伟大遗产。许美德则认为:“就拿‘大学’(university)这个词来说,在欧洲和北美洲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已经赋予了它特定的形式和内容,蕴含着它在欧美文化背景下丰富的历史遗产。但是,对于中国或其他一些东方国家来说,大学这个概念却有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学术机构。”然而,“大学不是孤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会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 第二,大学是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制度。大学既是依据西方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学术组织,又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制度,重要的是其根本属性是“知识的共同体”。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曾指出:“古希腊的哲学学校并不像中世纪的大学。这种不同不在于享受自由程度的不同,而在于结构上的差异。大学是一个学者团体,具有严密的组织、法人的性质、自己的章程和共同的印记。”但是大学的发展也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第三,大学是一套富有理念的价值体系。美国高等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认为:“大学是由相同的理念或理想,而非行政力量所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大学主要奉行这样三项价值原则:自主与自治的原则、学术自由的原则、教与学自由的原则。以上的价值原则在欧洲中世纪大学时就奠定了的,以后只是以各种形式在各个历史阶段重现生机而已,因为这些价值原则已经成为大学重要的精神与组织制度遗产。但是,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大学,因为“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映”。 第四,大学是一项特殊的国家资产。现在大学完全成为或者非常接近国家的一部分,丹尼尔·贝尔认为,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需要担负四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文化传承创新。所以,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素夫斯基认为大学“是一项特殊的国家资产”,从某种程度来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表现在大学与大学之间的竞争。 当然,随着明末清初及晚清第一波、第二波“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高等教育被导入中国。在将西方大学向中国介绍方面,传教士中除了先驱者艾儒略外,后来还有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Faber)1873年发表的《德国学校论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1883年发表的《西学考略》,都为在中国传播西方大学体系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明代传教士艾儒略最初对于大学的移译,有其翻译的首功,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像他描绘的大学实体的出现,其大学之名也并没有得到普遍使用而流行开来,以至于后来最早在中国诞生的大学都没有冠以大学之名,反而涌现出许多其他名称,如学堂、书院、公学、大学堂、大学校。即使晚清的传教士也没有使用大学之名,1882年丁韪良在考察七国高等教育基础上撰写的《西学考略》中同样没有使用大学之名,称日本东京大学为“太学”,称美国大学为“书院”,“论格致之学以杨湖金书院(霍普金斯大学—笔者注)为先,论律法之学以哥伦书院(哥伦比亚大学—笔者注)为最,至文艺各学诸臻美备莫如雅礼、哈法两书院(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笔者注)”。大学之名得到普遍使用是相对较晚的事情了。 实质上,西方的“university”确实与我国古代的国子学、国子监等教育机构不同,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体系,实在不可等同看待。许美德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既没有自治权之说,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同时,也没有一处可以称得上是大学(university)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一结论既符合历史事实,确实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大学本质上就是一种高等教育制度安排,西方大学制度安排肯定不同于中国古代大学制度安排,这是毫无疑义的。当晚清废除书院而兴办新式学堂、成立学部而取消国子监的时候,既是清政府对于原有教育机构及其制度的废止,又是民间对于新的教育体制的期望。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就是古代大学制度的延续或嫁接,即使古代的大学制度对于新事物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当我们用中文“大学”去移译英语“university”时,在汉语言世界中“university”无疑打上了中文的烙印而中文“大学”也具有了西方的色彩。 三、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举办教会大学溯源 凡物皆有起源,且值得探究,以至于哲学中有个著名命题就是“你从哪里来?”回答这一哲学追问一直是哲学家的使命。西方大学也有一个值得探究与诠释的起源问题。从大学诞生纪念意义角度出发,公元1088年作为欧洲第一所世俗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时间,从此开始大学的历史编年。其实,西方大学到底起源于何时,至今仍是一个谜。1888年,意大利为了举办规模宏大的大学周年纪念庆典,由著名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领导的一个委员会选定了1088年作为“传统建校年”,并举行了博洛尼亚大学800周年纪念庆典,其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所以大学史界称之为“大学起源神话”。但是,这恰恰肯定了博洛尼亚大学的出现是西方大学诞生时期的关键性事件。因为西方大学的产生在人类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曾说:“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得多了。”欧洲中世纪大学是人类黑暗时代萌生的一朵奇葩,在与教会、王室、世俗的各种顽强的斗争中娇艳地盛开着。大学一旦诞生,就显示出卓越的特性,成了“唯一在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其基本模式和社会功能与作用不变的机构”。然而,世界近代第一所大学的“诞生日”竟然是一个“神话传说”,这就给世人留下了更多想象的空间。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同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存在一些争议,很值得我们去探究。 从历史来看,在中国最早举办西式高等教育的是西方传教士,其高等教育机构现统称为教会大学。西方大学这一“舶来品”到底是何时在中国登岸的呢?这应该从古代和近代两个不同阶段来寻源。1571年,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圣保禄公学,然后于1594年升格为大学,并以圣保禄学院(俗称“三巴寺”)为名注册成立,1762年,按照葡萄牙国王唐约瑟的命令解散,作为大学前后存续了168年。圣保禄学院不仅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所西式教会大学,而且是整个远东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也就是说,西式大学在中国出现的实体要比艾儒略移译的大学之名要早很多年,只是没有使用大学冠名而已。倘若按照现在的历史分期法,圣保禄学院应该是属于中国古代教会大学了。 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应是山东的登州文会馆。1863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来到中国,于次年在登州创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家境贫寒的学生。当时,因为担心学生的家长会迫于社会的压力,让学生退学,所以学堂要与他们签约。1877年该学堂改名为登州文会馆,具备了中学水平。1882年,美国纽约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登州文会馆为大学。至此,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出现了,并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登州文会馆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的众多‘第一’可谓数不胜数——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第一批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第一个使用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第一个引进X射线理论知识,第一个使用发动机、亮起电灯、制造电子钟,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教学和写作,第一个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声学理论,第一首学堂乐歌,第一个发展学生自治组织……”1904年,登州文会馆正斋迁移潍县,与英国浸礼会于1884年在青州创办的广德书院中的大学班合并,取两校名的头一个字,定中文名为“广文学堂”(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1909年,广文学堂的英文名“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改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17年,正式向中国政府备案,改中文校名为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 在英语世界同时启用“Cheeloo University”作为非正式校名,而其正式名称仍旧沿用“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24年在中国注册立案后,学校以“私立齐鲁大学”为校名,学校颁发的英文文凭上则使用“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 University)” [“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齐鲁大学)” ]的名称。19世纪中国教会大学还有一些,但是举办时间都比登州文会馆要晚,其起初的中文名称同样不是大学,如金陵大学前身是1888年美国基督教会美以美会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岭南大学前身是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广州创办的格致书院。由此看来,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是1882年经美国纽约长老会总部正式批准的登州文会馆,1917年始冠以“大学”之名,但是在英语世界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到正式的过程。 教会大学的起源能否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主要有这样三个原因:一是教会大学是半殖民地的产物,表现出外国势力对于中国教育主权的侵犯;二是教会大学举办者与管理者是外国教会和传教士,而不是中国组织和法人;三是教会大学批准举办机关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外国机构。登州文会馆于1882年升格为大学的批准机关是美国纽约长老会总部。圣约翰大学堂于1905年在美国华盛顿取得正式注册。金陵大学于1911年获得美国纽约州教育局局长和纽约大学校长签署的特别许可证,金陵大学正式在美国纽约教育局立案,得以享受“泰西凡大学应享之权利”,大学毕业文凭由纽约大学校董会签发。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在美国立案,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在1900年中华教育会第六届会议上曾坦白地承认,“立案后的中国大学便变成为中国土地上的美国附属学校”。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治外法权原则的扩充。到1917年,英国在华设立高等学校19所,美国设立14所,英美合办9所,在校生共计9492人。教会大学具有“治外法权”,颁发的文凭来自国外,清政府允许其自由开设,“亦毋庸立案”,更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制约,所以我们不能将教会大学作为中国近代大学的起源,也不能同国人举办的近代大学相混淆。 然而,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教会大学的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西方教会学校在华“完成了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为中国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提供了示范性的借鉴。教会大学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把西方现代大学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给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传统教育提供了向近代教育转变的某种示范与启迪”,与几千年来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百熙在《拟进学堂章程折》中坦言,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近代教会大学尽管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个篇章,但是我们也不可无视其宗教性质与文化殖民的目的。 四、国人近代举办大学溯源 我们经常谈到近代大学的起源,言下之意就是近代大学与古代大学是有分界的,或者说两者不是一回事,否则我们就不会去寻求近代大学的起源了,而是到夏商周时期去说事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以及启民智、废科举、兴新学之产物,与传统的所谓大学教育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罔顾事实而言他。 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大学是北洋大学堂,紧接着就是京师大学堂,都是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清朝晚期。面对强寇环伺的岌岌危局,光绪皇帝祈愿能够出现“中兴”之局面,便下诏征“自强”“求治”之策。1895年,盛宣怀邀请中西书院院长美国人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1857-1930)共同草拟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希望奏请光绪皇帝开办一所“天津中西学堂”。《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大学章程,对大学学制、招生办法、规模、课程、经费和管理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盛宣怀筹设的这所学堂,虽名“中西学堂”,但其章程中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均属“西学”范畴,王文韶索性将其直接改为“西学学堂”,并于1895年9月30日向光绪皇帝上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两天之后,1895年10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光绪皇帝在这份奏折上做了“该衙门知道”的朱批,然后以军事急件的形式,当日就送返天津。清朝政府同意开办学堂的批准日期为1895年10月2日(现在天津大学以其前身西学学堂的批准日期10月2日作为校庆纪念日是准确又合理的),而学堂的开办日期为1895年10月18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一日)。至于该学堂之名,光绪皇帝御批的是西学学堂,对此应毫无疑义。然而,获得御批之后,政府公告则是以天津头等学堂为名,与当年9月22日王文韶《天津头等二等学堂批示》相符合,时人称之为北洋大学堂。据考证,“1895年11月8日,《直报》上刊登的一篇政府公告出现了‘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的表述。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也刊登文章,并标有中文标题‘北洋大学堂见闻’,文章结尾对盛宣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建起了一所西方式的大学表示了高度赞赏,并用中文再次明确标示了‘北洋大学堂’的名称”。实质上,1903年,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才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899年底,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头班25名学生完成了四年的学业,经直隶总督考试合格后,成为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1900年初,当时年仅19岁的王宠惠,从北洋大学堂获得了绘有蛟龙出海图样的“钦字第一号”“考凭”,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中华民国教育部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令“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1912年,北洋大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校。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大学令》。《大学令》规定:“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设立时以文,理二科为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才能称为大学:文理两科并设;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这就明确了大学的学科组织条件。1913年,北洋大学校又根据中华民国教育部令改称国立北洋大学。1913年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冠名“大学”之开启年,从此这一作为机构名称的专有名词开始行遍神州大地。“大学”之名指向了具体的机构之实,并真正以新的内涵与外延进入了中国概念史,可谓“旧瓶装新酒”。“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洋务派的盛宣怀创立的北洋大学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国政府行使教育主权并在中国国土上创办的“国批官办”大学,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大学,这是毫无疑义的。 与北洋大学堂相比,京师大学堂就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批国办”的大学。由于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们还是需要在此回溯其开办之初的情形。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在第六次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自京师立大学”。2月15日(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当日诏谕:“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妥议具奏。”由此看来,按照通例,2月15日应是京师大学堂获得“准许状”的建校纪念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而成立京师大学堂成为唯一写进这一维新纲领性文献“天字第一号”的变法项目,明确指出“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7月3日,总理衙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所奏拟之《京师大学堂章程》为梁启超代总理衙门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该章程明确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这就使其在充当“为各省之表率”的“全国最高学府”角色的同时,还必须身兼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直到1905年学部成立为止。由此看来,京师大学堂创立之初身兼传统的太学制度与现代的大学建制的双重身份。1898年8月5日和8月10日意大利和德国公使分别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干涉京师大学堂设置之事。8月26日管学大臣孙家鼐复总理衙门片称:“查中国开设大学堂,乃中国内政,与通商事体不同,岂能比较一律。德国、意国大臣,似不应干预。”由此可见,京师大学堂创办过程中受到了外国势力对于我国教育主权的干预。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后与教育行政管理职能分离,独立成校。1912年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严复为首任校长;分科大学监督改称学长。5月24日,“北京大学校之关防”启用。但是,私人已经将北京大学校简为北京大学了,5月15日,蔡元培参加北京大学校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称北京大学校为大学,并言“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7月22日,校长严复向教育部写了《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已称北京大学。由此看来,“北京大学”冠名是由非正式开始的。1913年4月北京大学校改称国立北京大学,当月《中华教育界》第一卷第四期报道“北京大学第一次毕业”,社会媒体亦称北京大学。近代教育机构“大学”冠名之初发生了“非正式”这一有趣的历史现象,外国教会起初将“齐鲁大学”作为非正式之名使用,而国办的“北京大学”起初也是由个人作为非正式之名开始使用的,“大学”之冠名经历了一个由非正式到正式的过程。 继北洋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兴办之后,清政府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初宣布实行所谓“新政”,8月颁布“兴学诏书”,昭告“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是年,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并获准,11月16日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堂,成为后来各省举办学堂的榜样。1902年(壬寅年)清政府颁布了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称为“壬寅学制”,1903年又推出了“癸卯学制”,制订了“大学堂”“通儒院”作为最高学府。辛亥革命后,1912年10月24日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令》,规定了大学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改“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通儒院”为“大学院”,1913年又公布了《大学规程》,基本仿照西方的大学制度安排。许美德认为:“在这个新学制中所使用的术语也表明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用‘大学院’和‘大学堂’这两个术语,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是想把西方的现代知识分类法纳入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体系之中。” 五、结语 我们对于“大学”概念演变作历史性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交织于从古至今的历时性与西方到东方的共时性转化,这不仅是一个语言史研究的范畴,而且是一个教育史研究的问题。只有认清了大学概念的前世今生才能明白围绕这个概念产生的所有纠缠。古代“大学”概念是对所有古代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制度的统称,并不存在一个冠名为“大学”的实体机构。明代传教士艾儒略首次将其作为英语“university”的汉语对译词,从此“大学”概念就开始具有西方“university”的含义,而“university”是东方原来没有的新事物。所以我们应该在明确了“大学”概念转化的前提下,来探讨中国近代大学之起源,此乃正途。晚清时期清政府起初兴办的“大学”以及“新政”中推行的所谓“新学”,无论冠以何种名称,无论是“大学堂”还是“大学校”,都是仿照西学体制而建,无怪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说:“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是,就是光绪政变,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因此,按照近代“大学”概念去理解,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应该是1895年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但是也不能忽视1898年举办的京师大学堂在近代大学起源时期的重要意义。至于教会大学中最早的始于1882年的登州文会馆,由于教育主权问题,是不能作为中国近代大学起源来看待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至此,我们应该是将近代大学起源中的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搞明白了,不再是一笔说不清楚的糊涂账了。当然,最后我们还需要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能会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哈罗德·珀金曾指出,产生于欧洲12世纪的大学这种古老机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向世界各地的“移植”,“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因此,在世界高等教育与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在谁都在谈大学的情形下,我们有权利与义务去诠释与发展“大学”概念,并看清楚我们国家大学的来时路,然后按照大学办学规律,办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境界的大学,为世界提供可资借鉴的“中国大学模式”。 图书信息
《大学建构》 蔡先金 著 定价:138.0元 2019年9月出版 ISBN 978-7-5201-5169-6 作者简介 蔡先金,历史学博士,古典文献学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山东交通学院院长助理、济南大学副校长、聊城大学校长,兼任过国家教指委委员、国家出版基金评委等。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与教改课题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新华文摘》《中国社科文摘》等转载1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近20部(其中1部入选国家社科文库),获得国家级与省级教学奖与社科奖10余项。 内容简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大学处于深刻的变革与建构过程中,大学人行进在思与变的路途上。在如此宏大背景下,本书汇集了作者对大学教育深度反思与认真探索的成果,既有历史的回溯,又有当下的实践;既有规律的遵循,又有主观的能动;既有理念的觉醒,又有蓝图的绘制;既有精神的提振,又有物化的配备;既有情怀的澄净,又有案例的充实;既有抱负的展现,又有操作的层面……意图展现一幅充满诗与力量的区域大学黄金时代的图景。 目录 第一篇 理念与文化 阅读不关风与月内心繁华始是真 我们大学的精神资源 大学“书院”建制的精神面向及其现实展开 大学的担当与价值维度 默会知识论视域下的大学默会教育 大学公共空间教育审视与反思 校园二次规划理念与格局的建议 做一名真实的大学人 第二篇 管理与治理 我国大学现代化进程及其特质 一流与变局:“一流建设”背景下区域大学发展愿景与突围策略 区域大学发展阶段评估、资源魔咒与现代化进程 区域大学综合改革草案 后勤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前头 提着变革的工具箱高配未来 变革迫在眉睫 我们的支点与出路 第三篇 教学教研 以“学”为中心,写好“一流本科”教学日志 做好大学布局这篇大文章 计算机教育的认知与趋势 整体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作 开创教学文化建设新局面 目前教学评建工作的形势与任务 “一流本科”建设共识 第四篇 学科科研 学术是大学的灵魂 学术之于大学意义的反思 高等教育视域下学科与专业关系及其现状厘析 学科建设怎么办? 山高人为峰 高瞻远瞩 第五篇 开放与合作 开放合作与耦合发展 天地广阔 大有作为 第六篇 教师工作 山青花自开 夺得千峰翠色来 同青年教师谈论几个问题 教育者也应该接受教育 第七篇 学生典礼致辞与寄语 学以成人 大道至简 坚毅前行 聊大学子就是有聊大学子的样子 锐于求志 认识自己 立己达人 积优成习 高配人生 反躬自问 多反思 准备好了 开始走出校门 我们大学的餐厅文化 致语2017年高考同学 致语2018年高考同学 第八篇 大学历史及其他 “大学”之名与中国近代大学起源考辨 破土新芽多靓丽——济南大学泉城学院的最初岁月 感恩中学生活 聊大,您好! 行者无疆 荷语 后记
策划:xwz 编辑:cxq 审校:tx 点“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
|
【本文地址】
今日新闻 |
推荐新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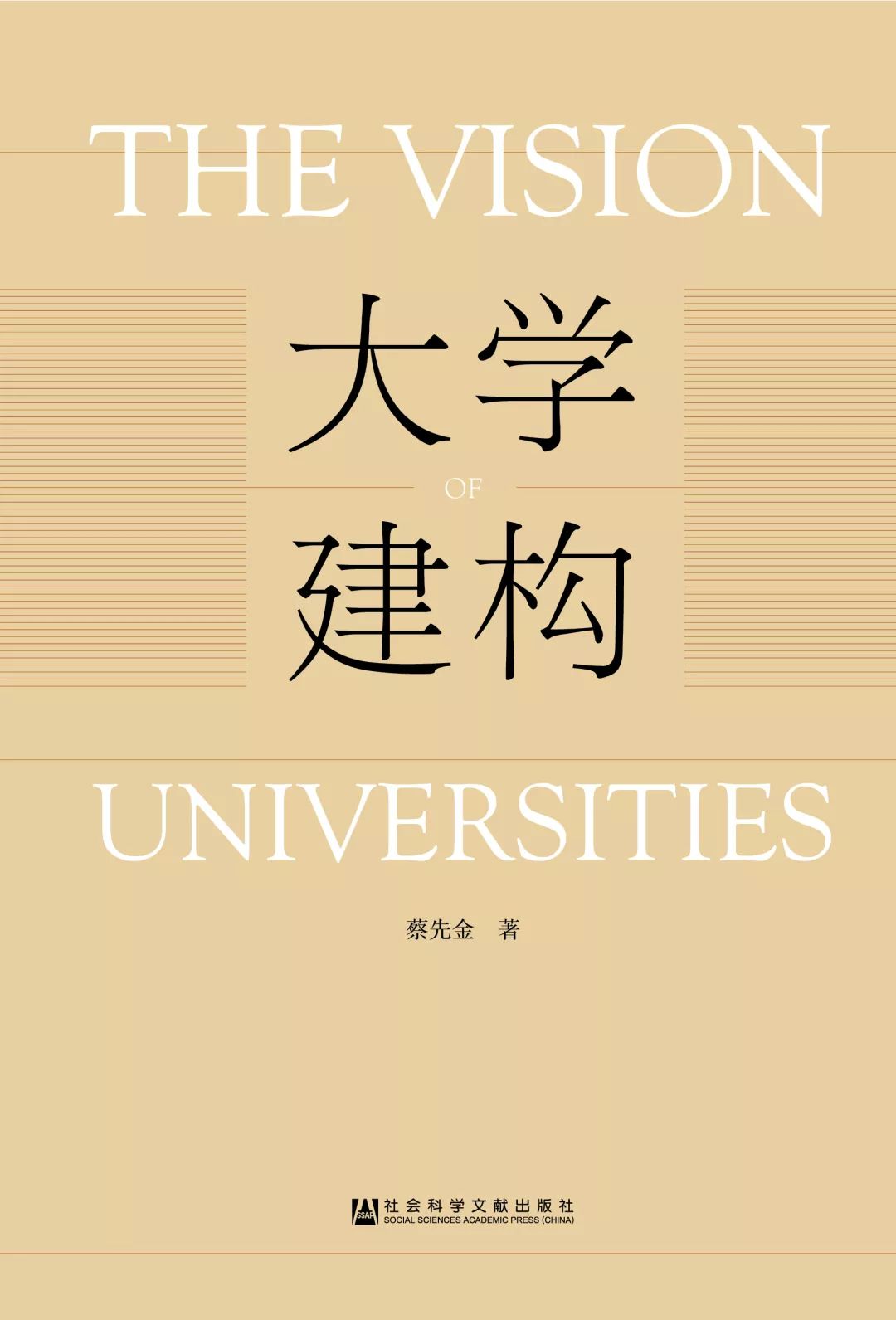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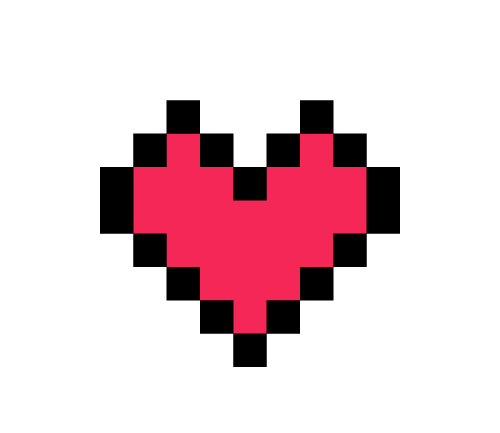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